衡水人萧振邦先生在《论装修补古旧书集》中提到,他在故宫图书馆修复善本的七年间,“曾遇到一部真正孤本,天下无有第二部”。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天下若有第二部,那还算什么孤本?不过,按我家乡人的说话习惯,但凡用上“真正”二字,那就是双重强调了:一来假孤本为数也不少,非孤本而乱说孤本的正多,所以必须用“真正”二字封印;二来,孤本未必就是珍本、善本,所以,珍稀第一、天下无双之善本,才当得起“真正孤本”之名。
让萧先生经手修复、目验心仪的真正孤本,是袖珍本《佩文韻府》的写抄本。看他描述此书的语句与语气,可以想象,每逢说起此书,他必会神采飞扬,心驰神往,如数家珍。
“忽看一片乌黑,”他说,“用放大镜视之,清清楚楚,工笔小楷,字小如小米粒,一律到底,实称国宝孤本,世间难得,无对无双”。他记得这部书的所有细节:共一百三十二册,订线,蓝绸皮。据殿版《佩文韵府》抄写。但开本缩小,书长二寸五分,宽二寸。板心长宽均一寸五分。半页行十六。每行二十二字。书前有乾隆相片,坐相,一寸高,着色,头戴冠冕,身穿龙袍,挂朝珠前补,足登朝靴。上有五方盖印:一、古稀天子,二、八徵寿念之宝,三、五福五代堂,四、太上皇,五是御览之宝。抄写这部国宝,只能用一根毛的笔完成……。
读到这里,我实在想在夜书房哪本书里找出此书的图片来。二十多年前我买过一本《两朝御览图书》画册,里面或许有此书图片?无奈我这会儿却找不到这本书。又恍惚记得今年三月我在杭州的《琳琅萃珍》大展上好像见过这部袖珍本的,一查手机图片,我见到的确实是乾隆御览过的袖珍书,但不是《佩文韵府》,而是《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李似之辑 宋刻本)。
《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五色织锦书衣,四眼线装,黄缎书签题:“万卷菁华后集。”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
萧先生书中所说“五方盖印”,应该就是所谓“小五玺”。杭州展览上的“万卷精华”也是袖珍本,前后钤的都是“小五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太上皇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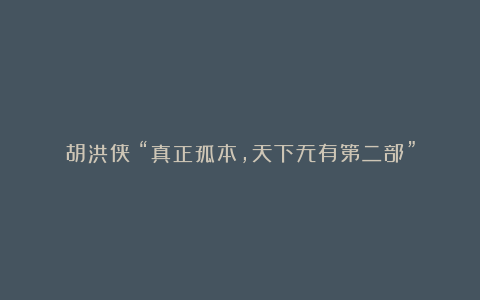
萧先生书中讲版本名称时,列出了古籍中巾箱本与袖珍本的尺寸,我因此知道巾箱本与袖珍本并非完全是一回事,袖珍本要比巾箱本更小。传说举子们赶考时揣在袖子里准备作弊的“小抄”才叫袖珍本,巾箱本不过是可以放在专门收纳头巾箱箧之中的板框较小的书,主打一个便于携带与收藏。
书籍开本中的小书(袖珍本、巾箱本、口袋本)诞生于写本时代,而非刻本时代或印刷时代。一般认为中国的巾箱本始于南朝,人们多把南齐王萧钧视为“巾箱本第一人”。据《南史·齐衡阳王钧传》,萧钧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
西方书籍史上,袖珍本的诞生比中国早三四百年,时值罗马帝国时期。据伊莲内·巴列霍《书籍秘史》(李静译,湖南文·博集天卷,2022),公元一世纪时,第一批手抄口袋本已经诞生,书袖珍到一手可握。西塞罗甚至说,他见过荷马《伊利亚特》羊皮书可以放进一只核桃壳中。
诗人马提亚尔据信是第一个对抄本册子感兴趣的作家,他写过一本《礼品》,书中给每件礼品写一首讽刺诗,介绍其材质、价格、特点或用途。那时他已经把书籍也列入礼品单内,推荐的是14本文学作品,其中5本是羊皮纸口袋本。多年后,他自己的诗集也加入了袖珍本行列。“如果你希望我的小书能陪你去任何地方,”他自卖自夸道,“如果你希望长路漫漫始终有它们相伴,来买羊皮纸的小书吧!大书就留给图书馆,我的小书一只手就能持握。”
除了便于携带,罗马帝国时期的小书还有特殊用途,那就是偷偷阅读,这个我们这边科考作弊专用的袖珍本有异曲同工:都是偷读,我们的举子们偷读的是八股文章,罗马人偷读的则是《圣经》。彼时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教徒常常受迫害。口袋书方便他们迅速将其藏进长袍,也方便他们迅速地找到文中的某个段落。另外,基督徒希望以袖珍册子跟犹太教的象征、代表异教徒的羊皮卷划清界限,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
因为袖珍抄本册子可以陪伴读者去任何地方,罗马人的读书风气好像要比先前更浓了。他们去打猎,在等待猎物落网时会读书;晚上失眠无聊时,也会读书。有文学作品记载过那时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的女人,坐在马车里读书的旅人,躺着读书的食客,还有站在回廊上读书的少年,好像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读书。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现在书店里新书的开本正在变小,厚度正在变薄,袖珍版或口袋本越来越多。希望这类小书不仅适应经济下行的时代,降低出版社的成本与新书的价格,还能鼓励读书人能随时随地读书,且读得聚精会神。我另有一个希望或奢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亲眼读一读萧振邦先生说的“天下无有第二部”之真正袖珍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