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颅磁刺激(TMS)诱发电位(TEPs)是一种创新性指标,可用于检验脑连接性并开发精神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因此,尽可能减少跨研究与跨受试者的 TEP 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可能源于方法学选择)至关重要。通过结合经典的峰值分析与微状态(microstate)研究,我们检验了在靶向初级运动皮层(M1)时,TMS 脉冲波形与电流方向如何影响皮层—皮层回路的招募。我们旨在厘清:改变这些参数究竟是影响同一神经环路被激活的程度,还是会改变诱发激活扩散所经过的通路。32 名健康受试者接受 TMS-EEG 实验,操控脉冲波形(单相、双相)与电流方向(后—前、前—后、外侧—内侧)。我们评估 M1-TEP 各成分的潜伏期与振幅,并采用微状态分析检验头皮地形图(topography)的差异。结果显示,TMS 参数显著影响 M1-TEP 成分的振幅,但对潜伏期的影响较弱。微状态分析表明,在单相刺激中,电流方向会改变早期 TEP 潜伏期的诱发微状态模式,并改变其持续时间与全局场功率(global field power)。本研究表明,单相脉冲的电流方向可能通过更具选择性地激活神经元群体及皮层—皮层通路,来调制对 TEP 信号有贡献的皮层源。双相刺激降低了与电流方向相关的变异性,当 TMS 靶向缺乏解剖学信息指导时,可能更为适用。本文发表在Brain Topography杂志。
引言
经颅磁刺激与脑电图(TMS-EEG)的结合,使我们能够以较高的空间特异性与时间分辨率研究 TMS 所诱发的皮层反应性与连接性(Bortoletto et al. 2015;Hernandez-Pavon et al. 2023b;Ilmoniemi et al. 1997;Massimini et al. 2005)。由于可以直接刺激皮层,TMS-EEG 允许检验被刺激区域对未刺激区域的因果影响。确实,TMS 诱发电位(TEPs)代表未刺激区域的次级激活,这些区域因靶区活动而产生反应(Hernandez-Pavon et al. 2023)。基于这一特性,TEPs 日益被探索为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包括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神经退行性疾病与癫痫等,这些疾病均强调了连接性异常(例如 Bagattini et al. 2019;Cao et al. 2021;Casarotto et al. 2019;Casula et al. 2023;Gefferie et al. 2023;Tremblay et al. 2019)。尽管 TMS-EEG 使用不断增加,但刺激参数(如线圈取向、TMS 脉冲的技术特征)对记录信号的影响仍不明确,这可能导致 TEP 的变异性并妨碍解释。为提升 TMS-EEG 在基础与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必须理解哪些技术参数塑造了记录信号,以及如何操控这些参数以优化信号测量。
在关键 TMS 参数中,已有证据表明脉冲波形与电流方向对刺激结果至关重要,它们决定靶区内被 TMS 优先激活的神经元群体。过去三十年中,TMS 文献常以运动系统作为研究模型,因为可通过运动诱发电位(MEPs)方便读取刺激效果,而 MEP 又可作为 M1 外源性激活的代理指标(例如 Casula et al. 2018;Cirillo and Byblow 2016;Corp et al. 2021;Davila-Pérez et al. 2018;Di Lazzaro et al. 2001;D’Ostilio et al. 2016;Kammer et al. 2001;Sakai et al. 1997;Sommer et al. 2006, 2018)。与本研究相关的是,Aberra 等(2020)近期构建了人类运动系统的计算模型,显示在 M1 上施加后—前(PA)方向电流的 TMS,会激活位于中央前回更靠后的神经元,而前—后(AP)方向电流激活的神经元更靠前(Aberra et al. 2020)。中央前回尾侧部分包含皮层—运动神经元细胞,它们通过快速单突触投射连接脊髓运动神经元;相较之下,头侧部分的神经元通过多突触或较慢的单突触连接与脊髓运动神经元相连(Siebner et al. 2022)。
重要的是,尽管尚少被探索,但脉冲波形与电流方向也可能决定哪些与其他皮层区和脑结构的连接被优先激活。动物研究显示,中央前回头侧与尾侧的神经元群体分别与不同的邻近皮层区具有直接连接。例如,猴研究发现,M1 头侧神经元主要连接躯体感觉区与高阶运动区,而尾侧群体更多与初级躯体感觉皮层交流(Stepniewska et al. 1993);此外,这些神经元的皮层—丘脑连接也略有不同(Matelli et al. 1989;Stepniewska et al. 1994)。在人类中,使用重复 TMS 与配对脉冲 TMS 的研究提示:对 M1 及其互联区域的刺激会依据所采用的 TMS 参数产生不同的神经生理后效应(例如 Delvendahl et al. 2014;Federico and Perez 2017;Hamada et al. 2014;Koch et al. 2013;Ni et al. 2011;Tings et al. 2005)。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不同 TMS 参数不仅会激活皮质脊髓束中可区分的神经元(这一点已被充分研究;综述见 Di Lazzaro et al. 2018;Spampinato 2020),还会根据 M1 被优先刺激的神经元群体,激活不同的皮层—皮层通路与网络。
迄今,少数研究探讨了在靶向 M1 后,电流方向与脉冲波形如何影响 TMS-EEG 结果(Bonato et al. 2006;Casula et al. 2018;Guidali et al. 2023),并发现主要在早期反应(即 TMS 脉冲后 <50 ms)出现信号振幅与潜伏期的调制。在我们研究组的工作中,我们聚焦于一个可能反映经胼胝体抑制的早期 M1-TEP 成分(即 M1-P15),发现当在单相刺激条件下改变线圈取向时,该成分会消失(Guidali et al. 2023),提示信号经胼胝体传播可能依赖所采用的 TMS 参数。
在提取 TEP 波形时(如上述研究),通常只使用了可用数据的一部分,主要关注特定时间窗内某些目标电极上的响应振幅,而忽略了全头皮信号的时间性转换。然而,TEP 振幅与潜伏期的差异无法区分:改变刺激参数究竟影响同一神经环路的激活程度,还是影响所涉及的皮层通路。地形图分析可以克服这一问题,因为它能够提供皮层信号传播的时空动力学信息(Michel et al. 2024;Vaughan 1982)。地形图是大脑内皮层源或网络激活的结果,其调制反映神经元活动来源的变化(Ding et al. 2024;Sulcova et al. 2022)。在 TEP 等诱发电位场景中,地形图分析可通过检验地形一致性,检测诱发反应皮层源的跨个体一致性(Habermann et al. 2018;Koenig et al. 2011);也可用于识别微状态,即地形图固定不变的时间片段(Lehmann et al. 1987;Michel and Koenig 2018;Tarailis et al. 2024)。微状态提供关于诱发电位成分的地形与持续时间信息,通过对其源模式的洞见,补充经典峰值振幅与潜伏期分析(Murray et al. 2008;Sulcova et al. 2022)。在我们的研究中,微状态分析对于理解刺激参数变化是否导致不同皮层回路被招募尤为关键,这可能涉及不同脑网络的激活(例如 Sulcova et al. 2022)。这种知识与波形分析互补,有助于更好理解 TMS 参数在记录反应中的作用。
利用 TMS-EEG,本研究旨在探讨在 M1 刺激后,TMS 电流方向与脉冲波形对不同皮层—皮层回路激活的影响,从而阐明 TEP 记录中可能的变异来源。为此,我们在记录 EEG 的同时,使用三种电流方向(PA、AP 与外侧—内侧 LM;均指脑内诱发电流方向)以及两种脉冲波形(单相与双相)刺激 M1。数据采用两种互补方法分析:首先,评估 M1 上经典 TEP 成分(N15、P30、N45、P60、N100、P180;Beck et al. 2024)在刺激参数改变时的振幅与潜伏期是否受影响;其次,检验不同条件下头皮地形图是否变化,以及微状态是否能提供信息以更好表征 TMS 诱发的 M1 活动扩散,并据此在刺激参数调制时识别不同回路的激活。
材料与方法
受试者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来自 Guidali 等(2023)的原始工作。数据集包含 40 名右利手健康受试者,年龄 18–50 岁,且符合 TMS 安全标准(Rossi et al. 2021)。在 40 名受试者中,我们排除了需要刺激强度超过刺激器最大输出 90% 的受试者(6 名)以及未完成全部实验区块的受试者(2 名)。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 32 名受试者[女性 18 名;年龄中位数:26 岁(范围:20–49 岁);受教育年限中位数:16 年(范围:13–21 年);爱丁堡利手量表(Oldfield 1971)得分中位数:83%(范围:42–100%)]。研究在意大利布雷西亚IRCCS神经生理实验室进行。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伦理指南,并获得该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流程
受试者参加一次单次实验会话,包含 7 个 TMS-EEG 同步记录区块(更多细节见 Guidali et al. 2023)。每个区块由电流方向(PA、AP、LM)与脉冲波形(单相或双相)的组合所定义。需要说明的是,在双相刺激中,我们始终以 TMS 脉冲的第二相作为参照(例如双相 AP-PA 刺激记作“双相 PA”)。每个实验区块依次包括:静息运动阈值(rMT)评估、TMS-肌电(EMG)记录以及 TMS-EEG 记录。TMS-EMG 以及第七个“单手收缩”条件下的 TMS-EEG 区块在本研究中未进一步分析。原研究(Guidali et al. 2023)中的 MEP 模式见补充图 1。rMT(静息运动阈值) 采用序贯测试最佳参数估计(PEST)程序测量(Awiszus, 2003)。TMS-EEG 记录每个区块包含 80 个 TMS 脉冲,脉冲间隔在 4000–6000 ms 之间随机抖动。每个区块的 TMS 强度调整为该区块 rMT 的 110%。六种条件下的 rMT 值见补充图 2。区块顺序按照拉丁方设计在受试者间进行平衡(图 1)。每个刺激区块结束后,向受试者施以简短问卷,评估与 TMS 相关的外周感觉是否存在及其不适程度(改编自 Giustiniani et al. 2022)。结果显示这些感觉在不同实验条件间无差异(见补充图 3)。
图1 Guidali 等(2023)原研究的实验流程
受试者在完成 EEG 与 EMG 安装、神经导航以及拇短展肌(APB)热点定位后,接受 7 个刺激区块。每个区块由特定脉冲波形与电流方向组合构成,包含 rMT 计算、20 次 MEP 记录以及 80 次 TEP 记录。为本研究目的,单手收缩条件下的区块未纳入分析。我们所有图中,TMS 线圈上的红白箭头表示在 M1 内诱发电流方向。
在整个实验中,受试者坐于光线昏暗的房间内,前臂舒适地放在桌面上,面对显示注视十字的电脑屏幕。要求受试者睁眼并注视十字。实验区块开始前,佩戴 EEG 帽,并在右侧拇短展肌(APB)上放置 EMG 电极。随后使用双相刺激器与 PA 电流方向确定右侧 APB 的运动热点,并将其作为实验期间一致的刺激靶点。
受试者佩戴降噪耳机,在各区块中播放白噪声,以尽量减少 TMS 锁定的听觉伪迹对 EEG 的污染(Biabani et al. 2019)。白噪声音量根据个体调整,最高至 90 dB。在 TMS 线圈下方放置一层薄泡沫,以减弱 TMS 引起的感觉刺激。
TMS-EEG 记录
所有刺激区块均使用“8”字形线圈(Magstim Alpha B.I. Coil Range,直径 70 mm)。单相区块使用 Magstim 2002 刺激器;双相区块使用 Magstim Rapid2(Magstim,英国 Whitland)。电流方向随区块而变:PA 区块线圈相对中线旋转 45°;AP 区块线圈相对 PA 取向旋转 180°;LM(外侧—内侧) 区块线圈相对中线旋转 90°。使用 SofTaxic Optic 3.4 神经导航软件(EMS,意大利博洛尼亚;www.softaxic.com)持续监控线圈位置。
EEG 采用与 TMS 兼容的系统记录(g.HIamp 多通道放大器,g.tec medical engineering GmbH)。使用 74 导电极(EasyCap,Brain Products GmbH,德国慕尼黑),按 10–10 国际系统放置;参考电极为 FPz,接地电极置于鼻尖。采样率 9.6 kHz,皮肤—电极阻抗持续维持在 5 kΩ 以下。记录前与记录中均对 EEG 信号进行目视监控,以识别并处理明显伪迹,如长时间衰减、噪声通道与工频噪声。
EEG 预处理与 TEP 提取
我们使用 Guidali 等(2023)相同的预处理 TEP 数据。预处理流程在 MATLAB R2020b 中实现,结合 EEGLAB v.2020.0(Delorme and Makeig 2004)与 FieldTrip v.20190905 函数(Oostenveld et al. 2011);该流程亦为我们研究组常用管线(Guidali et al. 2023;Zazio et al. 2022, 2024)。
具体而言,预处理步骤如下:在 TMS 脉冲附近对连续 EEG 进行插值(−1/2 ms),进行高通滤波(1 Hz 窗函数 sinc FIR 滤波器,阶数 31680,使用 EEGLAB 函数 ‘pop_eegfiltnew’ 默认参数),下采样至 4800 Hz,并围绕 TMS 脉冲分段(−700 ms 至 700 ms)。使用基于源估计的去噪算法 SOUND 降低测量噪声,采用球形头部三层模型构建导联场矩阵,正则化参数 λ = 0.1(Mutanen et al. 2018)。随后执行:(a)使用 EEGLAB ‘pop_jointprob’ 进行第一次自动伪迹剔除,剔除 EEG 信号超过 5 个标准差的分段;(b)进行独立成分分析(ICA),专用于眼动伪迹校正,使用 EEGLAB ‘pop_runica’(infomax 算法;纳入 73 通道;计算 72 个 ICA 成分)。对 ICA 成分进行目视检查,并依据垂直与水平眼动典型的地形与频谱模式剔除相应成分。随后,使用 SSP-SIR(source-informed reconstruction)算法去除前 50 ms 的 TMS 诱发肌电伪迹(Mutanen et al. 2016)。之后对分段进行 70 Hz 低通滤波(IIR Butterworth,四阶;EEGLAB ‘pop_basicfilter’),并将参考重置为 TP9–TP10 的平均。最后,在第二次伪迹剔除后,将数据重新分段为 −200 至 400 ms,基线校正区间为 TMS 脉冲前 −200 至 −2 ms,转换为 FieldTrip 结构并在试次上求平均。每位受试者每个实验条件分别独立预处理。各条件下 ICA、SSP-SIR 成分数量及被剔除伪迹分段的平均数见补充表 1。
为计算 M1-TEP 各峰在关注条件中的峰值振幅与潜伏期,我们选取了 M1 刺激常见的六个 TEP 成分:N15、P30、N45、P60、N100 与 P180(Beck et al. 2024;Farzan and Bortoletto 2022)。P15(Bortoletto et al. 2021;Zazio et al. 2022)在原研究(Guidali et al. 2023)中已分析,本研究不再考虑。对每个峰,我们进行如下步骤:首先查阅文献确定每个 TEP 成分通常测量的时间窗(例如 Belardinelli et al. 2021;Farzan et al. 2013;Gordon et al. 2021;Rogasch and Fitzgerald 2013;Zazio et al. 2021)。随后在我们的总体大平均(将所有条件合并)中验证该时间窗内确有信号偏转,并重新定义时间区间以避免与相邻 TEP 峰的时间窗重叠。之后,将与每个 TEP 成分峰值位置对应的 4 个电极的信号取平均(类似于 Guidali et al. 2023),并在所有受试者各实验条件下计算其振幅与潜伏期。各 M1-TEP 成分所选时间窗与电极见表 1。
表1 六个提取的 M1-TEP 成分的关注时间(TOI)与关注区域(ROI)。
微状态分析
为进行微状态分析,我们使用基于 MATLAB 的 Randomization Graphical User 软件(RAGU;Koenig et al. 2011),遵循既往文献指南(Habermann et al. 2018;Koenig et al. 2014)。首先将 EEG 下采样至 960 Hz。加载六个关注条件的数据(PA 单相、AP 单相、LM 单相、PA 双相、AP 双相、LM 双相)后,软件采用基于受试者间马氏距离的算法检测到 5 个离群个体(Wilks, 1961),并将其排除。我们设定被试内实验设计包含两个因素(电流方向、脉冲波形),随机化 5000 次,显著性水平 p = 0.05。分析前,将各受试者平均数据按全局场功率(GFP)归一化,以在尽量减少 TEP 振幅差异带来的影响的同时,检测头皮层面源空间分布的差异(Habermann et al. 2018)。最后,我们在刺激后 5–400 ms 的 TEP 数据中检验地形一致性与微状态。
各条件总体平均 TEP 的 GFP(全局场功率) 与零分布比较以执行地形一致性检验。该零分布通过随机打乱个体平均 TEP 的通道位置(得到随机地形图)并重复计算 5000 次平均 GFP 构建(Habermann et al. 2018)。
为确定微状态最优地图数,我们使用 Koenig 等(2014)提出的交叉验证方法,迭代 50 次。每一步将数据集随机分为学习集与测试集:学习集建立类别数从 3 到 12 的微状态模型,测试集用于验证类别并确定各模型解释的方差量(更多细节见 Koenig et al. 2014;Sulcova et al. 2022)。交叉验证结果提示本数据可由 6 个微状态类别得到最佳解释,因为 6 地图模型是第一个达到全局解释方差平台值的模型。我们使用 k-means 聚类(250 次迭代)将 TEP 分割为由 6 张不同头皮地形图定义的微状态。在每次迭代中,将所有条件的组平均数据拼接,从中随机选取 6 个头皮地形图作为初始模板,用与每个数据点相关性最高的地形图对该点标注类别;随后对同一类别标注的数据点求平均以更新模板;最终保留全局解释方差最高的一组模板地图。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的统计显著性阈值设为 p < 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mANOVAs)与协方差分析(ANCOVAs)使用 Jamovi(2.6 版;The Jamovi Project 2025);稳健 ANOVAs 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使用 R Studio(1.2.5019 版;R Core Team 2019),并调用 ‘WRS2’(Mair and Wilcox 2020)与 ‘lme4’(Bates 2018)包。
经颅磁诱发电位(TEPs)
对于每一个 TEP 成分,我们将振幅和/或潜伏期数值超过组均值 ±2.5 个标准差的受试者视为离群值并从分析中排除(范围 3–5;更多信息见补充表 2)。我们分别对每个 TEP 峰的潜伏期与振幅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mANOVAs),因素为“脉冲波形”(单相、双相)与“电流方向”(PA、AP、LM)。随后,为检验 TMS 强度对峰值振幅调制可能的贡献,我们对每一种脉冲波形分别进行协方差分析(ANCOVAs),因素为“电流方向”(PA、AP、LM),并将对应区块的 TMS 强度数值作为协变量。数据球形性用 Mauchly 检验评估;若不满足,则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事后检验采用 Tukey 多重比较校正。rmANOVA 的效应量报告偏 η²(ƞp²),t 检验的效应量报告 Cohen’s d。
我们对每个变量检查数据分布的正态性;如有需要,进行(a)平方根、(b)以 10 为底的对数、以及(c)倒数变换,以寻找使分布更接近正态的变换方式(与 Guidali et al. 2023 相同流程)。P60 的振幅分布通过以 10 为底的对数变换实现正态化。对于 P30、N45、P60、N100 与 P180 成分的潜伏期,上述变换均无效;因此,我们分别对单相与双相两种波形,基于截尾均值(截尾比例 20%)对三种电流方向(AP、PA、LM)在原始数据上执行稳健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Mair and Wilcox 2020)。
微状态(Microstates)
作为初步分析,我们先进行地形一致性检验,以验证各条件中是否存在一致的地形图。随后,为了具体检验 TMS 参数是否调制微状态特征,我们对每一个由微状态提取得到的类别(见 2.5)分别分析:(i)曲线下面积(AUC)——即该微状态被检测到的每个时间点上的 GFP 振幅之和;以及(ii)持续时间——即该微状态出现的所有时间点之和。分析采用一系列“脉冲波形 × 电流方向”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mANOVAs),与 TEP 指标相同(见上一段)。微状态持续时间呈正态分布;而我们计划的变换均无法使微状态 AUC 数据更接近正态,因此该变量采用一系列稳健 rmANOVAs(Mair and Wilcox 2020),方法同上。
此外,我们还进一步探讨不同刺激是否激活不同回路。为此,我们通过观察不同条件下微状态出现顺序来考察反应的时空模式是否改变。考虑到不同地形图代表不同皮层源的激活,从一个微状态到另一个微状态的转换序列若发生变化,很可能反映了不同回路的招募。因此,我们分析微状态起始(onset)值,即某一微状态类别首次出现的时间点,并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amma 分布,恒等链接)。将“微状态类别”(1–6)、“刺激条件”(单相 PA、单相 AP、单相 LM、双相 PA、双相 AP、双相 LM)及其交互项作为固定效应,被试作为随机效应。事后检验用 Benjamini–Hochberg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鉴于该分析目的,在事后比较中我们仅关注同一刺激条件内不同微状态类别之间的对比,特别关注两类微状态在不同刺激条件间出现顺序发生互换的情况。
结果
TEP 峰(TEP Peaks)
各刺激条件的 TEP 总体平均波形与各成分的地形图见图 2。M1-TEP 峰的时间序列及相关地形图与既往刺激运动皮层的 TMS-EEG 文献一致(综述见 Beck et al. 2024;Farzan and Bortoletto 2022)。在我们各实验条件之间,最显著的视觉差异主要出现在 TMS 脉冲后最初 50 ms:单相波形在不同电流方向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地形图模式,其中 AP 电流呈现最强的早期成分。
图2:所有条件的 TEP 总体平均及各成分的地形图。各成分的具体时间区间见表 1。地形图电压刻度随成分而变,见下方图例。
六种实验条件下 M1-TEP 成分振幅与潜伏期的均值(M)与标准误(SE)见表 2。
表2:六种实验条件下 M1-TEP 成分振幅与潜伏期的均值与标准误。
振幅(Amplitude)
总体而言,所有六个 TEP 峰的振幅均受到刺激参数的显著调制,并呈现“电流方向 × 脉冲波形”的交互效应(所有 rmANOVA 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见补充表 3)。
具体而言,N15 的事后比较(F₂,₅₆ = 26.53,p < .001,ƞp² = 0.487)显示:单相 AP 产生最大的(即更负的)振幅,而单相 PA 产生最小的 N15。后一条件在所分析电极中表现为缺乏负向成分(显著事后比较见表 3;图 3a)。
表3:TEP 峰振幅的显著事后比较(Tukey 校正)。
图3 六个实验区块中 N15(a)、P30(b)、N45(c)、P60(d)、N100(e)和 P180(f)成分的幅度。
在箱线图中,红色点和红色线表示分布的均值;中间的横线表示其中位数。黑色点和灰色线表示个体数据。箱体表示数据的第 25 至第 75 百分位数范围。须线延伸至最大观测值,该值位于第一/第三四分位数 1.5 倍四分位距之内;校正后的事后比较显著性 p 值以符号标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对于 P30(F₁.₆₅,₄₆.₁₁ = 11.37,p < .001,ƞp² = 0.289),事后检验显示:双相 LM (外侧—内侧)电流产生最小的 P30,且与所有其他刺激条件均显著不同。在双相波形内部,PA 方向诱发的 P30 振幅低于 AP 方向(图 3b)。
对于 N45(F₁.₅₉,₄₄.₅₄ = 35.98,p < .001,ƞp² = 0.562),事后比较显示:单相 AP 诱发的 N45 在所有条件中“最不负”(负向幅度最小);并且对单个受试者分布的观察(图 3c)提示该条件下 N45 极性变异很大。相反,另外两种单相条件(单相 PA 与单相 LM)诱发的 N45 比三种双相条件都更负(图 3c)。
对于 P60(F₁.₃₂,₃₄.₄ = 5.286,p = .008,ƞp² = 0.168),单相 PA 电流诱发的振幅高于对应的双相 PA。进一步地,两种 LM(外侧—内侧)方向诱发的 P60 显著小于单相 PA 与双相 AP(图 3d)。
对于 N100(F₂,₅₆ = 22.06,p < .001,ƞp² = 0.441),单相 AP 诱发的振幅比另外两种单相条件以及双相 PA 更负。相反,单相 PA 诱发的成分比对应的双相 PA 以及双相 LM 更不负。单相 LM 呈现与单相 PA 类似的模式——即相对于对应的双相 LM 与双相 AP,其 N100 更不负(图 3e)。
对于 P180(F₁.₅₆,₄₃.₆₅ = 19.7,p < .001,ƞp² = 0.413),事后比较显示:单相 AP 诱发的 P180 在五个其他条件中最高。与此同时,单相 LM 产生的振幅低于三种双相波形;单相 PA 诱发的 P180 小于双相 AP(图 3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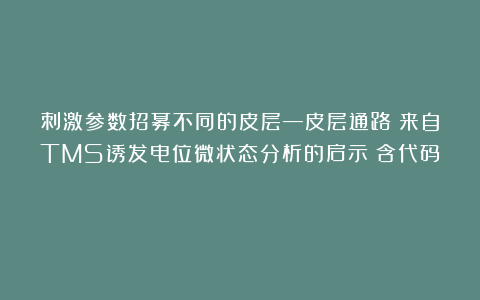
最后,为检验刺激强度对峰值振幅调制的可能贡献而进行的 ANCOVAs 显示:TMS 强度仅对 P180 成分有显著影响,且在单相(F₁,₈₃ = 14.97,p < .001,ƞp² = 0.153)与双相(F₁,₈₃ = 9.33,p = .003,ƞp² = 0.101)均成立。有趣的是,在双相刺激中,在控制 TMS 强度后,“电流方向”的净效应不显著(F₂,₈₃ = 1.88,p = .16,ƞp² = 0.043),提示双相条件中观察到的振幅差异主要由刺激强度差异驱动。相反,对于单相波形,“电流方向”(F₂,₈₃ = 3.94,p = .023,ƞp² = 0.087)仍然显著;事后比较显示 AP 诱发的振幅显著高于 LM(t₈₃ = 2.8,p = .019,d = 1.34),与主分析结果一致。
对其余五个成分,TMS 强度的贡献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所有 F < 3.12,所有 p > 0.081)。
潜伏期(Latency)
就潜伏期而言,只有 N15 与 P60 显示显著调制(所有 rmANOVA 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见补充表 4)。
N15 存在显著调制,并呈现“电流方向 × 脉冲波形”的交互效应(F₂,₅₆ = 10.39,p < .001,ƞp² = 0.271)。事后比较显示:单相 AP 的 N15 潜伏期显著短于另外两种单相条件(相对单相 PA:t = −5.4,p < .001,d = −0.98;相对单相 LM:t = −4.4,p = .002,d = −0.81)以及双相 LM(t = −3.4,p = .022,d = −0.63)。同时,单相 PA 与单相 LM 的潜伏期显著长于双相 PA(相对单相 PA:t = −4.4,p = .002,d = −0.81;相对单相 LM:t = −3.4,p = .023,d = −0.63)以及双相 AP(相对单相 PA:t = −3.6,p = .013,d = −0.67;相对单相 LM:t = −3.1,p = .047,d = −0.57;图 4a)。
图4 六个实验区块中 N15(a)、P30(b)、N45(c)、P60(d)、N100(e)和 P180(f)成分的潜伏期。
在箱线图中,红色圆点和红色线条表示分布的均值;中间的横线表示其中位数;黑色圆点和灰色线条表示个体数据。箱体表示数据的第 25–75 百分位范围。须线延伸至落在第一/第三四分位数 1.5 倍四分位距以内的最大观测值;校正后的事后比较显著性 p 值标注为(* = p < .05;** = p < .01;*** = p < .001)。
此外,单相脉冲条件下记录到的 P60 潜伏期受到电流方向的调制(F₁.₆₅,₂₆.₄₈ = 5.57,p = .013)。具体而言,LM 方向电流诱发的 P60 潜伏期显著长于 PA 方向(ψ = 0.003,p = .012;见图 4d)。
其余四个成分的潜伏期不随所采用的电流方向或脉冲波形而发生显著差异(所有 F < 2.56,所有 p > 0.092;见图 4)。
微状态分析(Microstate Analysis)
拓扑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时间点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性。鉴于所有条件下均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后续微状态分析纳入整个时间窗(0–400 ms)(补充图 4)。
所采用的 6 类微状态模型 共解释了 91.34% 的总方差。对微状态序列的目视检查显示,六种微状态在每一种刺激条件下均有出现。然而,不同条件之间在微状态的出现顺序与时序分布上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 TMS 后前 50 ms。在较晚的潜伏期,仅 单相 AP 条件 相较其他条件表现出不同的微状态序列,其特征为 缺失以前额–中央电极区正向电位为主的微状态图(即第 5 类)。总体而言,单相 AP 条件相较其他条件呈现出 最为不同的模式,在刺激后前 100 ms 内出现了 7 个微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 刺激后 100–250 ms(即 N100 与 P180 时间窗)期间,该条件表现为 左侧感觉运动电极区负向信号(第 6 类)和右额区正向信号(第 3 类)持续时间更长(见图 5)。
图5 微状态分析结果。上排:6 类已识别微状态的模板拓扑图。主体部分:在所有刺激条件下,模型能够解释的信号方差比例根据在各时间段占主导地位的微状态类别进行着色。与特定 TEP 成分对应的时间窗以该成分所对应的颜色进行标示。
对微状态参数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定量地刻画上述模式。六类微状态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 AUC、持续时间和起始时间的均值(M)及标准误(SE) 列于 表 4。
表4 六种实验条件下,各微状态类别的 AUC、持续时间和起始时间的均值(M)与标准误(SE)
微状态 AUC
AUC 的变化仅出现在单相刺激条件之间,提示微状态在不同电流方向下对信号的主导程度或解释量不同(所有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见补充表 5)。
第 1 类微状态(F₁.₉₈,₃₁.₇₃ = 22.40,p < .001)在 AP 条件下的 AUC 显著低于另外两种条件(PA:ψ = −102.11,p < .001;LM:ψ = −68.76,p < .001),且 LM 条件下的 AUC 亦低于 PA 条件(ψ = −26.94,p < .001;见图 6a)。
第 3 类(F₁.₀₉,₁₇.₃₇ = 20.68,p < .001)和 第 6 类(F₁.₂₆,₂₀.₁₆ = 0.26,p < .001)则呈现出 相反的调制模式:在这两类微状态中,AP 电流诱发的 AUC 显著大于 PA(第 3 类:ψ = 189.49,p = .025;第 6 类:ψ = 112.97,p = .003)以及 LM 条件(第 3 类:ψ = 184.04,p < .001;第 6 类:ψ = 117.68,p = .002;见图 6c、6e、6f)。
图6 六种刺激条件下,各微状态类别的 AUC
箱线图中,红色圆点和线条表示分布均值;中线表示中位数;黑色圆点和灰色线条表示个体数据;箱体为第 25–75 百分位;须线延伸至位于 1.5 倍四分位距内的最大观测值;校正后的事后比较显著性以符号标注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对于其余三类微状态以及所有 双相刺激条件,均未发现统计学显著效应(所有 F < 2.56,所有 p > 0.092;见图 6)。
微状态持续时间(Microstate Duration)
微状态持续时间的结果与 AUC 的发现一致(所有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见补充表 6)。在 第 1、3 和 6 类微状态 中观察到显著的 “脉冲波形 × 电流方向”交互效应。
第 1 类(F₁.₅₉,₄₁.₂₇ = 16.3,p < .001,ƞp² = 0.39):单相 AP 条件下的微状态持续时间显著短于另外两种单相条件及其对应的双相条件;此外,单相 PA 与 LM 电流诱发的微状态持续时间长于三种双相条件(见表 5;图 7a)。
第 3 类(F₂,₅₂ = 18.3,p < .001,ƞp² = 0.41)呈现与第 1 类 相反的模式:单相 AP 条件下的微状态持续时间显著长于单相 PA 与 LM 条件,而后两者又短于三种双相条件;此外,单相 AP 条件下第 3 类微状态的持续时间 长于双相 PA 与 LM 条件,提示该电流方向在除同源双相条件外诱发了 最长的第 3 类微状态(见图 7c)。
第 6 类:单相 AP 条件下的持续时间长于另外两种单相条件,而 单相 PA 条件的持续时间显著短于双相 AP 与 LM 条件(见图 7f)。
表5 微状态持续时间的显著事后比较结果(Tukey 校正)
图7 六种刺激条件下,各微状态类别的微状态持续时间。
在箱线图中,红色点和红色线表示分布的均值;中间的横线表示其中位数。黑色点和灰色线表示个体数据。箱体表示数据的第 25 至第 75 百分位数范围。须线延伸至最大观测值,该值位于第一/第三四分位数 1.5 倍四分位距之内;校正后的事后比较显著性 p 值以符号标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对于 第 4 类,发现显著的 “脉冲波形”主效应:无论电流方向如何,单相波形下的微状态持续时间均短于双相波形(F₁,₂₆ = 11.7,p = .002,ƞp² = 0.31;见图 7d)。
最后,第 2 类与第 5 类 未发现显著差异(所有 F < 1.8,所有 p > 0.176;见图 7)。
微状态出现顺序(Microstate Order of Appearance)
微状态起始时间分析显示,“微状态类别”存在显著主效应(χ²₅ = 82.91,p < .001),同时 “微状态类别 × 刺激条件”交互效应亦显著(χ²₂₅ = 141.54,p < .001)。具体而言,该交互效应反映了不同条件下 微状态出现顺序的改变,在不同刺激条件之间共观察到四种显著的微状态顺序反转。
这些微状态起始顺序的交换 不应被解释为某一既有神经过程发生时间的简单提前或延后(例如,一个通常出现在晚期潜伏期的神经过程不太可能突然出现在最早阶段,反之亦然)。相反,更可能的解释是 具有相同拓扑特征的新神经过程在更早时间出现。这些顺序交换表明,不同条件下微状态之间的转变并不遵循相同的顺序,提示 参与了不同的皮层环路。
首先,在 双相 AP 与单相 AP 条件 之间观察到两类微状态的顺序交换:在双相 AP 条件下,第 4 类与第 5 类的起始显著早于第 6 类(第 4 类 vs 第 6 类:p = .023;第 5 类 vs 第 6 类:p = .006);而在单相 AP 条件下,顺序发生反转,第 4 类与第 5 类出现在第 6 类之后(第 4 类 vs 第 6 类:p = .003;第 5 类 vs 第 6 类:p = .013)。
随后,在 单相条件 中,第 1、3 和 6 类 的相对顺序发生反转:在单相 AP 条件下,第 3 类与第 6 类显著早于第 1 类出现(第 1 类 vs 第 3 类:p = .004;第 1 类 vs 第 6 类:p < .001);而在单相 LM 与 PA 条件 中,第 1 类则先于第 3 类(LM:p < .001;PA:p < .001)和第 6 类(LM:p = .003;PA:p < .001;见图 8)。
图8 (a) 六个实验区块中六类微状态的平均起始时间,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b) 不同刺激条件下微状态起始类别的时间序列。不同条件间微状态出现顺序的显著交换以符号标注(*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所有 微状态起始时间的显著差异(包括未涉及顺序交换的比较)列于 表 6。
表6 各刺激条件内微状态类别起始时间的显著事后比较。
以粗体标出的对比表示在不同刺激条件之间涉及出现顺序交换的比较。所报告的 p 值均采用 Benjamini–Hochberg 方法 对多重比较进行校正,共考虑 90 个对比(6 种刺激条件 × 每条件下 15 种类别对比)。
讨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操控 TMS 参数会在受刺激网络内诱发不同皮层通路的激活,从而导致对刺激反应的变异性。在我们的刺激条件中可以观察到相同的 M1-TEP 成分与微状态拓扑图,但其时空模式不同,揭示了对 M1 信号传播的调制;这种调制在单相脉冲条件下较双相脉冲更为显著。
TMS 脉冲波形与电流方向影响与 M1 相关的皮层环路募集
综合 TEP 数据在幅度、潜伏期与拓扑分布方面的总体模式,首先一个显著证据是:与双相波形相比,单相波形会影响所有被分析的 M1-TEP 成分的幅度。同时,双相刺激仅在少数成分(即 P30 与 P60)上表现出不同电流方向之间的变化。鉴于单相脉冲只有一个能够导致神经元被刺激的相位,而双相脉冲具有两个在生理上有效的相位,并且第二个相位在神经元兴奋方面比第一个相位更有效(例如 Corthout et al. 2001;Groppa et al. 2012;Maccabee et al. 1998),因此这种模式并不令人意外。由此,单相脉冲会使被刺激神经元群体具有更高的方向特异性(Sommer et al. 2018),从而可能比双相脉冲更容易激活更为选择性的环路。
在这方面,微状态结果尤具信息量,因为它描绘了皮层活动的时空分布。与 TEP 的模式类似,微状态参数中不同电流方向之间的差异在单相条件下比在双相条件下更为明显,提示在单相刺激条件之间,皮层环路募集的改变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对微状态持续时间与 AUC 的分析显示,与双相波形相比,单相波形引起更大的调制;在第 1、3 和 6 类微状态中,AP 方向与 PA 和 LM 方向存在显著差异。对微状态起始时间(onset)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证据:类别出现顺序的反转主要仅出现在单相条件之内,并且发生在那些表现出 AUC 与持续时间调制的微状态上。也就是说,在 AP 刺激中,第 1 类的出现显著晚于第 3 类与第 6 类;而在 PA 与 LM 刺激中则呈现相反模式(即第 1 类早于第 3 类与第 6 类出现)。就同源电流方向而言,仅 单相 vs 双相的 AP 方向显示出微状态顺序的统计学显著变化:在单相 AP 刺激中,第 6 类先于第 4 类与第 5 类出现,而在双相 AP 中则后于它们出现。本研究结果指出,AP 方向也是在不同脉冲波形之间激活出最不相同网络图谱的方向。如前所述,这些微状态顺序的交换更可能指向具有相似拓扑的新神经过程的出现,而非既有过程发生时间的改变。因此,从一个微状态到另一个微状态的转变序列发生变化,很可能反映了皮层环路参与方式的不同。总体而言,这些证据提示:使用双相波形会从 M1 诱发更为广泛的活动,反映了某些皮层网络的贡献;而这些网络在单相波形下可能只有在采用特定电流方向时才会被选择性激活。
从整体 TEP 模式中得到的另一个结果是:我们的实验操控对 TEP 幅度的影响比对其潜伏期的影响更为显著,提示跨神经元网络的传播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受 TMS 参数影响(但参见既往关于 N15 以及此前报道的 P15 的效应,例如 Guidali et al. 2023;Bonato et al. 2006)。
最后,TMS 参数似乎对更早期的 TEP 成分影响更大,这与先前研究显示技术参数调制主要出现在早期皮层反应上的发现一致(Bonato et al. 2006;Casula et al. 2018)。具体而言,在我们的样本中,许多受试者表现出 N15、P30 与 N45 成分的极性反转或缺失,而较晚期的峰值仅表现为幅度调制。微状态类别的整体继替模式也凸显了这一点:在 TMS 后前 50 ms 内,不同条件之间(尤其是不同单相条件之间)出现了显著的调制。
综上,这些结果提示:当采用不同的 TMS 参数时,会激活不同的皮层环路,和/或以不同程度参与相似的皮层环路。
单相前-后向电流在最初 50 ms 内最大化募集不同的运动环路
如前所述,单相 AP 条件在 TEP 峰值与微状态参数上相较其他所有实验条件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第 6 类与第 3 类拓扑——它们代表单相 AP 刺激后 TMS 之后最先出现的微状态——在刺激部位下方表现为显著负向。该拓扑反映了 N15 成分,被认为揭示了与刺激同侧的感觉运动区与运动前区的激活(Farzan and Bortoletto 2022)。此外,第 3 类在对侧感觉运动电极上表现为正向,类似于与对侧 M1 胼胝体抑制相关的早期成分(M1-P15;Bortoletto et al. 2021;Zazio et al. 2022)。既往发现显示,单相 AP 脉冲诱发的 M1-P15 幅度更高(Guidali et al. 2023)。如果说 N15 的幅度与潜伏期告诉我们,单相 AP 是能够更有效、更快速地募集相关神经元群体的条件,那么微状态分析则提示该条件与其他单相脉冲相比激活了不同的皮层环路,这体现在 TMS 后前 50 ms 内不同的 EEG 拓扑分布上。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单相 AP 脉冲优先募集同侧及皮层-皮层的运动相关神经元群体。第 1 类的调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模式:第 1 类微状态在单相 AP 刺激中表现为最短持续时间与最低 AUC,并且表征了单相 LM (外侧—内侧)与 PA 条件下的最早期反应。其拓扑在刺激部位呈正向、在对侧额-中央电极呈负向,与 N45 的拓扑高度相似;而 N45 又恰恰是在单相 AP 刺激后显著降低的唯一 TEP 成分。
既往文献提示,在刺激 M1 时,PA 与 AP 两种电流方向会导致空间选择性的改变(例如 Aberra et al. 2020;Siebner et al. 2022;Spampinato 2020),我们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证据。一般认为,AP 电流方向会使 TMS 诱发电场最大幅度的位置向前移动,因此相较于 PA(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相较于 LM)电流方向,会刺激中央前回中更前方位置的神经元(Aberra et al. 2020)。中央前回的吻侧神经元与更高阶运动区(例如辅助运动区)的互联程度高于尾侧神经元(Spampinato 2020)。因此,AP 电流方向可比 PA 与 LM 更有效地刺激高阶运动神经元群体,从而导致 M1 激活的传播方式不同。除了更好地激活中央前回的吻侧部分外,既往采用重复与成对脉冲 TMS 的研究还指出:AP 电流更有效地刺激 M1 的浅层(即 L2/3),而 PA 与 LM 电流更容易到达深层(即 L5)(例如 Casarotto et al. 2023;Koch et al. 2013;Sommer et al. 2013)。有趣的是,动物模型研究强调,负责皮层-皮层通讯与网络范围激活的 M1 中间神经元在运动皮层浅层比在深层更为丰富;而深层则以直接激活锥体束的神经元群体为主(例如 Harris and Shepherd 2015;Mao et al. 2011;Weiler et al. 2008)。因此,AP 刺激可能更有效地直接激活皮层-皮层神经元,进而激活与 M1 在结构上相互连接的皮层区域;我们的微状态与 TEP 结果支持了这一点。
与抑制性与兴奋性环路相关的 M1-TEP 成分的调制
与抑制性与兴奋性环路相关的 TEP 成分的调制模式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个证据:TMS 参数会在 M1 刺激后调节皮层环路的募集。就负向成分而言,不同的药理学研究提示 N45 与 N100 与 γ-氨基丁酸(GABA)相关环路有关(Darmani and Ziemann 2019;Premoli, Castellanos, Premoli et al. 2014a,b)。其中,N45 与由 GABA-A 受体介导的抑制过程相关(Belardinelli et al. 2021;Cash et al. 2017;Darmani et al. 2016),而 N100 与 GABA-B 相关(Premoli et al. 2018;Premoli, Rivolta, Premoli et al. 2014a,b;Rogasch et al. 2013)。我们的结果显示,与 PA 与 LM 相比,单相 AP 诱发的 N45 幅度最低,但 N100 幅度最高。这可能意味着,当采用单相波形时,AP 与 PA/LM 方向能够以不同程度激活皮层环路,从而允许对 GABA-A 介导(后者)或 GABA-B 介导(前者)通路进行选择性调制。鉴于许多临床障碍(例如阿尔茨海默病、重性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Heaney and Kinney 2016;Luscher et al. 2011)的不同阶段或特定症状与 GABA 能功能障碍相关,进一步检验这种可能性在临床应用上将极为有价值。
不同条件下观察到的正向 TEP 成分差异则更难直接解释。P30 被认为反映了多皮层源参与的兴奋性活动(Farzan and Bortoletto 2022),并与 MEP 幅度有关(Ahn and Fröhlich 2021;Mäki and Ilmoniemi 2010)。有趣的是,既往研究显示,内-外侧(medial-lateral)方向是诱发 MEP 效率最低的方向之一(例如 Mills et al. 1992;Souza et al. 2018)。因此,当以双相脉冲采用外-内侧(lateral-medial)电流方向时,可能影响 M1 的皮层反应性,从而导致我们在 P30 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
P60 也出现了类似结果,其中 LM(外侧—内侧)仍是总体上诱发较小成分的电流方向。既往 TMS-EEG 文献将 P60 幅度与 MEP 的感觉运动回传(sensorimotor reafference)的皮层加工联系起来(Mäki and Ilmoniemi 2010;Petrichella et al. 2017)。关键的是,与 TEP 的发现相反,在本数据集中记录到的 MEP 幅度在不同刺激条件之间并无差异(见 Guidali et al. 2023 与补充图 2)。因此,P60 的模式可能更多反映了肌肉回传加工(例如 PA 与 AP 方向之间无差异)与皮层-皮层活动(例如 LM 效率较低)交织在一起的效应。
最后,考虑到与直接刺激 M1 并非严格相关的皮层过程的贡献,我们考察的最晚期成分 P180 是唯一一个在两种脉冲波形下都显示出 TMS 强度显著贡献的成分。这与当前文献一致:文献强调与 TMS 相关的听觉与躯体感觉输入对该成分具有贡献,而其活动主要位于颞顶区(Biabani et al. 2019;Conde et al. 2019)。确实,可以合理推测,在我们的受试者中,单相 AP 刺激所需更高的刺激强度在头皮上引起了更强的躯体感觉以及更响的 TMS 噪声(即“咔嗒声”——我们的白噪声无法完全掩蔽),从而导致更强的躯体感觉与听觉诱发电位。
需要指出的是,TEP 成分与 TMS 相关感觉输入之间的关系此前已在 60 ms 之后出现的峰值中得到证明(Biabani et al. 2019;Niessen et al. 2021)。尽管我们的数据未显示刺激强度对 P60 与 N100 成分的作用,也未显示不同刺激条件下对 TMS 相关感觉的主观感知存在差异(见补充图 3),我们仍无法完全排除其受到听觉与躯体感觉加工污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更早期成分(即 N15、P30、N45)的调制模式可能更为“干净”,因为它们不太会受到与 TMS 相关的多感觉加工影响。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需要考虑的局限。首先,若能为每一种刺激条件设置一个 sham(伪)区块,将有助于分离并去除反映 TMS 诱发外周伪迹的反应,从而更好地区分在较晚期 TEP 成分上观察到的模式。然而,在原始研究(Guidali et al. 2023)中实施这些控制对参与者而言负担很大,且超出其研究目的。未来研究可专门聚焦感觉混杂因素在本研究发现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深化。其次,使用两台不同刺激器可能引入与单相与双相条件所采用设备不同相关的混杂因素(分别为 Magstim 2002 与 Magstim Rapid2)。未来研究应采用能够同时输出单相与双相脉冲的刺激器,从而纳入并控制该潜在偏倚。此外,既往研究强调,改变电流方向与脉冲波形会影响诱发 MEP 的最佳热点(Stephani et al. 2016;Kammer et al. 2001)。在本研究中,我们在不同条件间保持刺激位置不变,以避免由于线圈位置变化而进一步增加 TEP 变异性。然而,未来有必要研究:根据不同刺激参数选择最优刺激点会如何影响 TEP。就微状态而言,其特征显示出较高的个体间变异(见图 6 与图 7)。将微状态分析应用于 TMS-EEG 数据是一个新兴但前景可期的研究领域。未来研究应更深入解析支撑 TMS 诱发微状态拓扑的皮层源,并将其与特定 TEP 成分相联系(例如 Sulcova et al. 2022),类似于 ERP 微状态研究中的做法(例如 Schiller et al. 2024;Tarailis et al. 2024)。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本研究的微状态结果。基于此,我们对脑网络调制的结论需要谨慎解读(例如 Kleinert et al. 2024)。此外,除我们考察的参数之外,其他 TMS 参数(例如 TMS 脉冲宽度)也会影响大脑对刺激的反应(Casula et al. 2018),未来应将其与本文所述参数结合纳入研究。最后,刺激强度基于受试者的静息运动阈值(rMT):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控制所有条件都诱发相同的皮质脊髓活动;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确保不同条件之间具有可比的皮层反应性。
因此,未来的 TMS-EEG 研究应仔细考虑 TMS 参数,以便可靠地将 TEP 用作生物标志物。扩展此类知识有助于优化用于调节或影响运动系统皮层-皮层连接性的 TMS 调制方案,从而更好地靶向特定神经通路/环路,尤其是在这些方案用于临床场景时(Guidali et al. 2021a,b;Hernandez-Pavon et al. 2023a)。此外,鉴于我们在传感器层面获得的有希望结果,源空间层面的连接性分析可能进一步深化本研究发现,超越微状态分析所能提供的信息。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研究也可扩展到其他皮层区域(例如背外侧前额叶、下顶叶小叶),这些区域已知在神经精神障碍中发挥关键作用(Cao et al. 2021;Farzan 2024)。
结论
总之,本研究强调了 TMS 参数在 TEP 调制及其变异性中的关键作用,提示不同的皮层环路与网络会根据所选择的电流方向与脉冲波形而被募集。总体而言,双相刺激允许改变线圈取向而不显著影响诱发反应;而单相刺激有助于获得更高的刺激选择性,这也得到了其他 TMS 研究的支持(例如 Fong et al. 2021;Hamada et al. 2014;Pieramico et al. 2023;Sale et al. 2016)。关键的是,与其他所采用条件相比,AP 电流方向引出了最不相同的时空模式。因此,根据研究目的必须谨慎选择最合适的 TMS 参数,因为当 TMS-EEG 被使用时,它们是一个重要的变异来源。结合将微状态分析应用于 TMS-EEG 数据的研究(Ding et al. 2024;Sulcova et al. 2022),我们的结果提示,微状态分析可在传感器层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可能与仅考察诱发反应幅度与潜伏期所得信息互补,从而帮助推断不同皮层环路的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