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四姐妹
张婉茹
我们鲁桥五渠岸张家兄弟姐妹六人,长兄今年93岁,大姐91岁,我88岁,三妹85岁,最小的小妹也73了。三年前,我们兄妹六人难得在故乡三原鲁桥镇相聚、合影。
2022年12月11日三妹夫去世后,在深圳看孙子的小妹马上让儿子到石家庄把三姨妈接了过去,住在距儿子5站路的锦绣花园小区。次年3月11日,小妹又陪三妹回石家庄炼油厂,协助三妹给三妹夫买了墓地,在纪念堂做了百日祭祀奠仪。4月19日,小妹又陪三妹回到咸阳我的家里。
我第一眼看见三妹就惊呆了,头上乌黑的波浪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薄薄稀疏的白发,头皮都看得见,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右手也颤抖着。我的心碎了,我极力控制住在眼眶滚动的泪珠,我用力把它咽到肚里。接过右手摇摆的提包,进家洗尘、休息。4月29日,大姐的儿子陈琦接我和三妹回三原团聚,车还没到姐家巷口,大姐和小妹己快步走到车前,接我们下车,拉手拍肩交谈,讲离别的思念,道各自的变化。
(六十年代初的全家福,左一是小妹)
进到姐家,我们姐妹四人围着茶几坐下喝着茶,说着话伸出了四双大手。我们的父母手都大,所以我们的手比一般人的手也都大。大家的手指大都有些弯曲了,大姐有八个手指都弯了,关节还肥大,我有两个手指弯了。最小的小妹有二个手指也弯曲了,因小妹刚会干活时家里入了社,就开始在地里干农活。只有三妹三妹是双福手,两只大手伸展开,十个指头端端正正、绵绵柔软,一碰都能滴水似得。三她被妹夫疼爱了一辈子,从没干过粗重活。
入农业社时三妹己到西安石油学校读书了,三妹夫是她上学时的班长,山东人直爽又热情。后来我外尧尧说他在同济大学上学时当班长,我祝贺他,他反而说,当班长就是当保姆。所以三妹夫一直就是三妹的保姆。刚结婚时有善良勤劳的婆母,下班回到家三妹炕上一坐,三妹夫把饭端上炕桌,三妹一吃就休息。婆母归天后,妹夫接着做保姆。妹夫的正作后来是几千人的厂工会主席,下班后就兼职做三妹的保姆,退休后更是成了专职保姆。他曾说做饭有趣,他还能做几样拿手好菜,妹只会当下手,洗洗刷刷。三妹夫有能力、有毅力,坚强,豁达,健谈。在五年病魔折摩中,他抗挣、奋斗,忍受了各种痛苦,有一丝气力,他还坚持做饭。直到2022年12月11日,在家中寿终正寝。
三妹夫的去世我们都很悲痛。三妹更是悲伤欲绝,三妹夫走了,三妹的天塌下来了!三妹的支柱倒了!三妹家的顶梁支柱倒了!三妹的精神几近崩垮了!在这节骨眼中,在深圳的小妹让儿子在次年元月8日,亲自把姨妈接到深圳,住在距外甥5站路的锦绣花园小区。小妹每天过去和三妹做晚饭,吃饭后陪三妹过夜。用亲情冲淡三妹亡夫的悲哀,化解三妹60年日积月累的夫妻情,用亲缘热血温暖凝结成冰的心。
每天早上5点小妹起床,坐两站地铁、三站公交到儿子家,和小妹夫分别送孙子上学、上幼儿园。中午在儿子家做饭、接孙女,下午又返回三妹住处,陪三妹吃完晚饭后姐妹促膝长谈,三妹在繁华的现代化的城市里,无心观景,而在小妹精心细微的感化下,渡过了人生最痛心、最苦涩的两个月。小妹对我们三个姐姐尽心尽力,有时比儿女超过许多。像我家老梁在2020年元月16日去世,小妹冐着新冠疫情,不顾我们的谢绝,元月18日就乘机来咸。当天咸阳阴霾蔽日,飞机无法降,飞到成都过夜,元月19日到咸,陪我住了20天才返深圳。
小妹夫退休后在三原开了个五金水暖店,那时大姐夫有肺气肿、糖尿病,不时住院,一住院小妹就把店门关了,小妹夫和大姐轮流在医院陪侍姐夫,小妹买莱送饭。一次我回去看姐夫,姐的大儿子也回来了,看到小姨父倒尿盆,赶忙接着尿盆说:“咋能叫我姨父倒盆子呢?”因他在外地工作多年,姐绝对不会让儿子请假侍候父母,这条张家无文的家规,也隨大姐出嫁带到了陈家。
姐夫喜欢看电视,小妹就买了个便携电视送到医院。当年我和三妹在外地工作,不常回家,没有给父母床前行孝,都是大姐、姐夫代我们给父母身边进孝、养老送终,我们从心底感激不尽。父母归天后我们回老家就常住大姐家,姐夫对我们如亲兄妹。姐常对我们说:“做任何事不管有多少困难,你放开干,一定能成功。”这就是大姐的人生哲理。
大姐解放前没进过学校,1952姐才正式上学。从没进过学校的姐直接报考高小,就考了第七名。初中我们一起报考三原县女中,姐还是考的第七名。
我们小时都受到严格的家教,饱读诗书的爷爷教给我们传统文化和做人的论理道德。姐每天做完家务,晚上就跟爷爷学古书,爷爷那时教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女儿经》《朱子家训》等,每天教几句。爷爷念一句,姐跟着念一句、再反复念。觉得背过了,姐就到妈房子炕头的板柜上写大字,写完爷爷批示,好的吃个红丸子(圈),错的打个红叉。我们都睡了,姐还在那写,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上炕睡觉,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就没有姐上炕睡觉。
我们姐妹四人团聚也不容易,因小妹懂事后,我三个都在县城住校上学,工作后我和三妹都在外地,退休后大家更是分居四处。
今天我四姐妹团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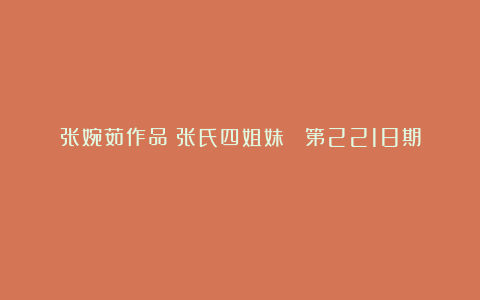
四个白发老姐妹,三个听力差,说话像吵架,放开嗓门喊,天南海北聊,深圳、桂林、新加波,日本,美国、加拿大,青年、童年,念书、拾棉花,说的话一串串地不间断,小妹一看时间12点都过了,我们才收拾休息。
第二天外甥带我们去看了郑国渠,大地原点。结果排了半天队都没看上。顺路参观了陕西水利博物馆,里面有个人体含水测量器,我们都站上去测了自己,结果都比标准64%低。我们认真看了李仪址对陕西水利事业的贡献,知道了关中有“八惠渠”,了解了几千年来前人先贤前赴后继的水利事业。
我们上了崇文塔。以前很早就知道有个泾阳塔,今天才知它的真名叫“崇文塔”,是我国现存的最高的砖塔之一。崇文塔始建于公元1591年(明万历年间),高81点218米,一共十三层,八边楼阁式,系当时的吏部尚书李世达为倡导各县学童努力向学而建的,故名崇文塔,塔身挺拔而俊秀,堪称地方一美景。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崇文景区被评定为AAA旅游区。
我们仔细的看了简介后,在外甥陈琦导游下,大姐前头走,小妹后头护,走进了黑古隆咚的崇文塔,塔里伸手不见五指,用手摸到台阶,很陡、很高、很黑,但很向往,我一步跷上一个台阶很费劲,我们就脚手并用,边爬边数,爬到了第二层才见了亮光。塔外壁有个小窗子,透进来一束光,塔身上一个个小窑孔里敬着观音菩萨和各路神仙,前面香烟缭绕,有游人敬献的糕点水果,一张张人民币。
我们向上攀登着,外甥鼓励我们说:“上,想上多少就上多少。”现在有亮了,我们站了起来,但还是得手脚并用,左手扶塔身,右手爬台阶,我们八十多岁的心,焕发出年轻人的热血,冲激着老姐妹四的心,我们想登上塔顶,我们要上到塔尖,我们也一定能上到顶上。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一层层的攀登,一圈圈的转,台阶宽度大约也就一人宽点,所以对面来了人,就得侧着身子上下,往往是别人给我们让路,好心的游客还不时地伸出手掺我们一把,不断有人给我四个竖起大拇指,我们更是心花努放,不能自己。特别有一对父子,小男孩很可爱,六七岁的样子,可个头很高,白白胖胖,总是走在我们前后,不时地伸出温暖的手帮你,就连那小孩都用那绵绵的小手扶我。
我们一步步数着台阶,看着所标塔层,10层、11层、12、13、14层,我们终于上到塔顶了。送给我们的大拇指就更多了,我们都怀抱满满的大拇指,我们登上了中国最高的古砖塔。除大姐外,我们都是第一次上崇文塔,有88岁大姐的榜样,我们腰不弯,背不鸵,气不喘,又说又笑登上了十四层高的崇文塔。
我们体会到了心情舒畅,走地更欢快了,上塔容易下塔也就不那么难了。上十四层、下十四层,一古脑双脚都走完,四姐妹回到家仍然到零点后才入眠。四姐妹聚会的日日夜夜,总有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我一进大姐的客厅,左边的书桌上,翻开的是《中国党史人物传》第26册,姐一册一册连续看,己看到了26册。茶几上还摆着《老年报》,上面用铅笔勾着,一问她像读课文一样,一课不漏的学,学过的就用笔勾画了;小茶几上还放着“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是小儿子给她的,听说在大姐的熏陶下,她的孙子也在读毛选。
大姐自豪地说,我很满足,在咱们鲁桥伍渠岸上,我十几个伙伴,姐掐着指头,一个个数,一名名算,王女、赵爱、杨芳梅、吴芳兰……从南到北、从渠东到渠西,近20个人,我们夹着识字课本,上夜校,上妇女班,上医务班,一起敲锣打鼓扭映歌,可现在回头看,仔细想,四姐妹都走出来的就咱一家。是的,不是姐夸口,不说在伍渠岸,就是在全鲁桥镇,像我们在当年那样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所有子女都坚持上学的家,也是找不到的。
54年我姐妹三个在三原县女中上学时,许多同学都以为我们是殷实之家,其实我们八囗人之家只有父亲一人四乡沿街推着独轮车卖点针线袜帽,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就不错了。父亲勤俭持家,从牙缝里挤出点钱,除大姐外,我们都适龄上了学。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位饱学诗书的爷爷,他放弃了在周至大商号管账先生的优厚待遇,回来帮助父亲持家,每天拾粪、烧锅,用高标准的中国优秀道德文化教育我们。爷爷和父亲给我们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故事,爷爷教我们古书。大姐在学校只念了五年书,后来几十年在三原县城获得优秀校长称号,是和扎实的家教分不开的。
我们姐妹四人,要发扬自己的长处,以健康为本,以书为伴,不忘入党誓言,严格要求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向中国11万百岁老人队伍进军,学习,奋斗!
2022年,耄耋之年六兄妹再聚首,
左起小妹、大姐、大哥、笔者、三妹、二弟
作者张婉茹:张婉茹,1937年生,陕西三原鲁桥人。196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数学系,一生从教,教授过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学生,后从咸阳师范学院退休。退休后闲暇之间阅读、写作,有作品发表于《三秦都市报》《当代女报》《咸阳师范学院校报》《嵕山》《石岗书院》《美丽八点半》《满天都是星》等媒体。有文集《宛如书印》行世。
子 非 堂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