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憨叫王有田,但村里没人叫他大名。叫他老憨,一是因为人实在,二是因为确实有点“憨”。
老憨三十岁那年,说话还打卷说不利索。村里人问他:“有田,吃了吗?”他就咧着嘴笑,露出两排黄牙:“嘿嘿,吃了,吃了。”再问吃的啥,他就掰着手指头数:“馍,菜,汤……”数完三样,没了。其实他娘做了四样菜。
老憨爹死得早,娘把他拉扯大。他有力气,两百斤的麻袋扛起来就走,但就是脑子转得慢。村里人都说:“这娃可惜了,一身力气,就是缺个心眼。”
老憨娘最愁的不是这个,是儿子的婚事。谁家姑娘愿意嫁个“憨子”?眼看老憨三十五了,还打着光棍。
那年腊月,村里来了个外乡女人,叫周巧云。说是逃荒来的,父母都饿死在路上了。巧云长得清秀,手也巧,会裁衣、会绣花、会做一桌子好菜。更难得的是识文断字——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稀罕事。
村里好几个后生动了心思,托媒人去说。巧云一个没应。
老憨娘也动了心思,但没敢去说。倒是巧云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天雪下得大,巧云敲开老憨家的门,头发上都是雪珠子。她问老憨娘:“大娘,听说您家还缺个做饭的?”
老憨娘愣了:“闺女,你这是……”
“我想嫁有田哥。”巧云说得平静,像说“今天雪真大”一样自然。
全村都炸了锅。
婚礼办得简单,三桌酒席,来的都是近邻。洞房那晚,村里几个后生扒墙根,想听听巧云会不会哭。
他们听见巧云在说话,声音轻得像棉花:“有田哥,从今往后,我给你做饭,给你洗衣,给你缝一辈子衣裳。”
老憨还是那样:“嘿嘿,好,好。”
第二天天不亮,巧云就起来了。她把老憨家三间土房收拾得亮亮堂堂,破了的窗户纸全换了新的,糊得平平整整。院里那口老井,辘轳坏了多少年,她让老憨修好,自己摇上来第一桶水,清了半个院子的雪。
老憨只会笑,跟在巧云身后,让干啥就干啥。
村里人都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了巧云这闺女。”
这话传到巧云耳朵里,她也不恼,只笑笑:“牛粪养花哩。”
日子一天天过。老憨还是那个老憨,巧云却让村里人开了眼。
她教老憨认秤——老憨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从前卖东西只会说“一块”“五毛”,现在能算清楚账了。
她教老憨种地——老憨有力气但没章法,巧云从娘家带来本《农事通》,照着书上的法子,教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老憨家的地,收成总比别家好一成。
最绝的是那年夏天,乡里来了收购药材的贩子,说要收柴胡。村里人漫山遍野地挖,挖来都是寻常货色。巧云却带着老憨往深山里走,专找背阴的崖壁——那里的柴胡长得慢,药性足。一季下来,老憨家卖了别人三倍的价钱。
村里人这才咂摸出味儿来:老憨不是真憨,是缺个人点拨。
但老憨也有犯浑的时候。
那年儿子出生,取名叫“盼聪”。巧云坐月子,老憨笨手笨脚地伺候。孩子夜里哭,他抱起来满屋走,边走边念叨:“莫哭莫哭,爹在哩。”那声音温柔得,让隔壁偷听的刘婶都红了眼。
盼聪三岁时,发了场高烧。村卫生所看不好,得送县医院。偏偏那天大雨,山路冲垮了一段。老憨背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往乡里赶——乡里有车去县城。
巧云跟在后面,雨大得睁不开眼。走到断路口,水已经齐腰深了。老憨把孩子交给巧云,自己跳进水里探路。一个浪头打来,他被冲出去两三米,幸亏抓住棵小树。
巧云在岸上哭喊:“有田!回来!咱想别的法子!”
老憨抹了把脸,水顺着头发往下淌。他回过头,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神色:“不行,娃等不起。”
他硬是蹚出一条路,把娘俩背过了河。到了乡卫生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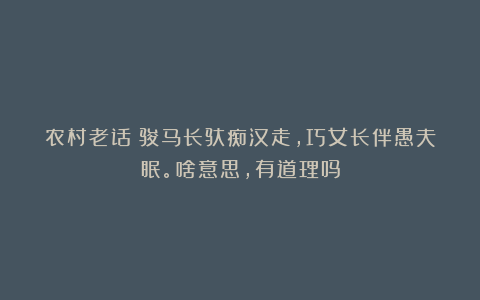
那天晚上,在医院走廊里,巧云握着老憨的手。老憨的手上全是口子,被水泡得发白。
“你咋那么傻?”巧云哭着说。
老憨还是那句话:“嘿嘿,没事,没事。”
如今,老憨五十多了,儿子盼聪大学毕业,在城里工作。村里早就通了公路,老憨买了辆小货车,给村里人拉货。巧云坐在副驾上,手里永远捧本书。
村里人也早就不说“鲜花牛粪”的话了。倒是张四爷常拿他俩举例子:“看见没?老憨是匹马,有力气,肯出力,但得有人牵着缰绳。巧云就是那个牵缰绳的人。”
刘婶现在也说:“什么痴汉愚夫?人家老憨心里明镜似的。巧云选他,那是慧眼识珠哩。”
那天傍晚,老憨的车停在了老枣树下。巧云先下来,手里提着个布包。老憨从车上搬下来两袋化肥——是给刘婶家捎的。
“有田哥,歇会儿吧。”巧云递过水壶。
老憨接过,咕咚咕咚喝了几口,额头上的汗在夕阳下亮晶晶的。
张四爷磕磕烟锅,慢悠悠地说:“老憨啊,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巧云。”
老憨看着巧云,笑了。这次他没说“嘿嘿”,而是清清楚楚地说:“我知道。”
巧云也笑了,眼角皱纹像朵菊花。
月亮上来了,照着村道上回家的两个人影。老憨走在前面,巧云跟在后面,两个人隔着一米远——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不远不近,不紧不慢。
张四爷还坐在老枣树下,对刘婶说:“瞧见没?骏马长驮痴汉走——老憨是马,驮着巧云走过了半辈子风雨。巧女长伴愚夫眠——巧云是巧女,陪着老憨睡过了三十年安稳觉。”
刘婶点点头,又摇摇头:“四爷,您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咋说?”
“骏马不痴,痴的是外人看不懂。巧女不愚,愚的是外人看不透。”
四爷愣了愣,然后笑了:“说得好,说得好啊!”
月光下,老憨和巧云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村道尽头,传来老憨哼的小调,不成曲,不成调,但欢欢实实的,像秋收后打谷场上的连枷声,一下,一下,夯实了日子。
那晚,巧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世人笑他痴,我知他心实;世人叹我愚,我乐此中足。”
老憨不识字,但他知道巧云在写东西。他烧了洗脚水,端到床前:“洗脚,睡觉。”
洗脚水热气腾腾的,像他们这半辈子的日子,不沸腾,但始终是温的。
总之,这句老话更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去: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性不公与个人命运的无奈。
警示现在:提醒我们婚姻应建立在互相欣赏、共同成长的基础上,而非外在条件的简单匹配。
启迪未来:真正的“配”不是外人眼中的“骏马配英雄”,而是两人能否在岁月中彼此成全、相濡以沫。
正如农村老人常说的:“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评的。”表面的“错配”,内里可能是外人看不懂的踏实与温暖。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