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出电梯,就在看电视的老人们中间寻找父亲。
只见父亲穿着法兰绒拉链外套,瘫坐在轮椅上,轮椅被锁在长桌上。不用问,他这几天肯定让人不省心,不是整夜整夜不睡,到处乱走,就是发脾气闹人。
父亲一眼就看了我,问:你回来啦?
我愣了一下,赶紧说:爸,我回来了。
这次离开白城没有告诉父亲,他一定时时找我们。我哥和小莎、无牙和抱抱分别去看他,他肯定不停念叨。他们也一定告诉父亲我和巫森去辽宁了。所以,父亲盼我回来,一定望眼欲穿,就像我小时候在前郭旗姥姥家,天天趴在窗台上,盼父亲来接我回家一样。
我把父亲推回房间,想让兽兽陪姥爷多待一会。
父亲一眼就看到了早就进了房间的兽兽,大声喊他,高兴坏了。
父亲坐到床上,开始不停说话。除了问我们啥时候回来的,就是念叨不想打针了。
巫森说:爸,打针有效果,你看你啥啥都明白了。
父亲说:我都一百来岁了,打啥针?死就死。花那钱嘎哈?没用。我都跟她们辩论了,非说姑爷让打的。姑爷让打针也不行啊,我都一百来岁了。谁能活这么大岁数啊?
说话时,父亲嘴唇颤抖,但眼神明亮,表情丰富,嘴也不那么歪了。
巫森问:爸,今天打针了吗?
父亲说:不打!不打!我让她们把钱退回来。也别说心疼钱,那不带劲。就是岁数大了,打针没用。
看来父亲打针的确有效果,知道心疼钱了。
巫森适时转移话题,问父亲,无牙老丈人来没来。
父亲说:来了,坐小车来的。
小莎父母、我公公婆婆都已过世,父亲的亲家亲家母只有抱抱的父母了。家有掸子群里实时播报了这场人生暮年的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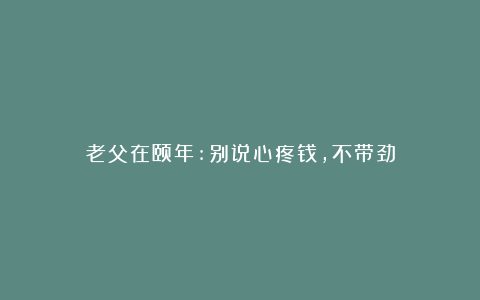
抱抱父母都年过八旬,身体健朗,能劳动,比父亲身体强太多。
不过,人老了身体能啥样,也不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父亲如此光景,我们已不知有多感恩。
我开抽屉拿人参蜜片,看到大家给父亲预备的纸巾。三种纸巾,来自三个儿女家。父亲总淌鼻涕,流眼泪,纸巾消耗量巨大。
我打开冰箱放月饼,看到里面早有一盒月饼。拆开包装盒,露出一块切成八小块的五仁月饼,看上去是抱抱的手笔。老年人不能多吃月饼,一次吃八分之一块,不会造成消化不良,也不影响吃正餐。
父亲夸我身体恢复得好。他臆想中我的那场病,终于在我一次次到来中痊愈。我又故意蹦蹦跳跳,不遗余力扮可爱。一时,房间成了我的舞台,父亲就继续夸我带劲。
父亲又说:得告诉老贲,咱们也不是不打针,打两针就够了。
看来我们受老贲启发让父亲打针,父亲都明白。
这时,护理员把晚餐送来了。我端起碗,准备喂父亲,担心烫,用小勺搅动着。
父亲却说:我不吃,不饿。他指着餐盘说:巫森,你吃。又指指饭碗,说:然,你吃。
我们告诉父亲,一会出去和朋友吃火锅,父亲才不再坚持,把一碗小米粥、两只玉米饼和炒菜都吃掉了。
掉到衣襟上的玉米饼渣,父亲都仔细捡起来吃掉。
海兵过来问饭菜够不够,父亲对她说:你是学医的,你不也不打针吗?我不打了。
海兵问我:一个疗程就差一针了,姥爷还打不打了?
我无奈地说:他不让打,那就只好不打了。
林语堂说:“在中国文化中,老年不意味着退场,而是’登台’。一位年长者,是一个家族的镇山之石。他不需发号施令,他的沉默本身就是命令。”
接到父亲如此执拗的命令,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父亲再衰老糊涂,再让人不省心,也是我们的“镇山之石”。我知道,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儿女三家,就可以一次次扑奔而去。一个父亲,定然有强大的磁力,一次次把儿女们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