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都知道我是谁
古城路的车流不算挤,却总让人心里发急。回昆山的路走了无数遍,那天瞥见路边“南港” 的路牌,忽然生出念头 —— 再去南巷走走,看看它如今的模样。
车驶过大桥,左手边见一座石拱桥,便想着这应该就是南港的老模样了。停车,寻着桥而去,没走多远,便是一座石拱桥。此桥不是那种玲珑秀气的小桥,桥面宽宽的,桥身用厚重的石块砌成,接缝处爬着暗绿色的青苔,像汉子胳膊上暴起的青筋。桥栏被岁月磨得光滑,指尖摸上去,能感觉到石头的凉和细微的纹路。它就那样稳稳地架在河面上,跨度不算小,弧度却很沉稳,不像江南女子的腰肢,倒像个常年劳作的粗壮汉子,敦实、有力,莫名就让人觉得很性感—— 是那种不加修饰的、带着生命力的性感。
站在桥上向西望了望,河水清清的,映着桥的影子,还有岸边老房子的飞檐。老街为东市街,河南与河北分别以上塘和下塘街区分。上下塘街基本少有人居住,只有零星的几房半开着门,好像还有老人咳嗽的声音,混着风吹过杂草的沙沙声,在空荡的街巷里飘得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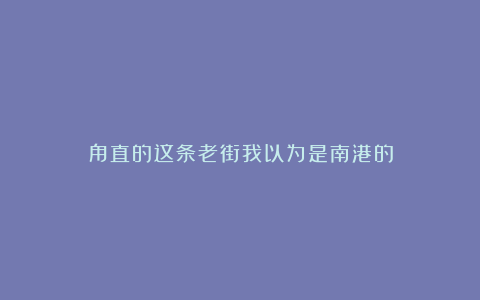
街确实是老街,脚下的路均是弹石,这在江南古镇已不多见,好处是雨停即路面干,坏处是走着却不舒服,尤其不宜穿高跟鞋。透过半塌的院墙,能看见里面倒塌的房梁,朽坏的木头泡在潮湿的泥地里,长出了白色的霉斑。巷子里的杂草快齐腰深,茎秆带着韧劲,刮过裤腿有些发痒。有户人家的门框还立着,砖雕的门楣虽已风化,却能看出当年的精致纹样,墙角堆着半截破损的木窗棂,上面的雕花还隐约可见,想来当年这该是户殷实人家。
原以为因南巷的撤并,而被人遗忘,正在叹息之间,一位牵着狗的老人从巷口走来。我上前搭话,老人笑着摆手:“这条街是甪直,南港没有老街。” 原来我搞错了,以前就总把南港和甪直弄混,私心里总觉得南港该也有这样的老街,查了才知,东市街分东段和西段,西段已被甪直打造成了历史文化街,而我那天走过的就是正阳桥至华阳桥东段的新市街,也是甪直的地界。感叹甪直古镇真的很大,单是眼前这段老街,就比许多古镇藏着更多过往的痕迹:深深浅浅的巷子纵横交错,高大的门楼带着岁月的沧桑,河上连着好几座古老的石桥,每一座都刻着不同的纹路。
老街还残留着更多烟火气的余温。沿街的老店铺门面排得整齐,深褐色的门板有的脱了漆,露出里面的木头纹理,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有一家门框上还钉着半截褪色的招牌,字迹模糊,勉强能认出“秤” 字。倒塌的房子里,半埋在杂草中的陶盆磕着缺口,盆底还留着些许泥土,该是以前主人种花草用的;墙角的榫卯木梁虽已朽坏,却还能想见当年工匠的手艺。
其实仔细想想,这样的冷落从来不是偶然。以前水路是命脉,河岸边的老街靠着商船兴盛起来,家家户户依河而居,做着买卖、过着日子,河面上的船桨声、街巷里的叫卖声,凑成最鲜活的烟火气。可后来公路修起来了,汽车代替了船只,新城区的高楼拔地而起,水电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人们自然愿意搬到更舒适的地方。年轻人带着孩子离开了,老人们慢慢老去,老房子没人修缮,漏雨、倒塌,杂草趁机蔓延,老街便渐渐沉寂下来。让一条街活起来容易些,让整个古镇活起来似乎有些难度。不然,当初甪直不会只保护和发展了半段东市街。
也许,这便是历史长河里最自然的法则。就像草木枯荣、四季更替,古镇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兴盛时,它是人们生活的舞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沉寂时,它就成了历史的印记,默默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不用为它可惜,它的荒芜不是被抛弃,而是自然的选择—— 当新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当便利的现代文明覆盖了古老的烟火,这些老街便顺着时光的河流,归于沉寂。
就像这座石拱桥,不管街上人来人往还是冷清寂寥,它都稳稳地架在河上,看着河水东流,看着青苔爬满石缝,看着老街从热闹到沉静。这便是最从容的真相:没有永恒的繁华,也没有永恒的荒芜,一切都是岁月的自然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