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报道:
黄功吾的自白
我的哥哥是美联社的一名摄影记者,非常敬业、努力。那时,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但他在报道越南战争(美越战争)时不幸遇难。
之后,我也进入了美联社,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我的哥哥。我的上司、西贡分社的摄影总监霍斯特·法斯(Horst Faas)接纳了我,让我跟着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记者、摄影记者学习,包括戴夫·伯内特(Dave Burnett)、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等人。
他们告诉我如何带着同情心工作,如何展现客观真相,如何创作出能够帮助边缘人的作品,如何通过我的影像改善人类的境况。
从16岁起,我就在西贡及其周边地区学习摄影多年。1972年6月8日,凝固汽油弹投向Trang Bang村的一群平民,我有幸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并捕捉到了现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标志性画面:在凝固汽油弹投下来后,潘金淑和她的家人从燃烧的建筑中跑了出来。当时,还有其他记者和我在一起,包括我的见证人戴夫·伯内特、彼得·阿内特和《纽约时报》的福克斯·巴特菲尔德。
《战火中的女孩》未裁切的原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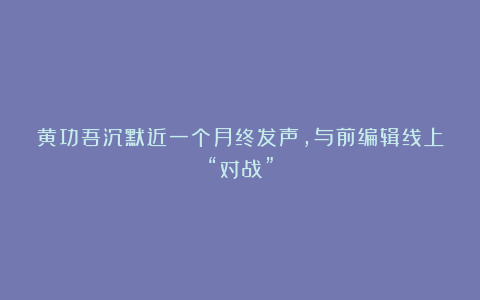
经过一番周折,我的老板法斯将这幅照片公之于众,并为我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许多其他荣誉。这张照片帮助结束了越南的战争。
50多年后的今天,我不明白当时在西贡的美联社同事卡尔·罗宾逊先生为什么要编造故事,说我没有拍摄《战火中的女孩》这张照片。
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罗宾逊先生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呢?在我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公布当天,罗宾逊先生就站在我身旁为我庆祝。现在,一些关键的证人和能够指控他说谎的人都去世之后,他才站出来。
左一的卡尔·罗宾逊(Carl Robinson)拿着香槟祝贺黄功吾(中,正对镜头)凭借《战火中的女孩》获得普利策奖,旁边还有邓文福(Dang Van Phuoc)、理查德·派尔(Richard Pyle)和霍斯特·法斯(Horst Faas)。
在我看来,罗宾逊先生现在的行为,是打了所有记录越战历史的人一记耳光。
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说我的照片不是我的,也从来没有人就我的照片与我对质,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战火中的女孩》是一个“特约记者”的照片。
当时,所有胶片在冲洗前都会被贴上标签,标上每个人的姓名,并通过标签与信封上的摄影师姓名进行比对。美联社西贡分社在底片归属问题上是万无一失的。
潘金淑的照片是我拍的,当天一些其他的照片,也是我拍的。没有人有权利说那张照片或其他的照片不是我拍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是我所做的工作的创造者。我的职业生涯长达50多年,虽然我现在已经从美联社退休,但我仍在继续创作具有影响力的图片,供世人欣赏。
我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罗宾逊的连续“轰炸”
那张著名的照片不是黄功吾拍摄的。当时,我是美联社的一名图片编辑,我正准备在照片上署名,给特约记者署名。我的上司法斯凑到我的耳旁,命令我:“黄功吾,写上黄功吾。”
我照做了。我把黄功吾的名字写在了照片上。虽然我已经查过,照片不是他拍的,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我愤然辞去美国政府的工作,和我的妻子留在越南。1968年,法斯给了我这份工作,他开启了我的新闻生涯。那时我和我的妻子有两个孩子要抚养。我怎么能辞职呢?我甚至没有争辩。
最终编发的图片(左下)由原始图片剪裁而成。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当资深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走上前去,向错愕的黄功吾表示祝贺时,我完全不高兴了。我把一位同事叫到外面,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能这么做?”另外,黄功吾唯一一次见到那个小女孩潘金淑是在他第二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真相。
后来,在我看到另一张现场照片时,我确信了,真正的摄影师,是右边穿白衣黑背心、手持相机的男子。这张图片显示的是潘金淑和其他孩子刚刚跑过两个摄制组。
视觉中国图片库中的一张照片显示——当时,有多位记者拿起相机记录这一场景。照片中显示,当天现场确实存在一位白衣黑背心的男子拿着相机。
去年,在巴黎,《特约记者》的制作团队找了一个调查团队,分析了那天在Trang Bang村外的多张照片和镜头。调查团队的3D重建和时间线显示,当潘金淑从村庄里出来的时候,黄功吾并不在第一梯队新闻工作者的队伍里。美联社的调查报告中黄功吾拍摄的其他照片也显示他在更远的地方。
纪录片《The Stringer(特约记者)》的海报。
这个调查团队得出的结论是,黄功吾极不可能拍摄了《战火中的女孩》,真正的拍摄者可能是第一梯队记者中的另一位摄影师——那个特约记者确实就在摄影师应该在的位置,这样他才能拍下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