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近70年间爆发了近千场的教案,甚至义和团运动都是教案引发的。
传教士早在元朝就已经进入中国,不过当时的传教士的数量很少,也没有产生太大社会影响,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不过当时并没有与中国的老百姓产生矛盾与冲突。雍正皇帝禁教后,除了少数俄国传教士可以在北京及京畿地区有限活动外,其他的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都被禁止了。
近代以降,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里面规定了西方传教士可以在华自由传教,因而传教士开始一批一批进入中国。不过与前两次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所不同的是,晚清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引发了一系列民教冲突的“教案”,近代在华传教士当中,又可以分为天主教和新教,其中最容易与中国老百姓产生矛盾的是天主教,而新教几乎很少出现所谓的“教案”问题,并且近代中国很多政要和社会知名人士都是新教徒。这一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
近代的教案始于1842年的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的陕西教案,期间比较著名的教案包括天津教案、南昌教案等等,教案在19世纪末期形成高潮,但是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教案开始迅速减少以至于最终消失,这与西方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传教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南昌教案
宗教从一开始的传播思想,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游戏,而负责传播思想的传教士,也逐渐沦为杀人工具。
惨案背景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名叫利玛窦的洋人天主教徒来到清朝,开始在清朝传播宗教思想。到清朝中后期,外国的宗教已经在清朝遍地生花。
华夏大地向来富饶,黄金白银遍地,但无能的清政府却只会躺着享乐。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不反抗,反而还被逼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随着西方国家在清朝的话语权越来越盛,西方的宗教也跟着水涨船高,一时间风头无限。自西方国家在清朝有了地位之后,这些宗教也跟着西方国家政府的身后吃着红利,尤其是这些所谓的传教士。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在全国重要城市广设教堂,广收信众。为了扩建教堂,这些传教士不惜占用民间百姓的田产。这些传教士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在民间极力蛊惑清朝百姓入教。其中有不少当地的地痞流氓,整日好吃懒做,在天主教徒的鼓吹下加入天主教。
南昌教案伊始
在江西一带,一眼望去,竟遍地都是天主教堂和天主教信徒。这些教徒整日无事可做,便变着法的欺压百姓。
这些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全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叫王安之的人给他们撑腰。这个王安之,虽然起了个汉人名字,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王安之在教中地位极高,教众对他极为推崇。自清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王安之的洋人身份更显得特别。而王安之之所以这么嚣张,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法国政府兜底。在他的纵容下,这些教徒在当地成了地头蛇一样的存在。
这些教徒仗着洋人的势,处处欺压自己的同胞,还以此为荣,百姓苦不堪言,但迫于压力,只好忍气吞声,见到他们都绕道而行。生怕一个不小心惹到他们。百姓的一再容忍,让这些教徒变本加厉,尤其是在江西新昌棠浦镇一带。这些教徒强抢民女,还公然殴打百姓致死。民间有一龚姓青年得知后,便为百姓打抱不平,将这些为非作歹的天主教徒挨个教训了个遍。但也因此和天主教结下了梁子。
王安之得知以后,觉得面上无光,便打算报复。他一纸诉状递到了当地县衙。打算利用官府镇压当地百姓。在当时,洋人很有话语权,各地官员有样学样,向洋人摆尾乞怜,处处讨好。王安之便是利用了这一点。当地县衙迫于西方列强的威压,不敢替百姓做主,只能由着这些教徒为非作歹。还下令逮捕了这个龚姓青年。
尘世肮脏违心愿
民间风气至此,致使民怨沸腾,当地百姓揭竿而起,准备反抗。王安之看到百姓的举动,便向法国政府说明要求出兵,还放下豪言,要血洗棠浦镇。
当地百姓听闻后,怕牵连无辜,便差人请来了素有“民间包青天”称号的南昌知县江召棠。江召棠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慨。他快马加鞭,来到棠浦镇。出面调解此事。在江召棠的调解下,百姓才免于灾祸。江召棠秉公执法,坚决要严惩犯人。将犯罪的天主教徒一并抓获,收押候审。
但江召棠此举却引来了王安之的记恨。原本王安之想利用洋人的影响力左右江召棠,但他没想到江召棠如此正直,为了保护了当地百姓,不惜得罪洋人政府。
惨案发生
王安之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报复江召棠,随着南昌总教的教主去世,让王安之有了可乘之机。王安之接替了南昌教主的位子,和江召棠开始了正面交锋。
王安之接替教主后不久,教内便发生了命案,江召棠依法来逮捕犯人,但王安之却拒不交人。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王安之见江召棠没有丝毫大事化小的态度,心里便起了歪招。王安之以调解为由,邀请江召棠来到家中做客。江召棠虽然心中存疑,但还是应邀前往。却江召棠没想到,这一去,将会断送自己的性命!
江召棠带着两名随从来到王安之家中,刚一进门,王安之便派人将江召棠的随从扣押,还将江召棠强行押入屋内,让江召棠重判当初棠浦镇的案件。爱民如子的江召棠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求,王安之见况,便掏出凶器威胁江召棠。面对如此场面,江召棠面不改色,不卑不亢。威胁不成,恼羞成怒的王安之便持凶器猛然刺入江召棠的咽喉,江召棠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
事后,王安之将凶器隐藏,又再一次恶人先告状,找上了江西巡抚,还告诉江西巡抚,江召棠是自刎。江西巡抚赶到时,江召棠还未断气,他临死前,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江召棠还以为清政府会为他洗刷冤屈,但没想到在他死后,王安之伙同法国政府,拒不认罪,还在报纸上声明,将此事推得一干二净。
事情发生后,法国政府为包庇王安之,竟然派出军舰威胁清政府。一向怯懦的清政府迫于威压,只能和法国又签订了友好条约。清政府不仅释放了犯人,还将行侠仗义的民间百姓收押。甚至赔偿给法国政府45万两白银。杀人者不伏诛,受害者却成了罪人。此等冤屈闻所未闻。民间百姓纷纷站出来为江召棠喊冤,但清政府却充耳不闻。
法国政府堂而皇之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抹去,只有当地的百姓和当初的验尸报告,证明江召棠是死于非命。江召棠的死,是无能清政府的损失,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缩影。当时的清政府,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吞噬殆尽。
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庇护下的肆行宣教活动,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缓刑4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49万两。天津教案使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舆论上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成为慈禧的替罪羊。
天津望海楼教堂
事件背景
清同治八年(1869年),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事件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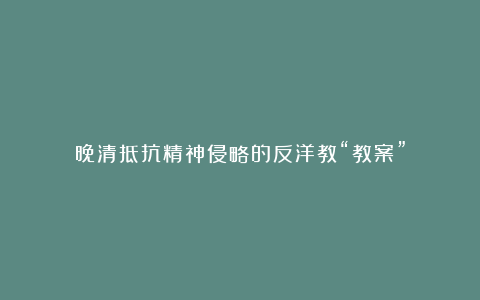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端午前后,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收养的中国幼孩因病毒流行,突然大批死亡,先后达数十人,葬于河东荒野。其中有一棺二、三尸者,有尸身无目、胸腹洞开、失去脏器者。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家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五月初八日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当时民情汹汹,既疑法国教堂虐杀儿童,复疑迷拐幼童之事与其有关。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只好将另外二名拐犯张拴、郭拐迅速审结正法,并宣称崇厚要去之人并非拐犯,以解众疑。自此人心稍安,浮议渐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县官不敢深究,且以河东前葬幼孩多棺,终觉怀疑莫释。
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
事件经过
五月二十日,复有乡民抓住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作为拐犯送至官府,到堂后供认:“伊系赵州宁晋人,帮人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并供称:“王三系天津口音,脸上有白麻。有天津人开药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白麻。则迷药之得自王三,似非虚捏。”此供于被获之时,他已告知乡民,因此刚经送案,而城乡四境早已哄传天主堂真有用药迷人之事。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感到左右为难:事涉教堂,势难穷追到底;而消息走漏,民情汹汹,又势难置之不问。于是,拿着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请示办理之法。张光藻以为事关教堂,如何办理应由崇厚决定。崇厚亦以为社会压力太大,势难不为查办,遂令天津道周家勋往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质对。该领事同意查问有无此人。
不料丰大业中途变卦。次日晨,崇厚令刘杰前往询问时,被丰大业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自往见丰大业。丰大业初推不管,继乃令天主堂主持人谢福音查问。谢福音将王三密匿堂内,诡称堂中并无此人。崇厚等无奈,只好放下王三不管,仅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巳时由天津道员周家勋率同府、县官员,带犯赴教堂指认门径。结果,堂内并无栅栏、天棚,与供情不符。天津地方官感到此案已无法再查下去,遂带犯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天津地方官员离开之后,仍有不少人在天主堂门外围观,见教民出入,齐声喝好讥诮。堂内杂役出扭一人发辫殴打。于是,双方发生争斗。法国天主堂离三口通商衙门甚近。谢福音派人告知崇厚,崇厚当即令两巡捕前去弹压。巡捕到后,众人均已敛手。这时,忽有堂内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丰大业闻声而出,持鞭将巡捕乱打,口称“尔宫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等语。两巡捕跑回告知崇厚,崇厚复令一名军官前往。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各执利刃洋枪,揪住这名军官的发辫,一同去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即放一枪。崇厚逃向内室,丰大业即将屋内器具砸毁。经众巡捕将丰大业劝住,崇厚复出相见。丰大业又放一枪,大肆咆哮,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崇厚向其周旋,他竟不理,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其时,纷传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前与法国人开仗,各水会鸣锣聚众,前往救援。人们满面怒容,手执刀枪,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而各处仍在鸣锣,水会会众塞满街巷,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向这里涌来。崇厚怕乱中出事,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丰大业更怒,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于是走出,崇厚只好派两名军官护送其回天主堂。两旁民众执刀怒视,却不敢动手,且纷纷后移,给丰大业让出通道,令其通行。丰大业行至浮桥,与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刘杰劝其暂回三口通商衙门。丰大业突然向刘杰开枪,打伤跟丁高升。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打死,随即奔往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遇害者有20名外国人(10名修女、2名神父、丰大业、西蒙、刚从法国来的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专员多玛三及其新婚妻子、法国商人夏玛桑及其妻子,以及一名叫普罗特波波夫的俄国商人及其妻子)和30多名中国信徒,多数房屋被烧毁,从天主堂救出中国人10名,从仁慈堂救出中国人150名,在天主堂内搜获拐匪教民王三,在教堂门前抓获拐犯教民安三。
事件结果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以法国为首。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并准备以一命抵一命的原则处死20人,但反对法方处死天津知府、知县的要求。八月以后,法国仍坚持杀天津府县才能了解此案,并不惜以开战相威胁。就在此期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清廷让曾国藩补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李鸿章补直隶总督。中法双方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 (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缓刑4人(余下四名,原为照抵被杀俄人性命,因俄国领事孔令再三要求缓办,遂拖下未执行),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 ,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历史影响
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国藩是极力揣摩清廷处置意图,但清廷一方面畏敌如虎,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不可能既持平处理又维护国权;另一方面清廷又怕过分屈从洋人会激起民愤,危及自己的统治。其态度随着外国的干涉不断变化。因此,曾国藩无法准确揣摩清廷的意图,更不可能有既为列强接受、又不致引起民愤的办法。其实李鸿章在最后也基本是按照曾国藩方法来办理的,却并未受到舆论指责。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处理办法违背民心、民气,清廷亦有意打压湘系势力,因此曾国藩“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调任两江总督,上不安于朝廷,下不安于旧部,在心力交瘁之下死去。
教案遗址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原发地“天津望海楼教堂”,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北侧,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教案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冲突事件,被后世民众牢记,被中国近代史学者们持续研究。天津望海楼教堂墙外,立有“天津教案遗址”的纪念碑。
安庆教案
一·、安庆教案
基督教东来大约可以上溯到唐朝,但是直到明清时期,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才在中国兴隆,其间也夹杂着“教禁”的磨难与痛苦,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人封闭的大门,《南京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迁,自此中国进入一个旷古未有之变局。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三条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岸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拂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因此,西方传教士认为这是向中国公开传教的转机,使得两百多年的“教禁”开始解冻。但在条约中还没有自由传教的说法,大部分传教士都是非法潜入内陆传教的。据统计,1844~1858年非法潜入内陆的外国传教士50多人,活动几乎遍及全中国 。以后又在传教士的要求下,清政府准许“弛禁”传教。《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像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原先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的布道者更是频繁穿行中国各地。1889年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已有1296人,1906年增至3833人,1919年达到6636人 ,这还不包括受有圣职的华人在内。面对在华外国传教士数目明显增多的形势,李鸿章在1874年曾述及:“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中国正是在这种古今未有之变中,徘徊于救亡与启蒙的旋涡里缓慢经历着畸形的近代化过程。 此时在江南这块沃土上的外国传教士更多。
江南原是一个省的名称,后分为江苏与安徽两省,两省设巡抚。当时的安徽省有13府55县,安徽省的巡抚驻安庆,从1662年起将近300年里,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这里三省交界,是皖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传教士希望以此地为基础,把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安徽各地,从而影响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1896年5月4日,根据委办洋务局的二品顶戴置安庆、庐、滁、和道潘如杰上报总理衙门的材料统计,当时安徽省各州县共有有教堂155所,分布在省内35个州县,其中安庆府有13所。这些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披着合法的外衣来往于中国各地自由传教,“做那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带着这个目标,教会的事业与传教士的活动在传教和慈善事业的掩护下,进入西方传教史上最不光彩的历史时期。
1858年之前,传教士还未深入安徽省的内陆。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安庆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列强为避免清政府怀疑其与太平军勾结,对在长江中下游的传教暂时保持克制的态度。1864年7月,太平军失败之后,这些地方的传教活动开始兴起,安庆地区传教人数由1869年的2人增至1876年的6人。
安庆教案源起于一位中国神父熊臣尧。他奉安庆教案与近代官绅阶层研究代牧主教鄂尔璧的指示,到安徽省省会创立新的教会立足点。熊神父接受任务之后,“乔装商人,用他私人的名义买了一座房屋作为他经商之用;他还冒险到安徽省边境的徽州府探访教友”。他以卖布匹为名,从事传教活动,广泛来往于安庆与徽州等地。另外被称为“勇士之中的勇士”的雷神父,他负责长江与运河流域的大城市,于安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创立永久巩固的事业”。1865年5月,内陆会鄂尔璧会长与“勇士”雷神父乘坐军舰“唐克雷德号”驶离上海,到达安徽省会安庆。他们拜访地方官商议传教事宜,地方官搪塞不见,而后为形势所迫无奈与教士们进行了表面上友好的会晤,并宣称他们只能按南京总督的指示来处理教会事务。而后那位牵头的熊神父把他在安庆城内以私人名义购买的房产让给了教区,一位医师住进去并给邻近贫者看病。熊神父继续以经商为名,从事传教活动。不久流言四起,说那位医师是传教士的代理人,为传教做铺垫工作的,于是教士们的行为遭到安庆官绅及平民的反对,只得求援于会与官方打交道的“勇士”。“勇士”雷神父得到消息立刻动身,1865年9月24日到达安庆。当时安庆的反洋教气氛已经很紧张了,雷在谈判时要挟地方官并且要求在安庆建立教堂,最后谈判不了了之。晚间,官员们暗地里组织了一次暴动,雷神父在医师和传教士的帮助下逃离至上海。雷神父在安庆遭到“袭击”之后,“耶稣教的教牧人员、商人、银行界人士同主教一起一致要求立刻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1866年3月10日,法国公使伯洛纳照会总理衙门:“安庆事件假如三个月之内不给解决,我将用战士占领一块城内的土地”。总理衙门通知李鸿章,李鸿章拒不答应传教士进入安庆,因为安徽是他的出身地,他认为在他任职期内,洋人侵入他的家乡可谓莫大的耻辱。1867年,曾国藩接替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10月,雷神父与他进行了商谈,“并要求归还安庆城内的神父住院,还提出要一块靠江边的土地,作为他前年受辱的赔偿”。曾国藩一一允诺,传教士备受鼓舞,于是安徽很快就成为传教的中心。当时管理江南的主教郎怀仁在信中这样说:“安徽省的传教活动在广泛地进行着,甚至发展到省的边。教区在前进,像巨人一般步前进”。1869年,就在他们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感到志满意得的时候,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达到高潮。安庆反洋教斗争的高潮是在湖南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拉开序幕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就此起彼伏,接踵相继,一张张的揭贴、海报、檄文,贴于各地的大街小巷,反洋教的呼声愈来愈高。1869年,一场反洋教斗争终于在安徽省省城安庆爆发了。
这一年的七月间,湖南反洋教揭贴流传到安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揭贴内容为:(1)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2)入教者必先毁除祖宗牌位,遇到庙宇,即行拆除。(3)教堂以甜言蜜语勾引男女,买给败类洋人,甚至远送南海岸侧,充作渔人钓饵。奸夷在条约庇护之下,经营商业,关卡通行无阻,不受查验,教士布满各处为之侦察。揭贴称“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号召“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安庆人民在揭贴的鼓动之下纷纷展开捣毁教堂和驱除教士的活动。
1869年8月,正是安庆县试府试期间。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平时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有浓厚的反教思想。10月,考生与教士发生口角,接着传出匿名揭贴,号召驱除教士。传教士发现后,要求地方官调查写匿名揭贴之人。地方官以府县转移人数众多,难以查证为词进行搪塞,并嘱咐教士切勿外出惹是生非,教士不理。11月3日,教士不听劝告到府衙抗议,要求道台惩办揭贴之人。在教士坐轿去衙门的路上,考生们蜂拥而至,在一阵喧闹中把教士坐的轿子掀翻,高呼“杀洋鬼子!打洋鬼子!”教士避入府里呼救。事既开头,不可遏止,许多考生及群众又涌入西右坊英教士的住所以及东右坊的法教士的住所,捣毁家具什物,驱除教士。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安庆教案。
在教案酝酿的过程中,府县官员若“诚能先事预防,次日断无集众滋扰之举;及事已酿成,倘能及时认真弹压,教堂倘不致闯入抢掠”。而地方官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采取的是纵容的态度。其实安庆地方官因传教士到安庆之初,挟势“租房”传教,将教堂盖在衙门附近,心存不满;继而传教士不听劝告,径闯衙门以致酿成事端,地方官更是不满;又因为地方的士绅势力派参与反洋教斗争,地方官不得不顾及,因而对英法教士提出的驱散闹事群众、赔偿损失、保护教士生命安全等要求,故意拖延,坐观事态的发展。“各地方官并不尽力设法禁卫”,传教士也毫无办法,于是教士逃往九江见公使阿礼国。阿礼国以安庆教案要挟地方大员,最后以指拨城内官地为教会堂基、赔款、惩办“肇事首犯”、申斥护教不力的官员等不平等要求议结1873年,“在安庆成立了一座外交衙门,神父们遇到什么困难,便可以向它反映”。
二、近代官绅阶层反洋教原因
近代官绅阶层中的“近代”是从时间上界定的,并不表示这个时间段上的官绅阶层整体近代化了。这个时代的官绅阶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占有统治地位,在社会结构的链条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官就是任职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官员;绅,就是士绅,亦称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些已经取得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亦官亦民,非官非民。在中国近代史上,官绅阶层广泛参加教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黄文治,陆发春:安庆教案与近代官绅阶层研究第4期案。笔者根据《中国教案史》、《江南传教史》、《教务教案档》等典型教案资料作了一个统计:1861~1900年,官吏、士绅与会党成员参与反洋教斗争总人数多达422人,其中官吏公开参加人数为68人,占总数的16%;士绅参加人数为248人,占总数的59%;会党参加人数为102人,占总数的24%。可见,中国官绅阶层反洋教的比例是很高的。纵观安庆教案,情况同样如此。教士的蛮横和盛气凌人的态度,把不少地方官绅得罪了,因此,官吏支持或者同情反洋教斗争,乡试学生直接参与战斗。
官绅阶层在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刻,有鉴于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毅然参加反洋教斗争,除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官绅阶层对外国传教士的偏见与痛恨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1)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对官绅阶层的打击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湖南流传到安庆的揭贴第三条就反映了这一点。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外交,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大量特权,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加上传教士依托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参与各方面的侵略活动,使官绅阶层非常反感,排外情绪勃兴。这种排外情绪不仅充满了朝廷,也渗透到地方的官绅阶层中。外国的侵略,破除了中国的中心观和“夷夏”观念,深深地侮辱和伤害了官绅阶层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官绅阶层的不平之感以及民族自尊心日益增强,中国到处都爆发排外运动,于是在官绅阶层的鼓动或者直接参与下,教案频发。安庆教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个案。
(2)中西文化碰撞造成了官绅阶层信仰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危机是近代官绅阶层反洋教的又一重要原因。湖南流传到安庆的揭贴第一条就反映了这一点。安庆教案中官绅反洋教斗争比较典型,因为在封建社会,官绅与中国的文化交融性比任何其他阶层都密切,他们赞扬孔子,信仰儒教。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系统地歪曲了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并且无情地攻击儒教为“梦魇”。传教士“破坏了家庭,干涉了祭祖礼节,把那已经深入在他们生活中的佛道礼仪说成邪教,而对传统的先师孔子的训迪并不称之为’圣’。他要求他的教徒们对本乡村和家庭的礼典的维持,停止贡献”。这些行为对官绅阶层的精神支柱冲击很大,于是“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在官吏看来,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革新者”。且“严夷夏之辨”历来是中国官绅阶层的一个指导原则,“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所谓“一道同风”就是指把社会的各方面统一到儒家的“圣道”之下,就是“中国人有中国之教,为中国之子民,即当尊重中国圣人之教”。而西方教会与传教士传播无道无孝、弃绝人伦的洋教,破坏了中国的“一道同风”。因此,在安庆教案中,中国官绅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发生更为激烈的思想和行动上的交锋也是在所难免。
(3)传教士对官绅阶层历来把持的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直接威胁到他们的世俗权利、地位和利益。安庆教案中,除绅士之外,传教士有与地方官平等往来的特权,他们有的直闯官府、咆哮公堂、侮辱官吏,这样洋教势力就成了一个独立系统。这个系统由公使、领事、主教、教士等组成,通过干涉民教诉讼,对官府的权威和尊严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他们在安庆这些内陆享有治外法权,甚至比官绅阶层更不受制于中国法律;且教堂霸占土地房屋,把教堂建在官府旁边,都损害了官绅的利益。另外,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仁爱堂、育婴堂,创办一批为中国官绅阶层所不及的文化、医疗事业,如发行新书报刊、开医院、设学堂等。染指这些本来由地方官绅阶层所承担的事业,特别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堂、出版著作、发行报纸,在真理问题上与官绅阶层唱对台戏;宣扬基督教真理,与中国官绅阶层争夺话语权,自然激起中国官绅阶层的不满。这也构成了他们反洋教的一个原因。
三、安庆教案的性质评价安庆教案,既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是反侵略的必然结果。
这次教案的突出特点是:地方官纵容;参加的阶层和人数众多,由知识分子发起;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其声势浩大不仅与教案发生在省城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还在于近代官、绅、民联合参加了反洋教斗争。
目前,史学界对反洋教斗争的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的性质,更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另一些学者认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官绅阶层往往充当领导人物,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常常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去对抗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因而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反思安庆教案,既不具备反封建的性质,也称不上农民革命,但官绅阶层借助绅士平民的声威,暗中支持鼓动并参与反洋教斗争恰恰证明了其反侵略性,客观上捍卫了民族利益。
当然安庆教案以维护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秩序的面目出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某些落后性的东西,反抗的方式也是愚昧落后的,但我们不能够因此低估其反洋教斗争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因为官绅阶层的参加,就从感情上贬低它。中国封建社会悠久漫长,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传统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到19世纪下半叶,传教士依附侵略势力,认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中国经历着亘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个古老且闭关锁国的帝国面对枪炮和基督的进攻,人们没有别的武器可拿,只有拿起传统的武器与斗争的方式来对付西方列强及传教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尽管其间渗透着盲目排外与落后的斗争方式,甚至有违反现代文明的地方,但我们不能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前人。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抵抗,他们的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