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骞是清初著名诗人,因身涉到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全家被发遣往宁古塔为奴,在那边待了二十三年。影视剧中常见的“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桥段,对吴兆骞一家来说是切身遭遇。
实际上他父母最终被赦免,不曾前往东北。妻子则是带着婢女于数年后抵达宁古塔。相比之下,《甄嬛传》中大橘把甄远道全家发配,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开恩,甄嬛最后把他nen死不冤枉。
宁古塔是清代边疆重镇,有新旧两处城址,均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流域。吴兆骞在给父母的书信中描述宁古塔为“寒苦天下所无”:
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这等边塞之地,其间主要居民是半军事化的驻屯人员索伦人,也就是“与披甲人为奴”中的“披甲人”。在上篇披甲人与发遣奴——清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中,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披甲人即索伦人是怎么一回事。清廷不但限制他们的居住地点,也限制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限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统治需要的压迫政策。
与披甲人对应的,就是给他们做奴仆的“发遣奴”。“发遣为奴”是清代特有的刑罚方式。受刑人被降籍为发遣奴,视家庭情况不同,被遣往东北、新疆和西藏,为当地头人和驻军从事农猎杂役。这种制度除了惩治本身,也是清廷对披甲人制度的补充与再利用——既然不允许索伦人脱离原始部落生活,总要打发人去伺候他们嘛。
近代俄罗斯人拍摄的索伦人部族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日子,据他自己总结,还算过得去。吴兆骞长子吴桭臣出生于宁古塔,17岁才回到江南,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宁古塔纪略》,记述了他们家在宁古塔的生活。在他笔下,吴家人钓鱼、冬捕、制糖、酿酒、打猎,除了冬天实在是长了点,也颇有一番趣味。
“冬则河水尽冻,厚四、五尺。夜间,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鱼辄聚其下,以铁叉叉之,必得大鱼。”
——听起来很像查干湖冬捕。
然而,吴兆骞一家在宁古塔过得凑合,不代表与披甲人为奴的日子是好过的。
诚如前言,“与披甲人为奴”本质上是刑罚。既然是刑罚,发遣奴的第一重身份就是罪犯;做发遣奴是要去给披甲人干活的,所以发遣奴的第二重身份即是苦役。事实上就是沦为贱籍的奴隶。
吴兆骞的特殊,在于他得到了宁古塔昂邦章京巴海和副统领安珠瑚的赏识。昂邦章京就是后来的将军。本文在上篇中介绍过,所谓将军和总管大臣,是专设为管理披甲人和发遣奴的治历官,即驻屯地最大的主子。吴兆骞被主子看重,自然可以登堂入室,进入当地统治阶层圈子,诗樽词盏,鸿儒往来,这日子能不好过吗?
“至戎所,戎主以礼相待,授一椽于红旗中,旧迁客三四公,皆意气激昂,六博围棋,放歌纵酒,颇有朋友之乐。”
吴兆骞的边塞诗写得很好,在清初据有重要地位。但他笔下的关外,最苦也无非是风雪苦寒,或给养不足,需要全家上阵种菜之类。这种困难来自当时东北的恶劣环境,而非发遣奴制度。他过的并非是发遣奴的生活,而是文人幕客的生活。他写过一首《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俨然如幕上嘉宾。
《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玉勒动珠愤,旌旗还肃纷。鸣弓行硕雪,飞盖入边云。属国鞭鱼部,佳丘鸾鹤韦。海东一万里。箱吹日相闻。
那么,这种特殊待遇是读书人身份赋予的吗?谈不上。吴兆骞的确很有才华,但同时期还有个同样很有才华的反例叫季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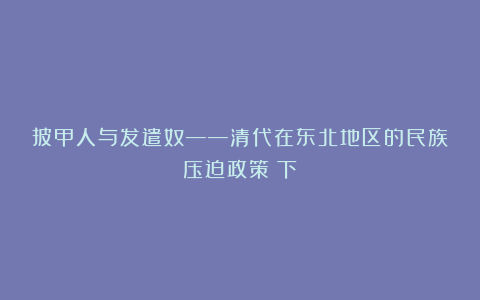
季开生发遣前的身份比吴兆骞要高得多,吴兆骞只是应试举子,而季开生早已是进士之身,充任庶吉士后还任过礼科和兵科的给事中,在京官中属于位卑而权重的类型。
这样一个人,在触怒皇帝、遣送东北为奴后,是个什么结局呢?史载其力阻顺治买女子入宫,顺治大怒,以“妄捏渎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杖责一百后遣送辽东尚阳堡,四年后为光棍殴死,“有司不问,疑有主使者”。
一个正儿八经的进士、京官,在地方上有背景,在士林中有声望,当他变成发遣奴,说打死就打死了,除了一句“疑有主使者”,没有任何下文。
等到了雍正六年,皇帝干脆下诏明确:打死发遣奴,无罪!
如果某种社会身份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产品、不拥有任何人身自由、对其人格和生命权的侵犯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那么它自然是事实上的奴隶。奴隶怎么会有好日子过?
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里描述了一种化外野民的优容生活。虽然事必躬亲,吃穿都要动手,但天地博大自由,物产应有尽有:
这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世外桃源,对于本地头人的幕上宾是可能的,对真正的奴隶来说无异于白日做梦。“自取”?关外资源是清廷私产,私自开掘的即使是正身旗人,也必须治罪,发遣到云南贵州、两广烟瘴地区为奴。
这就造成了一个神奇的历史现象:
类似于近年名梗“原来我祖先是被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那个”
真正的发遣奴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还是看吴兆骞的记录:
“至若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每一庄共十人,一个做庄头,九个做庄丁,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既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散。每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芦一百束。至若打围,则随行赶虎狼獐鹿。凡家所有,悉作官物,衙门有公费,皆来官庄上取办,官庄人皆骨瘦如柴。总之,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炭,并无半刻空闲之日。”
如此繁重的劳动下,却要承受极端的自然环境、微薄的给养和无底线的人身侵害。我们在披甲人与发遣奴——清代在东北地区的民族压迫政策(上)中谈到披甲人的生活已经够惨了,而发遣奴的生活还要等而下之。这种惨状造成了极为激烈和高频率的反抗。仅《清高宗实录》一书,就有发遣奴杀披甲主人、杀披甲全家、杀披甲全家兼左邻右舍的多条记载。《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类似记录更是数不胜数。
如雍正四年,有发遣奴纪二者,因不知农事,无法为披甲主人查书耕作,被后者打骂并克扣衣食,纪二没有活路,一怒之下将查书全家九口尽数杀死(见档编8-1727)。
因为反抗过于强烈,乾隆二年甚至下令,凡无家无口——用现代化语言描述就是“没有软肋”——的发遣者,不再送往关外。凡去往黑龙江、宁古塔、盛京等地的发遣奴,尽是拖家带口、易于控制的人。然而,反抗依然层出不穷。清廷的压迫政策,甚至反倒有“各处披甲人等竟有图占该犯妻女,不遂所欲,因而毙其性命者”的反效果。
至于吴兆骞的妻子葛氏,竟能带着婢女前往宁古塔,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男耕女织还连生好几个娃,这才是奇迹。
归根结底,清廷的发遣奴制度实在太严苛了。明代的充军军户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例如万历名相张居正,就是荆州军户出身(参见牛皮癣与钉子——读《张居正大传》)。但清代的发遣奴如无恩赦,子子孙孙都不得参加科举,也不得入关。据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发遣奴子孙世代,均为奴籍,不得出户为民。虽然有一定晋升途径,也不能到关内任职。清代在东北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柳条边制度,就连私自奔逃的希望也一并断绝。
在如此严格的约束下,清代东北发遣奴最终走向一种历史特有的吊诡结局。
人到底是自然界的顶点。与定期上交血税、人口越来越少的披甲人不同(清初至中期战争史,调动索伦兵超过70次),由于不必打仗,发遣奴在关外顽强地站住了脚并繁衍生息,以至于皇帝们开始担心东北老家被发遣奴人口置换了。柳条边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圈住盛京到长白山的“龙兴之地”,不允许关外平民进入。嘉庆时期甚至试图把东北发遣奴全部发往新疆,结果引起了民变,最终不了了之。
东北相当多的老满洲都是发遣奴的后代。满洲驿丁是三藩的部队后人,宁古塔的水手、辽阳堡的兵丁,也多从发遣奴之中招募。许多年的光阴下去,到了清末,他们也都成了正经的老满洲了。现代基因学技术下,满族的基因组成与汉族多有重叠,就跟这种地区人口变迁有关。
挖了主子的老参被发配云南的满洲,后人自认是大明沐王爷的部下;天地会造反失败的总舵主,在东北留下的血脉说自己有通天纹,岂不怪哉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顺治年间官方发动的垦荒人,三藩之乱的参与者,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受害者,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义军,天地会成员乃至各路偷鸡摸狗之辈和山大王,这些统治者眼里的社会渣滓,最后手牵手一起变成了东北的满洲。我大清在东北的民族压迫是绝对一视同仁的,正如本文的上篇所论述,披甲人的披甲,也只是比发遣奴这等事实上的奴隶,多了一重为大清送死的权利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