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纸,生命的印记
——读张慧谋老师的《民间草纸》札记
张慧谋老师的《民间草纸》,像一本用最朴素的材料装订起来的民间志。它记录的,不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也不是文人墨客的风雅趣事,而是一张张粗糙、泛黄,甚至带着竹屑的草纸,以及它背后那些与普通人生死相依的温暖与庄严。
张老师以他那简朴而深情的笔触,为这即将成为历史的“民间草纸”,立下了一篇动人的传记。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与记忆,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即将消失的物件里。当我们回望来路,那一路的印记,或许就印在这一张张粗糙、柔软而坚韧的草纸之上。
“纸媒”二字,对于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把我拉回了那个慢节奏的年代。我的祖父抽水烟筒,他的火刀、火石、竹纸媒筒,还有芋叶包的熟烟(烟丝),都装在一只白色四角塑料袋子里。
张老师写六伯父“慢悠悠地,从大襟衫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纸媒筒,娴熟地擦石引火点纸媒”。读到这些文字时,祖父抽烟的背影跃然脑海,火刀、火石、纸媒筒这“三件宝”不仅是点烟的工具,更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
在火柴已是寻常物的年代,我的祖父与张老师文章中的六伯父,乃至与他们年纪相仿的乡野村夫,仍固执地沿用着更古老的方式,那“嚓嚓几下”迸发出的火星,点亮的不只是纸媒,更是乡村寂寥夜晚的精神之光。
祖父曾与我讲过水烟筒吓退贼人的故事:某村的一户人家,睡前抽了一筒烟,他睡熟了,那水烟筒还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噗”冒着泡。下半夜里,有贼人来偷东西,听到水烟筒冒泡的声音,他以为这户人家还有人没睡在抽水烟筒,于是这贼人就在这家的柴房躲着,等抽烟的人睡着他再动手。然而,那水烟筒的冒泡声久不久地响着,眼看天将亮了,那贼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不久,这贼人被抓,供出到这户人家偷东西被水烟筒声吓着没敢动手。
张老师的文字里,萦绕着那股混合着烟火、墨臭和竹香的复杂气味,那是生活的原味,是生命最本真的印记。
他笔下的六伯父是一位搬运工,也是一位乡间郎中,更是一位“讲古佬”。纸媒的微光,映照着他饱经风霜的脸,也连接着《三国》、《水浒》里的英雄世界。张老师写道:“楠蔴树下偶尔有月影的光斑漏下来,有时没有,夜色黑黑的。六伯父烟上瘾了,就模出口袋里的宝贝,嚓嚓几下,纸媒亮了,半个指甲大的’媒头’,像给夜烧穿了一个小洞。”这画面极富诗意,那被烧穿的小洞,是现实与传奇的通道,是六伯父用他的方式,为乡邻们开辟的一小片精神栖息地。
这小小的纸媒,承载的是知识、是技艺、是乡情,也是一个人不随波逐流的风骨。如今,火刀火石早已进了博物馆,水烟筒也少见,六伯父那样的“讲古仔”的夜晚,更是一去不返。那随着纸媒燃尽的,是一个时代的烟火气。
草纸的历史,源远流长。它可视为中国古代伟大发明——造纸术——在民间最广泛、最持久的应用。虽然蔡伦改进造纸术多用树皮、麻头等,但竹纸的制造后来居上,成为草纸的主要原料。关于古代造纸,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杀青》中详细记载了造竹纸的过程:“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当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以将生枝叶者为上料。” 这种古朴的工艺,在东水山的草纸作坊里,竟跨越数百年,依然被黑衣人“弯腰舀纸”的姿态所延续,令人顿生敬意与沧桑之感。
接生纸与花纸,生命的始与终,阴阳的界与约。如果说“纸媒”关联着日常,那么“接生纸”和“花纸”则直指生命的两个端点——生与死。“接生纸”这个名字,初读觉得直白,细思则感到震撼。作者小时候看到带血的草纸感到害怕,母亲一句“莫惊,那是’接生纸’”,道尽了生命的真相。原来,“村中每个小孩出生时,都是接生婆从草纸上抱上来的”。那深红稠浓的血迹,是母亲分娩时的剧痛与伟大,也是每一个生命降临人间最原始、最庄严的仪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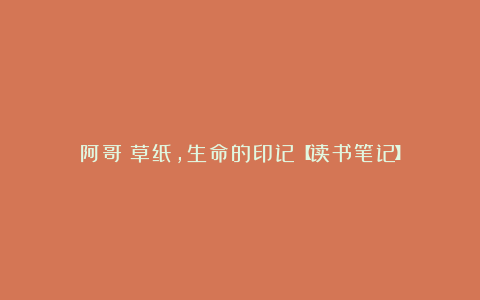
草纸,成了人生第一件“胎衣”,记录下第一声啼哭。它卑微,却承载着最隆重的新生。张老师感慨:“乡下人的命虽贱,但也庄严。起码老草纸维护了他们的庄严。”这庄严,同样延续到生命的终点。
文章里写到张老师的父亲去世时,“后脑枕着草纸,脚踝下压着纸钱”。从接生到送终,草纸贯穿始终。母亲叮嘱“多烧纸钱”,生怕父亲在另一个世界手头紧巴。出殡时,纸钱从村口撒到村外,这是生者对死者的不舍与祈福。
在这里,草纸化身的纸钱,成了连接阴阳两界的媒介,寄托着无尽的哀思。父母忌日同一天的巧合,更让这份生命传承的宿命感,显得沉重而温情。而“花纸”则关乎另一个世界——鬼神的世界。阴历七月十四的“鬼节”,母亲用竹簸箕印花纸,外婆剪出“女装大襟衫”式的花衣。整个村子在这一天,通过焚烧这些草纸制品,完成了一场与“孤魂野鬼”的盛大对话。
“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花衣花筒、纸钱香烛”,夜幕降临,“青烟四起,焰火灼灼,照红半个天空”。这是民间信仰中最具画面感的场景,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也体现了阳界与阴界之间一种朴素的“默契”。大人们神色凝重,孩子们则在这种神秘气氛中,进行着“收香脚”、“扭香脚”的游戏。生死大事,庄重仪式,最终在童趣中收场,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
草纸,在此刻成了调和恐惧与日常、神圣与凡俗的奇妙存在。
草纸手札,粗糙之上的文脉传承。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草纸手札”这一节。在“小时的乡村是罕见字纸的乡村”的年代,草纸成了作者练习书法的宝贝。这种窘迫与渴望,我父亲也曾对我讲起。他说他小时候练字,也是在廉价的草纸上,墨汁会迅速晕开,形成毛刺,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锻炼了对笔锋的控制力。
张老师说“草纸虽粗糙,却凝墨藏锋,笔意质朴内敛”,真是深得其中三昧。最动人的细节是,父亲“宠得不行”,任由儿子写光家里本用于折纸媒、印纸钱的草纸,并且将那些充满“浓烈墨臭味”的草纸,“一张也没扔掉,拿到太阳下晒干,再折纸媒”。这是一个沉默的、深沉的父爱故事。父亲或许不懂什么书法艺术,但他用最实际的方式,守护了儿子对文化的热爱。那带着墨臭的纸媒,点燃时燃烧的,不仅是草纸,更是父亲无声的期望。
后来张老师用宣纸,却觉得“宣纸是贵族,草纸是草民,草民品性正合我心性”。于是他买回草纸,抄录《论语》,作成“草纸手札”。这个行为,极具象征意义。最经典的儒家典籍,用最民间的纸张来承载,这正是文化扎根于泥土的生动体现。
文化的血脉,正是在这粗糙的、坚韧的草纸上,被一代代人默默地书写、传递。
张慧谋老师探访东水山即将消逝的草纸作坊,那“沉闷坚韧的舂臼声”仿佛是古老文明最后的脉搏。
草纸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但我们不能忘记,它曾如何紧密地编织进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经纬里。它见证过新生的血污,陪伴过孤寂的亡魂;它点燃过水烟筒前的谈古论今,也承载过少年笔下的横竖撇捺;它在鬼节的烈焰中沟通阴阳,也在日常的角落里散发微光。
乙巳年八月初五夜整理,配文图片来自张慧谋老师、庄健鹏等朋友圈
作者简介:
阿哥,六十年代出生的庸夫俗子,自喻为带孙的乡野村夫,自封为九品御前带孙锦衣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