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涛画柿子,先以没骨法点出饱满的果身,一笔下去,水分与朱砂自然晕开,边缘渗出轻浅的绯,像少女初次害羞的红晕;再以焦墨勾出萼片,轻挑一线,果柄便挺了起来,仿佛随时可以“啪嗒”一声掉进草丛。那团红,被他调得极亮,却不浮,像是从宣纸里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呼吸,也带着霜降的清冽。
这一刻,柿已非柿,而是一团火,一枚红日,一句低声的祝福——“事事如意”。
松鼠是柿子树最顽皮的客人。它总是从画外“嗖”地闯进来,长尾一甩,枝头的柿子便轻轻一晃。王雪涛喜欢把松鼠的尾巴画成一弯弧线,墨色由深到浅,像一截被风吹散的烟;小爪紧攥枝条,指甲用极干的笔锋擦出,带着“沙沙”的质感。
松鼠的眼睛最妙,只两点焦墨,却滴溜溜乱转,仿佛下一秒就要张口偷咬。于是,整幅画便活了:柿子因松鼠的觊觎而更红,松鼠因柿子的饱满而更馋,人与自然的呼吸在纸面上悄然合拍。观者忍不住想伸手替松鼠摘下一颗,又怕惊扰了这份秋日的私语。
喜鹊来得更隆重些。它们尾巴一翘一翘,像提着幅喜帖。王雪涛画喜鹊,用墨极省,背羽一笔带过,却在飞羽处突然顿挫,留下飞白,仿佛能听到空气被翅膀划开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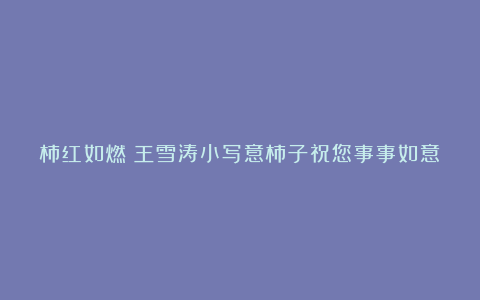
画家把这一瞬凝固成永恒:柿子因喜鹊的到访而有了喜宴的隆重,喜鹊因柿子的火红而添了归家的暖意。于是,“喜上枝头”“事事见喜”的吉兆便从纸上漫向人间,像一缕不肯散去的炊烟。
他的色彩也带着市井的欢喜。朱砂、赭石、藤黄,都是年画上最常用的颜色,却被他调出高级的透明感。柿子的红,亮而不燥,像被井水沁过;叶子的绿,沉而不滞,像老铜器上长出的包浆。
偶尔点上一只青壳甲虫或半截枯黄草茎,画面立刻有了“野”味——不是荒野,而是野趣,是孩子扑蝴蝶、抓蚂蚱的野,是老人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的野。王雪涛把这份野趣轻轻拢进宣纸,像拢住一只扑棱棱的鸟,翅膀还在动,却已安心栖息。
有人说他的画“雅俗共赏”,其实这四个字背后是滚烫的慈悲。他见过菜市口为几文钱争执的小贩,见过雪夜里卖糖葫芦的老人,见过新婚夫妇把“囍”字贴在漏风的窗上。
于是他把柿子画成人人都能读懂的句子:你若想要丰收,它便沉甸甸压弯枝头;你若想要吉祥,它便招来喜鹊;你若想要团圆,它便圆滚滚像十五的月亮。那些松鼠、喜鹊、螳螂、蜻蜓,都是他派往人间的信使,带着“好好生活”的口信,轻轻落在你的袖口。
当最后一幅柿子图完成时,他题了八个字:“柿柿如意,岁岁平安。”墨迹未干,窗外的柿子树忽然坠下一颗熟透的果,“咚”一声砸在阶前,像一声轻轻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