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绍昆经方系列 ○
娄莘杉 ○ 编著
第
6
讲
——读懂桂枝汤①
1、桂枝汤的药物
读懂桂枝汤,让我们从桂枝汤药物的讨论开始吧。
《伤寒论》的药方,除甘草汤之外,所有药方都由二味、三味或三味以上药物组成,每一味组成药物都有一个、二个或几个症状作为自己的治疗目标。
药物和药物治疗目标,就组成了“药证”(药征)这个概念。
提出“药证”(药征)这个概念的是吉益东洞。他写了一本《药征》的书,书中指明了《伤寒论》中每一味药的治疗目标。《药征》和我们本草学中所讲的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药性不一样,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类的内容。吉益东洞这本书奠定了汉方医学临床研究的基础。
《伤寒论》的条文中没有单独地讲每一味药的性能与效用,后世医家都是利用《神农本草经》或《本草纲目》等本草专著来解释《伤寒论》药物的性能与效用的,而这样的解释对于《伤寒论》的药物效用并不一定适用。可以说,几千年来对《伤寒论》药物治疗目标的研究没有系统地进行。
吉益东洞的研究是一个创举,《药征》的书名即有深意。这个“征”字就是用药时应该依据什么征兆和证据的意思。《药征》刊行100年以后,尾台榕堂根据《药征》临床应用后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一本《重校药征》,对《药征》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校订。我国清朝邹澍的《本经疏证》与周岩的《本草思辨录》中也记录了一些有关《伤寒论》的药征。
黄煌教授在《药征》《重校药征》《本经疏证》《本草思辨录》等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发挥,撰写了《张仲景50味药证》,其分类更为科学,临床应用更为方便。
先人对于方证辩证的认识,应该是先懂得了药证,接着了解了要基证,然后才把握方证,通过这样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发展起来,其中的基础就是药证。
然而,几千年来我国中医界却很少有对药证方证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屈指可数的只有清代黄元御的《长沙药解》、邹澍的《本经疏证》、周岩的《本草思辨录》、莫枚士《经方例释》等几本。民国时期的陆士谔先生肯定了药证的临床研究价值,对邹澍的研究做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士谔医话》中写道:“日本医学博士眼光中,只认识李时珍之《本草纲目》,尚未认识邹润庵之《本经疏证》。仅知药性,不识方义。”“以武进邹润庵《本经疏证》为研究方法,处处脚踏实地,字字皆有来历,不矜奇不立异,大中至正,必以实用为归。”“中医的学说,大别之可分作两种:一种是依据《内经》,偏重说理的:一种是依据《伤寒论》,偏重认证的。就可惜历来注释《伤寒论》的几位名家,《内经》的主观太重,总用《内经》的见解来解释《伤寒论》,以致《伤寒》一书,不解倒还明白,愈解愈糊涂,什么标本中见,什么寒化、热化、湿化,一大堆不相干的话,听得人家莫名其妙。正如翠屏山戏中潘老丈所讲,你不说我倒明白,你一说我越糊涂了。医不是仙人,病不会开口,因此偏重认证的,总说症者证也,要认清是表是里,属虚属实,在经在络,还须辨出个寒热,辨出个脏腑。旁敲侧击,审之必确,问之必详。就为病证关系人命出入,不敢草草,亦不忍草草。偏偏依据《内经》的,好为理论,自作聪明,创出’医者意也’的谬说,用演绎法推测百病,不用归纳法归纳病证,毫厘之谬,差及千里。一人有过,遗及全体。我们中医吃亏的地方,即在于此。照我偏见,大家研究仲景之书,研究人手,照武进前辈邹润庵夫子《本经疏证》做去,我们中医才有光明的一日。”“仲景《伤寒论》,研究家用尽心机,辨明某几句是仲景原文,某几句是叔和改作,某条该移方向前,某条该退之使后,吃饱了清水白米饭,没事做,把这些工作来消遣。依我,张仲景也不是我的亲家,王叔和也不是我的冤家、究竟哪一位动的笔,我也不曾亲眼看见。我现在只要瞧他合理不合理。王叔和合理,我也该信仰:张仲景不合理,我也该驳斥。古人是古人,书是书,理是理,一一分析,不得稍有含混。遇到于理有未合处,发生疑问,便当反复推勘,以求彻底。如邹润庵之疏本草,读《伤寒》,一字一句,不肯轻易放过,必求其奥,必得其理,这才是中医改良工作。自打天下,杀开一条血路,不是去依傍人家,影戤人家的响牌子。”
陆士谔真是一个明白人,他能够透过邹润庵《本经疏证》这本著作,看到了邹润庵已经洞悉大论之原旨。如果他不是一个精透领悟《伤寒论》而圆机活法的医者,绝不能有此等之眼光。
2.桂枝汤中的甘草
甘草,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中药之一。“甘草,帖帖有份”是民间的口头禅,其意思是在中药方中甘草无处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连专门研究《伤寒》《全匮》的陆渊雷也这样认为。他在《陆氏论医集·肺主皮毛的解释》中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写道:“甘草好像是位党国要人,各机关都有他的大名,却不甚负责办事。”可见几千年来,人们对于《伤寒论》中甘草的作用所知甚少。
甘草,在康治本桂枝汤(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的药物排序中列第三位。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前讲甘草呢?因为甘草在经方医学发生发展的道路上厥功甚伟。日本汉方家对甘草的赞誉更是无以复加,说“甘草的使用是《伤寒论》构成药方的第一原则”。这是日本汉方家远田裕正教授提出的,在这之前大塚敬节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们的这一观点发掘出了《伤寒论》所隐藏的秘密,冲破了传统药方构成的认识框架,无疑是在中国中医药界撕裂出一个不小的口子。
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个有趣味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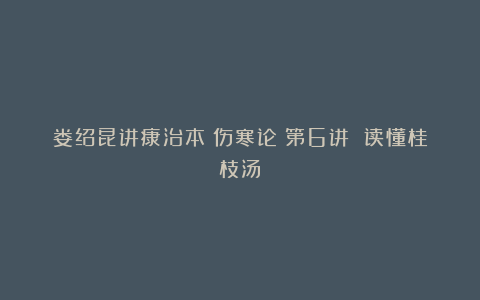
人类都是“喜甘爱甜”,汉人也不例外。甘草是一味甘甜的东西,在中国汉民族生活圈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呢?在没有糖果之前的千万年的社会里,甘草就是小孩子们的“糖果”。记得20世纪50年代,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当时糖果已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里买到,但我还是经常和同学一起到中药铺里买甘草吃,觉得甘草有和糖果不一样的甜味,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当然,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甘草不能够乱吃,吃多了会引起水肿与血压升高等水钠潴留的副作用。遥想上万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先人生活在一个以打猎、捕鱼,摘树上的果实、挖草根维生的年代。当他们发现甘草的时候,其可口的甘甜之味所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我认为没有什么药物的发现能够比甘草的发现,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快速度地传播了。
原始社会,先人的医疗活动除了外治方法之外,所服用中的药物也只能是周围的动植物。治病的药却大都是苦口的东西,所以服药是一种无奈的需求。人类是“喜甘厌苦”的,科学研究证明人吃到甜味,大脑中会分泌多巴胺,让人感到愉悦和幸福。服药是人类求生本能战胜“喜甘厌苦”本能的无奈之举。而甘草是一味甘甜的良药,它的发现在无意之中打破了单味药治病的僵局。于是先人自然而然地把甘草作为矫味矫臭的药物引进了以往单味药治病的实践,引发了一场药方配伍的革命。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发现了甘草之后,开启了中药配伍的机会,而中药配伍的开展与展开,又出现了药方形成的机会。据此我认为,有没有发现甘草的中医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甘草这一无可替代的里程碑样作用,也许就是其“国老”别名的由来吧!
3.甘草的治疗目标
先人在发现甘草的同时,也渐渐地掌握了它的治疗目标。《伤寒论》由单味甘草而独立成方的“甘草汤”,明确地指出它能主治“咽痛”。吉益东洞认为,甘草的药证是“主治急迫”,就是具有“缓急”的作用。“缓急”作用表现在哪里呢?吉益东洞在《药征》做了具体的讲解:“故治里急、急痛、挛急,而旁治厥冷、烦躁、冲逆之等诸般迫急之毒也。”我们结合临床实践来说,“甘草”可以治疗所有的急性病,因为它能缓解人体抗病中的激烈反应。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它能治疗各种急性疼痛、心脏的剧烈跳动、精神的极度兴奋、肌肉的过度痉挛、癔病和癫痫的发作,以及由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昏厥与肢冷等病证。当然吉益东洞说的治疗目标不是指由甘草单独完成的,而是在由它组方的方证中所表现出来的。甘草具有“主治急迫”的效用,和中国历代本草文献对甘草功效的记载有所不同。本草文献认为甘草能解毒,能调和诸药。如此论叙甘草的性能,显得比较抽象与笼统。
4.以甘草为配伍的药基证
以甘草为配伍的药基证是自然而然发现的。
甘草和其他几种当时已经发现的药物组成了药对(药基),形成了药基证。如桂枝甘草基证、芍药甘草基证、茯苓芍药甘草基证、茯苓桂枝甘草基证、麻黄甘草基证、大黄甘草基证、黄芩甘草基证、甘草干姜基证、麻黄甘草基证、栀子甘草基证、石膏甘草基证、知母甘草基证、甘草大枣基证、甘草干姜附子基证、大黄甘草芒硝基证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以甘草为核心的药基证呢?这并不是有意识理性的思考,而是先人运用野性思维所形成的经验。比如桂枝和甘草一起服用,服用后发觉味道比以前容易下咽。而且发现,桂枝治疗目标是汗出、心悸,和甘草配伍后,汗出、心悸等症状的改变比前服用桂枝还好,服药后的疗效也更加稳定了。古人就觉得如此配伍,何乐而不为呢?桂枝甘草基的证治就固化了下来。芍药也一样,芍药有酸酸的味道,但是跟甘草配伍之后,甘酸相合,其味更佳。芍药能够止痛减痉,加上甘草以后,止痛减痉效果倍增。干姜、甘草,甘辛味醇不辣,单味干姜治疗胃冷、疼痛、腹泻等效用,加上甘草后,干姜作用大大地提高了。麻黄、甘草,甘辛相合,其味可口,比单用一味麻黄治疗气喘的效果更好,同时又避免了出汗过多的弊病,后来就成了《金匮》的甘草麻黄汤了。大黄、甘草配伍后,大黄的苦涩味变淡而容易下咽。大黄会引起腹泻,但是腹痛便秘的人腹泻了以后,其原来的腹痛便秘就好了。于是,人们就知道虽然大黄不适合每一个人吃,但是对有那种腹痛腹胀、大便拉不出的人,大黄是个好药。单独服用大黄,有时候腹泻止不住或者腹泻以后肛门很痛,而服用大黄甘草基后,大便能够泻下,但又不至于腹泻无度,肛门也不会那么痛。
经反复积累、沉淀,上述的药物就渐渐地形成了《伤寒论》里最基本的药对。如果把这些最核心的药对再进一步进行配伍,《伤寒论》整部书中的基本药方就会在无形之中呈现出来。这些方子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都可以看到。这些最基础的方子,几千年来都始终保留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方子还有作用。这些只有两味药的方子,在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批治病的药方。这几个最为核心的药基证,为下一步重要药方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尾台榕堂在《类聚方广义》里对这几个方所进行的对照,是我们临床医生比较好掌握的。大黄甘草汤的治疗目标:大便秘结而急迫者。大便秘结主要是大黄所针对的症状;急迫是疼痛、神志方面感到很紧张,这是甘草所起的作用。当然,这样的人症状偏实,这个方主要是用来治疗怀孕后呕吐。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云:“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一般理解为,中医药治疗要因势利导,患者欲上吐,不可强之使下。但这并非是硬性规定,不是所有呕吐者都不能用大黄等泻下剂。只要这个人有大便秘结而急迫,即使有呕吐,也可以使用大黄甘草汤等泻下剂。《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云:“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呕吐可以说是大黄甘草汤的应用性症状,而特异性症状是大便秘结而急迫。《千金要方》治胃反吐逆不消食、吐不止方,皆用大黄。学习《伤寒论》,要辩证地看待问题,不可画地为牢而死于句下。
大塚敬节把甘草当作核心药来展开讨论。在他的《汉方的特质》这本书里,就把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桔梗甘草汤、麻黄汤、大黄甘草汤都解读成为甘草所派生出来的方剂。这些方剂不是普通方剂,是核心又核心的方剂,是最重要的方剂,其他方剂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在组方方面,甘草的作用非常重大。远田裕正的《伤寒论再发掘》更进一步论叙了甘草的作用,他通过大量的论证、举例、比较,得出一个结论:甘草是经方医学药方形成的第一原则。他提出《伤寒论》里那么多方的形成都离不开甘草的参与,没有甘草,这些方的组成就不可能,所以他认为要组方,首先要讨论甘草的效用。除了上述的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桔梗汤甘草、麻黄汤、大黄甘草汤之外,还有知母甘草基、石膏甘草基、黄芩甘草基、柴胡甘草基、栀子甘草基、茯苓甘草基,这些都非常重要。若把这些再展开,几乎就可以看到整个《伤寒论》的全貌,所有方剂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可见,甘草在组方方面的重要性。
总之,甘草在《伤寒论》从药到方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用甘草配合成汤方,在不改变治疗目标的基础上使人容易下咽,并能缓和主药的烈性,使服药更为安全。同时甘草药源丰富,容易采集。
5.甘草有储水的作用
《伤寒论》的理论核心是存津液,所有方药的证治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有关水的代谢问题。甘草有储水的作用,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储水作用。前面讲到甘草吃多了就会浮肿,古人对浮肿的理解是人体把水储藏起来了。甘草能够把水储存起来,虽然会形成病,但是相反的,有的人大量丧失水的时候,吃会储水的甘草就能够好了。这样的想法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对于一些出汗过多、腹泻过多、小便失禁,甚至出血过多的人使用甘草,或与甘草配伍的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都会出现明显疗效。
由于甘草的使用范围极广,又与最为重要的药物组合成核心药基证,这才使得《伤寒论》方证群的构成有了可能性。因为药方配伍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药物与药物之间的指抗与协同关系。甘草的储水作用,在与其他排水或储水不同效用的药物配伍时,就使药物配伍中的拮抗与协同关系得以充分的发挥。甘草与桂枝、麻黄、大黄、芒硝等强排水的药物配伍时,通过拮抗作用,使发汗与泻下得以有效的控制,这样发汗与泻下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可以说,假如没有甘草的配伍,发汗、泻下的治疗方法就无法施行。在那个远古社会原始的医疗活动中,这种拮抗作用是通过大量反复发生的实践而得知的,其可靠性经得起重复检验,拮抗作用的重要性就好像汽车、火车、电车、飞机里的减速器与刹机构,假如没有这两样东西,汽车、火车、电车、飞机绝对无法使用减器、刹车机构和发动机组成的关系,就是拮杭关系。这个拮抗关系对于桂枝、麻黄、大黄等通过排水治病的药物所发生的作用非常之大。这也是经方医学的方药与民间单方,股方的一个不同之处,大塚敬节在《汉方的特质·汉方药与民间药之区别》中曾说:“最近的化学药品一若没有制动器之汽车、乱向目的地突进,出事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汉方汉药,由于有各种各样成分,互相牵制合成,正如汽车有制动器与方向转换机,能安全运转。”
那甘草与干姜、芍药等储水的药物配伍又是起怎样的作用呢?毫无疑问,起的是加强储水的协同作用。干姜具有储水的作用,是通过反出汗、反吐、反泻下而达到其用的。与甘草配伍以后,同气相求,就会强强联合,增加这种效用。芍药也一样,也是储水的,能够使机体无法控制的津液流失减少或停止。甘草和芍药配合就起协同作用,这也就确定了三阴病治疗时的储水目的。三阴病需要津液的补充,需要储水。回阳救逆就是防止津液的流失,而防止津液的流失就是间接地储水,所以就有了“补阳气是补津液”这句话。三阴病的津液不足有三种状态:一种是功能不足引起津液的流失;一种是体液不足;还有一种是功能、体液都不足。甘草干姜汤类方、芍药甘草汤类方、芍药甘草附子汤类方分别承担了补阳、补阴、阴阳并补的作用。
总之,甘草在《伤寒论》从药到方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用甘甜的甘草配伍的药方,通过矫臭、矫味,缓和主药的烈性;通过协同与拮抗的作用,使每一个药方达到有效与安全。《伤寒论》中唯一一张以一味药组成的方剂就是“甘草汤”,足见在整理者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视甘草的作用。
桂枝汤中的甘草,通过桂枝甘草基与芍药甘草基,一动一静,共同完成皮肤排水的解表作用和收敛津液、补充津液的作用;再加上生姜大枣基的配合,治疗太阳病“恶寒。头痛,脉浮缓”的病证。
这种在方药中加人生姜、大枣、甘草(简称“姜枣草”)的方法,在古代是很流行的。甚至在现代中医界也还传承着。比如由三位日本汉方医家编著的《宋以前伤察论考》各论一《医心方〉中的古代伤寒治法》中写道:“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时,受到过老中医焦树德的教诲。在患者诊疗中最后我决定处方的时候,当大部分的药物考虑成熟时,最后的二三味药物用什么呢,我很快添加了’甘草、生姜、大枣’。”我们要注意这一现象,对于其中的机制值得深入研究。
6.问题讨论
问:太阳中风桂枝汤证是虚证还是实证?
答:太阳中风是三阳病之一,其中的桂枝汤证的治疗是通过皮肤排水的汗法,因此非阴病,非虚证。然而和太阳伤寒麻黄汤证相比较,太阳中风桂枝汤证则偏于虚。因此,选用调和气血营卫的桂枝汤解肌发汗,而不用麻黄汤、葛根汤等强烈辛温解表发汗剂。马堪温、赵洪钧等医家在《伤寒论新解·太阳篇新解》中写道:“(宋本)第12条桂枝汤服法中即明言,桂枝汤可连服至三剂,麻黄汤服法无此说。故读者须牢记桂枝汤之’发汗’与麻黄汤大不同。又,麻黄汤见微汗即止服,桂枝汤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