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清朝盛世的奠基者。在他统治下的清朝,百姓安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富强。
可偏偏这样一位天子,有那么一晚在棋盘上被逼得抬不起头。更蹊跷的是,那位把他困住的对手,只是个腰间挂刀的小侍卫。十天之后,这人倒在河边,再也没醒过来,皇帝转身留下一句八字重话,像一块石头丢进深井,回声至今还在。
时间往回拨到康熙三十七年。夏末秋初,北方的风已经带了凉意,车驾往木兰围场去。路过伊逊河,水色清亮,岸上的草半黄半绿,皇帝看着顺眼,说就在这儿歇营。帐篷一字排开,炊烟冒起来,夜一深,营地外侧就只剩水声和虫鸣。
这会儿最怕的就是无聊。御前的人都知道,主子要找乐子,陪着笑就行。有人端了棋盘来,几位红人被叫进去,手心里捏着汗也得装轻松。大家都知道规矩:君前无胜。棋盘上可以佯攻,可以虚招,但该让的那一步不能忘。不用多说,皇帝连赢几局,却赢得乏味——连连得手,挺像一碗过甜的粥,入口就腻。
“朝里没个能和朕对上手的?”他话不重,意思够明白。为了调动兴致,他干脆开口:谁敢赢,重赏,还有官阶上提。这话一出,帐中一阵静。赏是动人的,帽子更要紧,可真要下到收官,把皇帝逼在角上,谁敢?谁敢呢。
偏偏就有人站了出来。是个侍卫,年轻,眉眼不显锋芒,站久了身板挺得直,手背上有拉弓留下的薄茧。照旧例,像他这样的,没轮到他发言的份,可他往前一步,抱拳请战。康熙眼睛里闪了下光,像终于遇见个能把无聊赶走的人,挥了挥手:坐。
这人叫那仁福。书上没给他留下太多话,只记了个名字,其余像被风吹散。大概他自己的命,也没想到要跟一盘棋扯在一起。
开局没多久,场子里的味道就跟往常不一样了。那仁福下得很锋利,像练拳的人突然换了短刀。象棋在军营里不稀罕,他走的都是实战路数,直来直去,不绕圈子。皇帝的棋也不差,老练沉稳,一路挡拆,可那仁福盯住一个缺口,用力一拧,把对方的主力撕开,最要紧的那枚“车”被兑掉了。帐中人面面相觑,空气一下子凝住了。
那一瞬,你能感觉到皇帝的眉心绷了一下。不是怒,是一种不曾被预备的“被看见”。御前的大总管嗅觉最快,他不看棋盘,眼角已经抬向帐外。下一刻,声音从帘外掀进来:“前林里像是有猛兽!”喊声带着急,不像多想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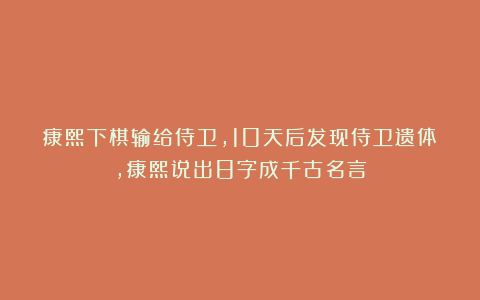
猎,是此行正事。皇帝起身,拿弓,马蹄声很快洒了一地。临走前,他只说了一句:棋别动,等朕回来再续。那仁福起身应声,退回棋边。
山林里没虎,倒撞见一头鹿。皇帝亲手放箭,鹿倒在枯草间,许多人跟着欢呼。风在树缝里吹,兴头一上来,队伍越走越深。夜里篝火明亮,肉香翻腾,笑声压过虫鸣。第二天再进,第三天再追。猎是一件容易让人忘了时间的事,尤其当每个人都在看你的脸色。
留在河边的那仁福,将军未落,棋没完。他也许以为,自己守着棋盘,就守住了皇帝说过的话。御营的人来来去去,送水的挑子总是往里帐走,菜汤热着先给上座的人。侍卫能不能自作主张去找口吃的?理论上是可以的,可谁能担得起“擅离”的名头?更何况,他是那个敢对弈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夜深了,河风凉得牙齿打战。第一夜他站着,第二夜他坐下,第三夜,他开始晕。到第五六天,人的念头会变慢,嘴唇裂开,指尖冻木。第十天,大队马蹄回返,河岸边已是秋凉深入骨头的冷。
康熙这才想起那盘棋,随口问了一句:“那侍卫呢?”身边的人互相看,谁也说不清。有人说,也许还在棋边守着。赶回去时,棋盘还在,棋子一动未动。人,已经仰倒在草上,身子硬了,脸上像覆了一层霜。
围着的人都不说话。风从帐篷的缝里刮,吹得火舌一卷一卷。康熙看了很久,开口短短八个字:“君而无信,何以为君?”声音不大,却足够每个人听见。你很难说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是心里真被撞了一下,还是在更大的棋盘上落子。
于是,很快有一纸自责的诏书出来,言辞诚恳,把责任揽到君王自己身上。那仁福的家人被寻到,赏钱和抚恤送去,礼数不薄。很多人由此更加敬服,说皇帝能认错,这是美德。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是能耐——把一个冰冷的结局包起来,给它套一层温暖的外皮,让它看上去像一段教训,而不是一个警告。
那晚的棋局,到底谁输谁赢?表面上棋未完,那仁福没“赢”。可更深一点看,他不该出手那么狠吗?不,他只是认了棋。问题在君前——这世上,总有些时候,你赢了棋,就输了命。御前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棋盘上留手,在话头上留白,在笑容里留出分寸。
那仁福没有。也许他懂事,但他更直;也许他笨,却笨得诚实。那个说“有猛兽”的人,没有多余的恶意吗?未必,他可能只是想替主子解场,给皇帝一个台阶。可台阶搭起来,往下走的是一个活人。再往后,所有人都学会了更娴熟的谨慎:当皇帝兴致上来,不要让兴致碰到锋刃。
有人问,为什么十天没人给他送一碗热汤?我也想问。军营里最不缺的是人手,跑个腿,一两句话的事。可是规矩像一道看不见的墙,墙后是另外一套气味:谁把食物递给那个“差点赢了主子”的人,等于在场面上承认他赢得漂亮。这口锅,谁背?谁愿意背?于是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别处,让风把一条命慢慢吹干。
也有人说,皇帝会不会真想一把公道,才特地回来续棋?这话太善良了。善良并不在这里无效,它只是在更大的秩序面前显得脆。皇帝说“无信”,既像是对自己,也是对所有听见的人:你们别学那仁福,别把“信”理解成执着守候的那种“信”。君要守的,是一种更方便拿捏的“信”——由他定义的、可以随时转弯的那种。
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是怎么教人活的。伊逊河边那具僵硬的身体,是一种答案。棋盘不大,命运很大,手指拨动棋子的声音很轻,背后轰隆作响的是制度与脸面。那仁福下棋的样子像他拉弓——动作干净,不怕痛。他也许以为,棋局就是棋局,没想到棋局就是世界。
如果那天没人喊“有猛兽”,又会怎样?皇帝会不会大笑一声,说好,重赏,让你做官;还是棋下到关键处,忽然收手,说改天再战?我们不知道。历史只告诉我们:那盘棋没完,人先走了。后来人说这是“人君的反思”,也有人说这是“高明的安排”。我总记得河风的那股凉,吹灭过一个年轻人的体温,也吹亮过一位帝王的名声。到底哪一个更重?这事儿,谁也替谁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