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4期】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
中国·辽宁·北镇
医巫闾山文学社
主编 程占全
岁月里的黄豆香
文/蒋秀英
梦圆医巫闾
初冬的早晨,冷风吹打着阳光房的塑料板,声音沉闷、厚重,跟村里哪个老头子咳嗽似的,告诉你,冬天来了。被窝里热乎乎的,人就跟赖在里面似的,蜷着,不想动弹。
忽然,村口那头,飘过来一声吆喝,又长又亮:豆——腐——
我“嗖”一下就坐起来了,那点懒劲儿全没了。拉开窗帘,南山顶上还罩着一层薄雾,东边天都白了,太阳正要冒头。前趟街,有的人家烟囱已经冒烟了。这日子,就算开始了。
我赶紧穿衣服,洗手、拿碗,趿拉着拖鞋就往外跑。还好,刚出大门,卖豆腐的驴车正好到门口。买了两块,捧着往回走,那股子豆香味儿,直往鼻眼儿里钻,比被窝里的热乎气儿还勾人。
我这个人,就跟黄豆有缘。豆浆、豆皮、豆腐脑、水豆腐、干豆腐、冻豆腐……只要是黄豆做的,我都爱吃。这毛病,打小就有了。
我记得,五月初,家家都要种黄豆。雨水要是调和,就种浅点,苗出得快。赶上春旱,就得深种,得让种子够着湿土,苗才能出全。我家自然也种。
十几天吧,小苗就拱出土了,就倆片子叶,嫩绿嫩绿的,看着就让人心里高兴。没几天,长出了真叶,开始分杈,叶子也密起来,颜色由淡绿渐渐地变成了墨绿。
到了七月,雨水足,黄豆就开花了。那小白花,不怎么好看,可小巧玲珑的,倒也逗人喜爱。
九月,天高了,云淡了,庄稼都熟了。黄豆在地里摇啊摇,墨绿的叶子慢慢变黄,一串串饱满的豆荚,就那么露在外面,风再大点,感觉就要“啪”地一声炸开。
所以,要是哪天早晨刮了南风,还带着点雾气,空气湿漉漉的,我爹娘就挑这么个天,天蒙蒙亮,带着早就磨好的镰刀、拧好的榆树条子,就下地了。为啥?就图个潮气,豆荚才不会炸开。
割完的黄豆,毛驴车拉回来,码在场院边上晾着。场院是黄土地,让多少年的碌碡给压得,跟石头一样硬。乡下人实在,一家一家挨着码,没人动别人家的东西。晾几天,水汽散了,豆粒都硬实了,就能打场了。
打场的时候,先把豆捆子解开,在场院上铺成一个圈。套上毛驴,毛驴眼睛得蒙上,不然它偷吃。我爹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扬着鞭子,嘴里“喔喔”地吆喝着。毛驴也听话,一圈一圈地走。走几圈,我爹就把毛驴牵到边上歇歇,自己卷根旱烟,吧嗒吧嗒抽两口。我妈就用耙子把脱了粒的豆杆搂到一边。这么来回几趟,豆杆上的豆子就都掉下来了,地上铺着一层金黄金黄的豆子。我和我妈撑着麻袋口,我爸用簸箕把豆子敛起来,走到一边,簸几下,豆荚皮、碎草、土末子就都飞出去了,剩下干净的黄豆,倒进袋子,扎好口,拉回家,搁仓房里。豆杆也得拉走,场院得扫干净,因为下一家还等着用呢。这是乡下的规矩,也是人情。
每次看到拉回来的豆杆,我就会想起那首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诗里说的是伤心事,可我们烧豆杆,不是为了煮豆,是引火。做饭,灶坑里先塞一把榛杆,再抓一把豆杆,火柴一点,“噼里啪啦”一阵响,混着草木香的饭味儿就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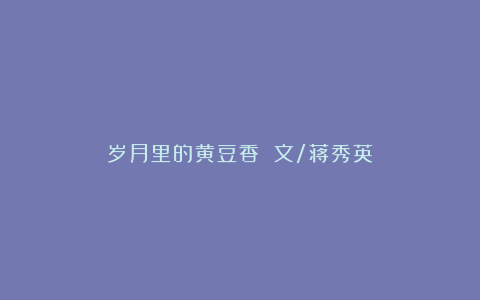
粮食都进了仓,一年的活儿就算完了。仓房里那几袋黄豆,爹娘心里都有数:哪袋是榨油的,哪袋是烀酱的,哪袋是做年豆腐的,还得留点,平时炒个盐豆,或者生点豆芽。
霜降一过,天就凉透了。爹娘张罗着去四十里地外的城里榨油。村里几户人家就约好一天走,路上有个伴,榨油时也能搭把手。那天,天还没亮,我和俩弟弟还在睡呢,爹就赶着驴车,拉着黄豆和几个空油桶走了。掌灯时分才回来,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从城里买的饼干和糖块塞到我们手里。现在想起来,爹娘顶着星星走,又顶着星星回,一整天,那饼干,他们怕是一块都舍不得吃吧。那几桶浓香的豆油,不只是一家人饭菜里的油星,那是爹娘对这个家、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心。
一转眼,就到冬月了,该烀大酱了。大酱,可是庄户人家少不了的东西。一家子要是没有个酱缸,是会让人笑话的,说这家人不会过日子。所以,我妈年年都把烀酱当一件大事。豆子得一粒一粒地挑,生怕混进一颗坏的,坏了酱的味道。烀豆子更得用心,火小了,豆子不熟,酱就没味儿;火大了,容易糊锅,串了烟,那酱就没法吃了。烀好的豆子在大锅里焖一宿,豆子变得红红的,油汪汪的。第二天,把豆子捣碎,摔成一块块长方形的酱块,用报纸包好,放在立柜顶上,让它慢慢发酵,等来年四月十八下酱。
那时候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外头冰天雪地。屋里却总是暖和的。我妈过些天就去仓房舀一碗黄豆,温水泡上小半天。黄豆吸水的过程有意思,先是起了褶,然后慢慢鼓起来,变得又胖又亮,看着就喜人。水沥干了,拿块干净布盖上,搁在炕头热乎地方。早晚用温水过一遍,两三天,豆皮就裂了,小芽就钻出来了,脆生生的。晚饭时,我妈用荤油炒了一大碗,就着高粱米饭,那是冬天里最暖和的味道。
小时候最盼着进腊月。腊月里天冷风大,雪也多,可一想,进了腊月就离过年不远了,那点冷,也就不算什么了。腊月里除了做粘豆包、杀年猪,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做年豆腐。
得提前跟豆腐坊定好日子。到了那天,我爸吃过早饭就把豆子送去,豆腐匠好提前泡上。做晚饭的时候,我爸端回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豆腐。水豆腐,就是刚点了卤,还没压成块的:白、嫩、滑。舀一碗,浇一勺我妈做的鸡蛋酱,那滋味,醇厚,香。现在想起来,嘴里还好像有那个味儿。
晚饭后,我爸用扁担挑回来两桶豆腐,我妈跟在后头,手里托着几张豆腐皮。豆腐皮是豆腐的精华,稀罕物。我妈把豆腐皮挂在仓房的秸秆上,让它慢慢阴干,留着过年或者来客了吃。
那两桶豆腐,我妈捡出一些,放盆里,加清水,留着凉拌或者炖菜。剩下的,一块一块摆在秫秸帘子上,搁仓房顶上。第二天一早,豆腐就冻透了。我妈取下来,码在南墙根的大缸里。过两天杀了年猪,炖一锅酸菜,放上十几块冻豆腐,这杀猪菜,才算有了魂儿。
我有三个舅舅在内蒙古库伦旗,老舅家在农村。姥爷姥姥搬过去后,发现那儿很少有卖豆腐的,姥爷就把丢下多年的手艺又捡了起来——做豆腐。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十四了。大舅到辽宁出差,顺道来看我们,跟我妈说:“我带秀儿去住些日子,她姥爷姥姥老念叨。”我就跟着大舅,头一回去了内蒙。那时候,那儿比我的老家还穷,没啥好玩的,就是一道道的黄土梁子。唯一有意思的,就是看姥爷做豆腐。不过,姥爷做的豆腐不好吃,颜色发黑,还硬,远不如我老家的豆腐白嫩、醇香。
没事干,我就跟着姥爷坐毛驴车去蒙古族人多的地方卖。车上放着两盘蒙着纱布的豆腐,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出去十里地才看见人家。进了屯子,姥爷就开始吆喝。不一会儿,就有个女人拿着小铁盆过来了,身后跟着四五个孩子,男孩女孩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有光着膀子光着脚的。那时候豆腐一毛钱一块,那女人递给姥爷几毛皱巴巴的钱。豆腐捡到盆里,我以为他们会端回家,没有。那女人拿起豆腐,掰成两半,一个孩子分一半。那些孩子,就跟吃饼干一样,几口就把豆腐吃完了。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跟着娘走了,心满意足的。走的时候,有个小女孩,还过来摸了摸我脚上的红塑料凉鞋,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几十年了,我总会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些像吃饼干一样吃豆腐的孩子,还有那个摸我凉鞋的小姑娘。姥爷的豆腐为啥发黑?也许是水的问题。为啥压得那么硬?也许是土路远,不好走,怕颠坏了。可我总觉得,或许,也是为了方便那些孩子那样吃吧。
豆腐,让黄豆换了一种活法,也丰富了人的饭桌。可我觉得,豆腐,也是另一种样子,另一种滋养。
现在,村里人种黄豆的少了,腊月里也很再有人家做年豆腐了。一年四季,什么菜都有,豆腐,反倒成了个稀罕物,偶尔买一块,也就是桌上配个菜。
可那股子黄豆的香味儿,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那不只是吃食的味道。那是土地的味道,是日子的味道,是爹娘辛劳的味道,也是那些蒙古孩子吃豆腐时,脸上的满足劲儿。人这一辈子,吃过的东西,走过的路,见过的人,都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就像黄豆,小小的,却能生出百般滋味来。这,大概就是岁月吧。
【顾问】汪玉铎 刘兴龙
中国·辽宁·北镇
传承北镇文明
弘扬医闾文化
打造地域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