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麻花花的故乡情
张文艺
晋北高原的风,总裹着山野清冽的凉意,漫过繁峙县的晨霭与代县的炊烟,轻轻落在每户人家的灶台上——那抹绕骨缠心的香,原是崖间的贼麻花。它生得素朴,无艳色招摇,登不得珍馐雅席,却藏尽山川灵秀与故土本味。指尖轻捻撒入滚烫油锅,滋滋声响里,粗茶淡饭便染了岁月温软,寻常烟火也添了几分鲜活清润,这样的滋味,成了刻在游子心头最暖的念想,任时光流转,始终未曾淡去。
贼麻花是山野养就的灵秀,扎根千米海拔的山巅沟坡,耐得住朔风割骨、烈日灼肤,偏在盛夏七月攒足气力,于崖间坡畔静静绽放。粉白细瓣缀着晨露,如撒落的星子藏在碧叶间,不争不抢,却把清浅香气漫过整座山塬,勾得人为之魂牵梦绕。
家乡代县鹿蹄涧村北,大沟河绕着崖塬蜿蜒流淌,九头十八嘴的沟壑纵横交错,向阳土坡的肌理间、崖壁细碎的缝隙里,皆是它眷恋的栖身之地。蛐蛐叫鸣刚撕开暑气的薄纱,村庄便浸在淡香里动了起来:白发老翁揣着粗布布袋,踏着晨露慢悠悠往坡上挪,脚步轻缓得怕扰了花间晨宁;扎羊角辫的丫头举着自制长杆,蹦跶着追着花影跑,笑声脆生生地撞碎晨雾,漫过沟谷;邻村乡亲亦寻香而来,身影散落在青黛沟壑间,弯腰拾撷、抬手轻捋,指尖拢起的不只是粉白花瓣,还有山野馈赠的暖。这幅浸着烟火暖意的采摘图,岁岁盛夏,岁岁如斯,最终成了故乡最鲜活的注脚。
儿时最盼的,便是跟着大哥大姐去北半坡撅贼麻花。熟稔山路后,一入暑假,便约着伙伴扎进村北九头十八嘴的山沟河川,踩着碎石路寻花踪。有时沿着沟崖奔走四五公里,脚掌磨得发疼,一天也只撅得半升升,却仍攥着布袋不肯停;为了多摘些,偶会奔到北山上的小沙梁,漫坡寻遍,到头来也只收得半碗碗,垂头丧气往家走时,肩头布袋虽轻,心里却揣着满当当的不甘,盼着下次能寻到更密的花簇。
后来听大人说,翟嘴的高崖上藏着成片贼麻花,只是崖壁陡峭,鲜有人能上去。我们几个小伙伴一碰头,当即组起“探险队”,誓要闯一闯这险峭秘境。老辈人常念叨“登上翟嘴嘴,麻花尽有有”,柳沟河水库横亘前路,唯攀绝壁方能抵达,也正因这份险远,那里的贼麻花少有人扰,长得格外繁密鲜嫩。出发前,我们瞒着大人悄悄筹备:削尖枣木做带钩长杆,磨亮锈迹斑斑的小铲,粗麻绳缠腰缠了一圈又一圈,兜里再揣几根脆嫩黄瓜当干粮,满心忐忑掺着难掩的雀跃,盯着窗外夜色,盼着天早日破晓。
天刚露微熹,晨雾似崖间薄霜漫笼石壁,湿凉气裹着草木清味扑面而来。大人们扛着锄头下田的身影刚隐入村口晨色,我们便如撒欢的小马,循着羊肠小道往翟嘴奔去。立在沟底抬眼望,崖壁如刀削斧凿般直插云天,羊头般粗藤盘绕石壁,似蜷卧的巨蟒静守岁月沧桑;野杨枝桠在风里轻晃,漾开呜呜清响,添了几分幽深。头顶老山鹰盘旋,锐利眸光扫过坡间,似在打量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童;喜鹊扑棱着羽翅,叽叽喳喳啼个不停,反倒像含着几分关切,拦着我们往前闯,可心底的执念,早推着脚步向前不肯退缩。
攀崖需寻野杨与山榆交错的险处,小铲往石壁轻轻一凿,碎土石簌簌坠下,落在沟底乱草间,悄无声息没了踪迹。每攀一步,掌心便沁出冷汗,粗糙树皮磨得掌心发疼,划出细小红痕,火辣辣的疼也顾不上揉拭,只死死攥紧枝干。拽着柔韧杨枝翻向山榆时,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沟谷,风从耳畔呼啸而过,心似悬在嗓子眼,连呼吸都不敢重些。抬眼望去,前方竟藏着一道雨水冲刷的浅沟,窄窄浅浅,恰似通往花海的秘径。我们屏住呼吸,贴着潮湿崖壁,如壁虎般一寸寸挪行,指尖抠紧石缝,指甲嵌进土粒,脚掌踩着仅容半足的石台,不敢有丝毫差池,终是凭着一股蛮劲,攀上了翟嘴塬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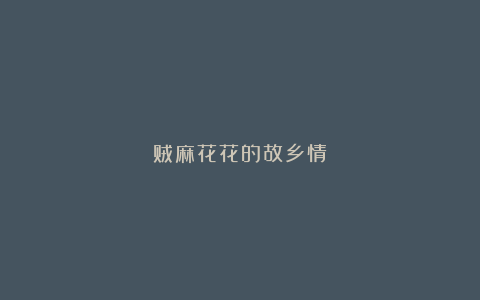
眼前骤然亮堂——四五亩葫芦形平塬上,贼麻花铺展成粉白浅浪,漫过视野尽头。花瓣或昂首绽露热烈,或敛瓣藏着羞怯,晨露缀在瓣尖,晃着细碎莹光,风一吹便轻轻滚落,坠进草丛里。风过处,花海轻漾涟漪,清甜香气裹着暖阳暖意漫涌而来,绕着鼻尖不肯散,恍惚间,粉白花瓣似踮足起舞的素衣女子,轻晃得人眼波微漾,连满身的累都淡了大半。“摘大朵的!”有人轻唤一声,我们即刻扎进花海,双手翻飞间,粉白花瓣簌簌落进布袋,指尖沾了清润花香,连额间汗渍都染得甘醇,满心满肺都是欢喜。
日头渐高,暑气漫溢,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浸湿衣衫贴在后背,凉丝丝的反倒沁着几分爽意。我们躲到伞状大榆树下歇脚,围坐成一圈,掰开揣来的黄瓜,清甜汁水漫过舌尖,混着布袋里贼麻花的香,成了童年最难忘的山野野餐,简单却满是滋味。风歇暑缓,抬眼望时,山河铺展如卷:往西眺望,姑姑嘴的梯田里、杏树林间,人影绰绰,吆喝声、山野小调顺着山谷飘来,脆生生绕着崖壁转。我们扯着嗓子喊:“登上翟嘴嘴,气死对面小妹妹!”对面即刻传来姑娘们的嗔笑:“小毛孩,当心山蚂蜂蛰你!”我们吐着舌头做鬼脸,笑声惊飞树梢黄翠鸟,扑棱棱羽翅声混着风吟,轻落在满坡繁花间,漫过沟谷,漾着少年时光的鲜活。
立在翟嘴北坡高处,夏日暖风轻拂肩头,柳沟河百亩库面映入眼帘。库岸边一排垂柳亭亭玉立,枝条轻舒漫舞,倒映在水中,随波漾开细碎光影。深绿色的水面上,风起时便掀着层层涟漪,三五成群的白鹭舒展双翼,在水面低翔盘旋;几只白色捞鱼鹳鸟骤然扎进水中,又倏然跃出,尖喙间叼着银亮小鱼,振翅奔向远方。受了惊扰的小鱼纷纷跳出水面,银鳞闪过,似撒落的碎玉,拼命向深水区逃亡。对面水库石坝边,四五个少妇正捶洗衣物,木槌起落间溅起晶莹水花;两个小女孩牵着一条黄毛小狗,在岸边浅滩戏水,笑声与水声交织,酿成一幅鲜活温润的乡野画卷,看得人心底发软。
抬眼向南远眺,巍峨挺拔的五台山脉自东向西横亘天际,黛色山峦叠着淡雾,藏着万千气象;正南马鬃山的尊容大佛静立云端,眉眼慈爱,似凝望着故土生灵,护佑一方安宁;东南五台山巅覆着淡紫岚气,偶有七彩佛光轻漾,漫洒山川大地,圣洁又温柔。山川中一条素带轻飘而下,自东向西蜿蜒远去,柔婉缠裹着崖塬沟壑——那哪里是素带,原是滋养故土的母亲河——滹沱河!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村庄藏在葱郁林莽间,袅袅炊烟轻腾而起,缠裹着烟火暖意漫过屋顶;田垄间,翠绿庄稼迎风轻摇,高粱缀满红穗,玉米挺出嫩缨,谷子垂着饱满穗子,丰年盛景尽数铺展眼底。望着这般山河秀色,方才攀崖撅花的疲惫,竟悄悄散了踪影,只剩满心的澄澈与骄傲。
撅贼麻花藏着祖辈传下的门道,是与自然相守的温柔默契,已然刻在每个家乡人的骨子里。零星生长的,单手轻捻花瓣,指尖力道放得极柔,莫碰损分毫,留得花株再续生机;长势繁茂的,双手齐拢轻捋,动作缓柔似抚易碎珍宝,不贪多、不滥采。“三不怕”“三小心”早记在心间:不怕骄阳灼红脸颊,不怕荆棘勾破裤脚,不怕蚂蜂绕耳嗡鸣;要当心空心崖壁,踏之易滑坠险,每一步都要踩实;要避让草丛菜花蛇,莫惊扰山间生灵,远远绕开便好;要绕开崖缝马蜂窝,免得遭蛰添痛,护着自己也护着蜂群。每摘一朵,皆是与山野的倾心相待,藏着对故土生灵的敬畏,也藏着祖辈传下的处世之道。
布袋装得鼓鼓囊囊,粉白花瓣溢到袋口,指尖仍沾着化不开的香。太阳西斜时,余晖洒在崖壁上,染得石壁泛着暖橙,便该返程了。下山比上山更险,我们将布袋顺着崖壁轻放沟底,生怕碰损花瓣,再握紧腰间麻绳,脚踩石缝缓缓挪行,每一步都凝神聚力,不敢有半点马虎。待最后一人落至沟底,众人皆瘫在软绵草地上,大口喘着气,听着彼此急促的心跳,望着头顶澄澈蓝天,云朵轻飘,满身疲惫尽散,只剩满心欢喜——我们攀上了翟嘴,摘到了最鲜的贼麻花,成了自己心中的小英雄。
归至家中,贼麻花的香漫了满院,绕着鼻尖绕进心底。奶奶佝偻着脊背,坐在院中小凳上分拣花瓣,枯瘦手掌轻抚过粉白花瓣,仔细挑去枯叶碎枝,浑浊眼眸里满是欣慰,嘴角噙着浅淡笑意;母亲系着素色围裙在灶台前忙碌,金黄炒鸡蛋、软糯素糕次第摆上桌,待油锅烧得滚烫,抓起一把鲜花瓣撒进去,“滋啦”一声,浓香瞬间涌满全屋,裹着烟火气,勾得人直咽口水。一家人围坐桌前,红面鱼鱼裹着贼麻花的清鲜,滑进喉咙,暖意从舌尖漫至心口,熨帖得浑身舒畅。笑声裹着花香飘出院子,撞得院外老榆树叶片轻晃,簌簌作响似应和,岁岁年年的烟火暖,大抵便是这般模样。
岁月匆匆流转,当年的稚童已踏过半生烟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日子过得步履匆匆,车马喧嚣里,总念着那抹崖间清芬。每当家乡亲友捎来贼麻花,指尖捻起柔软花瓣,熟悉的清甜漫涌鼻尖,记忆便如潮水般翻涌:晨露里老榆树的淡香,早春野小蒜的辛鲜,秋天酥梨的甘醇和甜如蜂蜜的脆枣,还有母亲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奶奶院中分拣花瓣的模样,少年时攀崖寻花的执念,乡亲们山间采摘互相照应的暖……眼眶不觉间便有了湿意,乡愁顺着花香蔓延,缠着故土,绕着牵挂,不肯离散。
贼麻花的香,早已刻进我们血脉深处,融在岁岁年年的牵挂里。它不只是舌尖萦绕的滋味,更是乡愁的信物,是故乡的印记,像柔软的绸带,一头牵着漂泊在外的游子,一头系着魂牵梦萦的故土山河,岁岁年年,从未间断。唯有在那片黄土坡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才懂这方寸花瓣里,藏着最浓的故乡情,藏着一辈子都褪不去的暖,藏着此生难忘的故土岁月,藏着无论走多远,都牵挂不已难以忘怀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