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长沙子弹库被盗掘出土的帛书(或称“楚帛书”),是迄今仅见的战国缣帛古书,弥足珍贵。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盗出帛书的墓葬(73长子M1),据其中剩余文物判断,该墓属战国中晚期之际,帛书成书的时代下限也可依此认定。帛书中不仅记载了战国楚地流行的古史传说,更以当时的宇宙论为背景框架,叙述了带有五行思想特点的天象灾异等数术内容。《汉书·艺文志》曾将先秦时期的这一流派思想归为阴阳家,可惜所载《宋司星子韦》《公梼生终始》等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古书久已亡佚,以至后世对阴阳家的学说了解甚少。子弹库帛书的出土和材料的公布,拉开了战国阴阳家学说研究的帷幕,中外学者长期热衷讨论,研究成果丰硕,近年出版的《楚帛书诂林》《子弹库帛书》等,对相关研究和图像著录又集以大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基础条件。加之近二三十年来,楚地出土战国古书倍蓰于前,时有相关新知增益,尤其是最近刊布的清华简《四时》《司岁》《五纪》等重要数术文献,其抄写时代与子弹库帛书大致相当,内容关系也极为密切,有不少可以相互印证的内容。因此,我们觉得很有重新讨论这件珍贵古书的必要,以期能进一步揭示当时阴阳家学说的特点,尤其是澄清与宇宙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帛书构图顺序与《四时》篇中创世传说时间概念的生成逻辑
子弹库帛书按构图可分三部分,过去大家习惯以甲、乙、丙篇称引其文。但由于诸家对甲、乙两篇的先后顺序理解有别,为避免混淆,我们认为李学勤、李零等先生以文义为题的方式较为妥当,也符合古书通例。关于各篇的定名,中部书写方向互倒的两组文字,即常被颠倒称引的甲、乙篇,八行的一组以“四时”为中心,两位先生都题为《四时》,可从。十三行的一组根据李守奎先生最新的研究,是以“理岁”为中心,可题为《理岁》。四周排列附以绘图的十二段文字,经李学勤先生考证,与《尔雅》所记十二月名相应,这些月名现又见于清华简《五纪》,这一部分可按李零先生意见称为《十二月》(即“丙篇”)。
帛书的构图是与当时宇宙方位观密切相关的。左旋排列书写的《十二月》,应以左春——东,上夏——南,右秋——西,下冬——北为正向。从同时或时代相近的出土材料来看,这一方位可以与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五纪》所述之“天纪图”,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楚地出土的古图相印证。比如《筮法·卦位图》四周文字按左——上——右——下的顺序依次记有“东方也,木也,青色”“南方也,火也,赤色也”“西方也,金也,白色”“北方也,水也,黑色也”,即为明证。如此,三组文字内容可依《四时》《理岁》《十二月》的次第阅读。
然而,如果从时间单位由大至小的一般逻辑来看,将《四时》篇排在《理岁》篇之前似乎有所矛盾,这也是过去学者们对所谓“甲”“乙”二篇排序有别的问题所在,以至于李零先生后来为了调和此矛盾认为帛书“没有固定的视角”。其实,当我们回到帛书文本中就会发现,《四时》《理岁》《十二月》亦符合帛书内容的叙述逻辑。试看下面这条线索,《四时》篇先载:
未又(有)=(日月),四神【第三行】相弋(代),乃(时)以为(岁),是隹(唯)四寺(时)。
继而又称:
千又(有)百(岁),=(日月)【第四行】允生,九州不坪(平),山陵备(倾)。
可见“日”“月”后于“四时神”诞生,且它们诞生的过程是在《四时》篇里先行介绍的。而《理岁》篇则曰:
=(日月)星辰,(乱)(失)亓(其)行。【第一行】
=(日月)(皆)(乱),星(辰)不[同]。=(日月)既(乱),(岁)季【第七行】乃□,寺(时)雨进退,亡(无)又(有)尚(常)(恒)。
这已然是在描写“日”“月”诞生之后的情景了。如果以“日”“月”生成的记述作为参照,显然也是《四时》篇在前,《理岁》篇在后。
上述内容不仅有助于我们确定帛书构图方向,进而明确当时的宇宙方位,而且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帛书所载时间概念的生成顺序。最先出现的“四时”,是由“太一包戏”(即伏羲)与“女填(真)”(疑即女娲)所生的四子。此时尚未有“日”“月”,是靠“四神相代”的一个周期来确定“岁”。这里的“岁”不是指“岁星”“太岁”,其含义是回归年的时长。于此“千有百岁”之后,“日”“月”方才诞生,“月”的时间概念才形成。由这一套创世传说总结出来的时间概念生成顺序,也是以“四时——岁——月”为先后。
这一次第与古人对时间认识的一般规律并不相符,尤其是在没有“日”“月”的情况下先有了“四时”。然要注意的是,这组时间概念已被披上创世神话的外衣,在清华简《五纪》中,“日”“月”等二十四位被称为“群祇”,而与“四时”关系更紧密的“四维”等十八位则被称为“群神”。帛书的这套时间概念生成逻辑,其实反映了古人在特定宇宙论系统框架中创造代表时间概念的神明的先后次第,以及神明地位的高低,其对文化研究的价值不容忽视。
二、从“天柱”与“四柱”看帛书宇宙论的系统框架
位于创世传说《四时》之后的《理岁》篇,内容更为复杂,涉及的当时天文数术思想也更为丰富,部分核心概念我们过去颇不理解,现在可以提出一些新认识。由于后面将要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理岁》的首章,现将此释文抄录如下(重点讨论的内容划线标出):
隹(惟)[■■]日月,则(盈)绌不(得)亓(其)(常)。旾(春)(夏)(秋)(冬),又(有)□(失?)□(亂?)尚(常)。=(日月)星辰,(乱)(失)亓(其)行。(盈)绌(失)[](乱),芔(草)木亡(无)【第一行】尚(常)。□[■]夭(妖),天(地)乍(作)羕(祥)。天(柱)(将)乍(作)(荡),降于[下]方。[■](使?)山陵亓(其)(废),又(渊)乃渴(竭),是胃(谓)=[=](理岁。理岁)[■]月,内(入)月【第二行】=(七日)[=(八日),乃]又(有)雺(雾)(茫)雨土,不(得)亓(其)参职(识)。天雨彭=(滂滂),[是胃](谓)(失)月,闰之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胃](谓)(失)(终),亡【第三行】奉,[■■]亓(其)邦。四月、五月是胃(谓)(乱)(纪),亡(厉),□□□(岁)。西(域)又(有)吝,女(如)=(日月)既(乱),乃又(有)鼠[■]。东(域)又(有)【第四行】吝,□□乃兵,(害)于亓(其)王。【第五行】
第二行“天(将)乍(作)(荡),降于[下]方”句中的“天”一词,过去受到图像质量和文字认识的影响,曾被误释为“天棓”等,认为是《开元占经》所记之彗星等星名。后来李零、何琳仪等先生正确隶定出了“”字,另提出“天鼓”说。李学勤先生则进一步总结相关文字资料,指出“”乃“梪”之繁写,并提出了“天柱”的读法,但仍将其看为星名。
《五纪》将“四梪”与“天”“地”“四荒”“四冘”“四维”并称为“羣神十又八”,可总结为“宇宙神”。简文明确记载“四梪同号曰天梪”,这里的“天梪”才应是帛书之“天”。
“四梪”之“梪”在《五纪》中还有“”“”两种异写,整理者皆读为“柱”。注释中对“四柱”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谓支天之柱。《淮南子·地形》:‘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其二:“传说中撑地的四根支柱。《博物志》卷一:‘地下有四柱,四柱广十万里。’”所援引的《淮南子·地形》之“天柱折,地维绝”句,旧注引文皆作“天维绝,地柱折”,其中或许有讹传的情况。然从“天柱”这一名号来看,“支天之柱”的看法无疑是更合理的。帛书“降于[下]方”句第三字有残损,过去被释为“亓(其)”,陈媛媛女士改释为“下”,可信。“天梪”在上,方能“降于下方”,亦可视为佐证。
在我们看来,《五纪》中“四梪”“天梪”也可读为“四树”“天树”,这在语音和用字习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作为宇宙神,从其功能职司来讲,读为“柱”是恰切的,它起支撑天、地的作用;若从具体形象看,则可读为“树”,就是指帛书四隅所绘的四棵神树。两种读法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时人用此名称也极可能是一语双关的。研究帛书的学者早已提出四隅之树是“承天之柱”的看法,只是多将之与上篇《四时》提及的五色木相关联,二者虽并不是完全无关,但其数目无法相合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如今我们根据《五纪》知道“天”有“四”,对于帛书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遂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
从《五纪》内容看,“四柱”这一组概念兼有宇宙方位和神明名称双重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帛书上与四棵树临近而位于四边的《十二月》内容,分别配有十二位神像,同用绘画方式表达的四棵树,在性质上很可能与十二神像相同,也是四位神明。如果这一看法不误,那么帛书的“四树”与《五纪》的“四柱”在神明属性这一点上也是吻合的。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下面为不至于行文混乱,我们仍从其功能职司出发,统一将“梪”“”读为“柱”。
帛书将“四柱”绘于角隅位置,为我们认识《五纪》之“四柱”的方位提供了直接依据。大家知道,《五纪》中所载“四柱”只见有二“东柱”和二“西柱”,从《五纪》通篇的系统性看,这一现象最初显得十分费解。然若晓得“四柱”位于四隅方位,则东南、东北二柱皆可称“东柱”,西南、西北二柱皆可称“西柱”,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此外,帛书《理岁》篇首章还提到“西(域)又(有)吝”“东(域)又(有)吝”云云,也具有只言东、西,不见南、北的特点。将二者结合来看,这段内容也很可能受到了“天柱”“四柱”概念特点的直接影响。
上引《五纪》(简三七–三九)的内容已反映出,十八位“宇宙神”是以“天”“地”“四荒”“四冘”“四柱”“四维”为排序,《五纪》通篇在涉及这组概念时,都严格遵守这一次第,足见其排序是有深意的。其中“天”“地”“四荒”总是成组出现,又被合称“六合”,由此可以悟知“合”是取“合拢”“合围”之义,指“天”“地”“四荒”建立起的一个三维空间(或可表达为一个六面体),代表宇宙总体空间。经比对,“四荒”具体名为“大和”“少和”“大乘”“少乘”,它们尚没有东、南、西、北之分,似乎意味着“六合”还处于“混沌”的状态。“四冘”简文明确指出是天之东、南、西、北四正方向,与《淮南子·天文》等所载“四仲”含义相近,是具有方向坐标功能的大神。方位建立好以后,要用“四柱”稳固对“天”“地”的支撑。最后在天球上布置“四维”,由于天球不停旋转,正向和隅向之间不停转换,故“四维”含有正向、隅向双重内涵,《七谏·自悲》:“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王逸注:“天有八维,以为纲纪也。”所谓“八维”正是双重内涵的反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明确“天柱”在当时的宇宙观中具有稳固空间的重要作用,更可以推拟出一幅宇宙框架的三维结构图,如图1。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一个观测者的概念,《五纪》中所载的“后帝”或即其代表。古人以面南背北为尊位,如《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后帝若位于天顶中央,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俯视宇宙,其所见场景转化为二维的平面图,方位正与子弹库帛书的构图以及《五纪》整理者推拟的“天纪图”相契合。二者显然是同一宇宙观下的产物。
图1 推拟楚帛书、《五纪》中的宇宙框架结构图
三、《理岁》篇之“亡奉”“亡厉”与岁星纪年系统
宇宙论的一个现实意义在于诠释天文星象的变化机理,从而指导观象授时。帛书《理岁》篇正是在这套宇宙论的支配下,来解释“太岁”等运行的特点及其纪时意义。第二行“是胃(岁)”是本篇的中心,也是关键疑难。从韵文角度出发,我们赞同“”后“(岁)”字下也有重文号的推断,将“岁”合在一起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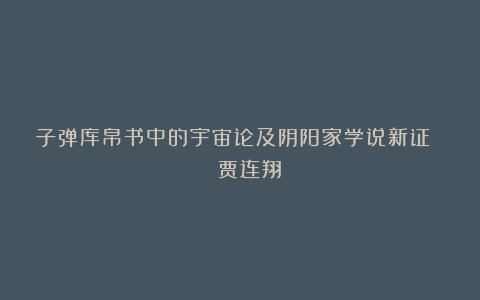
“”字过去长期被误释为“孛”,理解为悖逆、彗星等,因能顺接文义,影响很大。随着战国文字材料的增多,学者们相继正确指出此字就是楚文字中的“李”。郑刚先生进一步指出“李”指天理星,或称“天李”等,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天李》等,是数术中的重要禁忌项目,是可信的。
“理岁”之“岁”应指“太岁”。大家知道,由于岁星(木星)运行的方向与将黄道等分的十二辰(十二支)的方向相反,所以古代天文假设了一个岁星,与实际岁星运行相逆,仍像岁星一样以十二年运行一周天,这样就可以与十二辰相配合。这个假设的岁星在先秦时也称为“岁”,如后文所引清华简《司岁》中的“岁”。而其更明确的名称则是“大岁”“太岁”(《尔雅》《汉书》),或称太阴(《淮南子》)、岁阴(《史记》)。太岁也有神明之属性,古代数术家认为凡太岁神所在之方位及与之相反的方位,做事均有禁忌。过去认为这类思想起源于汉代,根据重新梳理的帛书内容来看,这一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然形成。
更关键的意义是,由于假设出的“太岁”配合了十二辰的方向,从而催生了影响重大的“岁星纪年法”,它能更好地顺应天时,因此太岁也同时具有积极的一面。过去学者已发现帛书“德匿”一词是可作正面和负面双重理解的,在我们看来,这正与“太岁”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相吻合。
《理岁》篇的“岁”指“太岁”其实还有进一步的佐证。首章第三行末至四行首的内容颇不易理解,诸家句读分歧较大,前文所引我们所作的释读与大家都不相同,主要根据在于“亡奉”与“亡”两个词出现了新的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清华简《四时》后面有接续抄写的一组关于十二岁的内容,二者原为一卷竹书,整理者将后者拟题为《司岁》。《四时》与《司岁》分讲天文数术的不同方面,前者以日、月运行规律为中心,后者则以“岁”的运行为基础,二者是否应该分为两篇,还可另作讨论。《司岁》起首曰:
(凡)行水旱火疾兵(丧)死之道,正亡丰、亡万、六(辰)以为纪。亓(其)六(辰):一为(哉),二为上寺(时),三为中寺(时),四为下寺(时),五为(间)。
(凡)六辰司(岁):(摄)(提)之(岁)……
《尔雅·释天》:“大岁在寅曰摄提格……”因此这里的“岁”显然也是指“太岁”。《司岁》以十二岁所值之辰对“水旱火疾兵(丧)死”等进行吉凶占断。简文明确说“六辰”是指“(哉)”(简文又称“受序”)“上时”“中时”“下时”以及二“间”。与“六辰”并列的“亡丰”“亡万”(简文“万”字或作“厉”,本文后面皆以“亡厉”代称),明显是与“六辰”性质相当的专门术语。根据“凡六辰司岁”这一总领句子还可分析出,在占断过程中,“六辰”起主要作用,“亡奉”“亡厉”只是辅助。
“奉”从“丰”声,故帛书之“亡奉”可与《司岁》之“亡丰”相通(本文后面皆以“亡奉”代称)。帛书“亡砅”之“砅”原从厂、水,作“”形,是饶宗颐先生所释,称:“为濿别体,见《说文》。”楚文字之“石”旁常省为“厂”,现已成为常识,这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诗》曰:‘深则砅。’’濿’,砅或从厉。”“濿”则是形声字。《说文》引《诗》文见于今本《邶风·匏有苦叶》,作“深则厉”。“亡砅”显然与《司岁》之“亡厉”也可相通。倘若“亡奉”与“亡砅”各自单出,上述通读恐怕也仅仅是一种猜测,但其成对出现,又与“岁”之记载相关,二者的对应关系应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奉/丰”“砅/万/厉”的本字为何,由于是专门术语,颇不易定,此暂付阙疑。
关于“亡奉”“亡厉”的具体所指,简文有清楚的介绍。《司岁》注释已指出:“无丰,十二岁所属地支有子、丑、辰、未、申、酉。无厉,十二岁所属地支有寅、卯、巳、午、戌、亥。一岁之中,无丰和无万所属地支共有六个。”这是严格总结《司岁》内容而得出的结论,其情况可参看表1。其中“亡奉”对应的“子丑”“申酉”,与“亡厉”的“戌亥”“寅卯”,都有两两相隔的规律,而“辰巳午未”四者的分配则有所不同。子居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现象,认为简文当有错讹,并提出“亡奉”当恒定在“子、丑、辰、巳、申、酉”,“亡厉”当恒定在“寅、卯、巳、未、戌、亥”。情况是否如此,目前尚无法肯定,还有待更多线索加以验证。
表1 六辰、亡奉、亡厉司岁表
由《司岁》得知,“亡奉”“亡厉”代表了固定的辰(支),借此反观帛书一、二、三月的“亡奉”和四、五月的“亡厉”,就会发现它们是对特殊日子的表述,即指在不同的岁次一些固定“地支”的日子。其后的文句虽已残损,但应该也是负面的意思。这与帛书四周《十二月》所记禁忌内容性质是一致的,也与《日书》类文献以干支择日进行吉凶判断的方式如出一辙。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本文下一节所引睡虎地《日书》的《土忌(一)》和《门》中,“入月七日”紧随的“春戌”“夏丑”“秋辰”“冬未”,也是以固定的“地支”相称,这与后面大量出现的以“天干”称日区别明显。在战国晚期楚地的九店56号墓出土简册中,《建除》《成日、吉日和不吉日宜忌》《裁衣》等是以“天干”称日,《丛辰》《五子、五卯和五亥禁忌》《占出入盗疾》《生、亡日》等是以“地支”称日,与之区别特征相同。
“亡奉”“亡厉”专用于“十二岁”,极可能属于岁星纪年法系统中的术语。而“一月”“二月”“三月”与“四月”“五月”,应是指帛书四边《十二月》之“取(陬)”“女(如)”“秉(寎)”和“余”“(皋)”五个月份。屈原在《离骚》中介绍自己生日时采用的也是岁星纪年法,其文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可见“摄提”等岁星纪年与“陬”等十二月纪月法在楚地也确实有使用,应与“荆夷”等楚月名是并行的。前面提到的以“天干”称日的九店简《建除》等内容,往往与楚月名并出,而以“地支”称日者则无见。与此同时,鉴于“摄提”等星次名与“陬”等月名又每每同时出现,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帛书与《尔雅》《五纪》所载的十二月名,连同“亡奉”“亡厉”所代表的“地支”称日,很可能都是属于岁星纪年法系统的特点,即这一纪年法有一整套专用的岁次名、月名和称日术语。
此外,清华简《筮法》第二十三节《果》载:“凡果,大事岁在前,果;中事月在前,果;小事日乃前,果;其余昭穆,果。如卦如爻,上下同状,果。外事数而出,乃果;内事数入,亦果。”整理者认为:“’岁’’月’’日’在前,疑指所值干支在卦象的上卦出现。据此当时似已有用干支纪月、纪年的制度。”这种干支纪月、纪年的制度,很可能也与岁星纪年法密切相关。
四、“入月七日”与清华简《四时》的“三十七时”设日
在“亡奉”“亡厉”之前,《理岁》篇在第二行末至第三行首清楚地记载了“内(入)月=(七日)”这一特殊日子,显然也应是别具意义的。合文“=(七日)”下有两字残损,上字仅余上部似“八”的两个笔画。两字缺文李零先生拟补为“八日”,被大家普遍相信。李先生曾简单提及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与“入月七日八日”相似文例,揣想主要是指《日书》甲种《鼠襄户》:“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日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这里的“七日八日”是置于全月之中的两个一般日子,而帛书中所述是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且与天文星象相关,二者虽在语言表述上有可比性,但就性质而言,区别十分明显。
清华简《四时》为“入月七日”等日子的特殊意义,提供了系统的解释。这篇简文是以观测日、月的周年视运动为基础,详细记载了一些特定日期的星象风候。它将全年设为十二个月,起始月在“孟春”,并将四时中的三月分为孟、仲、季,方式与《吕氏春秋》等相同。在将一年分为十二月的同时,《四时》又建立了“三十七时”的概念,第“一时”就是以孟春七日为始,“二时”在孟春十七日,“三时”在孟春廿七日,其后各时皆定在每月的七日、十七日和廿七日。以“孟春”之月为例,其文曰:
孟旾(春)受舒(序),青(气)乃。内(入)月四日,东风,青云,(解)冻,寒门乃(暆),奴(如)不至,玄维乃需。七日一寺(时),四(辖)皆[](逾),[■■■]。【简二】=(八日),(征)风(启)南。十{四}日,啬以,必又(有)取。十四日,东叙(舍)乃发,天(帑)乃章,(征)乌北行。十七日二寺(时),(俊)风乍(作),四维[■■,■■]【简三】之云宾。廿=(二十)日,四门皆癹(发),东风乍(作)。廿=(二十)四日,四门皆(逾),洹雨乍(作),以生众木。廿=(二十)七日三寺(时),四钩皆(解),玄维乃(盈),以(惑)(阻)亓(其)(笃)。【简四】
通观《四时》各月所记日子,除每“时”所在的七日、十七日、廿七日外,朔、十、廿日三个旬日,以及其中间的四、十四、廿四都是固定的观测日期。唯独在全年起始的孟春之月见有一次“八日”的风候,故整理者疑其为“衍文”。倘若我们联想到帛书这处缺文,从特殊日子的角度或可建立二者的联系。但需说明的是,依帛书的抄写特点及行款,“=”采用合文,“八日”亦当如是,这样其后还容有一字之阙,按此思路,另一字可补为“乃”之类的连词,属下为句。当然,“=(八日)乃”的补文由于具有很大推测性,尚不足为据。
单就帛书清晰记载的“入月七日”而论,已足可与清华简《四时》以“仲春七日”作为“三十七时”起始的情况合观了。根据“三十七时”的设日特点,每时10日,全年实际只需有三十六时,剩下的第三十七时,简文称:“卅=(三十)七寺(时)日乃受舒(序),乃(复)尚(常)。”我们认为这一时是为了调和360日的四时设日周期与回归年365.25日(不计岁实)的时长之差而设立的。第一时从“仲春七日”开始,只有7日,也需要依靠上一年的第三十七时来补足,具体调整方式已超出本文所论,我们将另作说明。
以“孟春七日”为起始的设日方式,直接影响了每月七日的特别地位。在择日类数术文献中也屡见此特点,比如睡虎地11号墓《日书》甲种《土忌(一)》曰:
凡入月七日及夏丑、秋辰、冬未、春戌,不可坏垣、起之,必有死者。以杀豕,其肉未索必死。【简107壹】
正月丁庚癸,三月四月丙己壬,五月六月乙戊辛,七月八月甲丁庚,九月十月癸己丙,十一月十二月戊辛甲,不可以垣,必死。【简108壹】
从中不难看出,所记之日以干支纪日为基础,或称地支,或称天干,唯独“入月七日”一处,是完全不同的纪日表达。相似的情况还可举同书的《门》:
入月七日及冬未、春戌、夏丑、秋辰,是胃(谓)四敫,不可初穿门、为户牖、伐木、坏垣、起【简143背/24反】垣、勶(彻)屋及杀,大凶;利为啬夫。
丁亥不可为户。【简144背/23反】
放马滩1号秦墓《日书》乙种亦曰:
凡入月七日及春戌、夏丑、秋辰、冬未,不可垣及□【简363】
其中“入月七日”也是独立于其他干支纪日的特殊纪日。另值得注意的是,睡虎地11号墓《日书》乙种的《亡日》《亡者》二篇,均以“正月七日”为首列之日,恰可与“孟春七日”相对应。上述文献的出土地除放马滩外皆属楚国旧地,从与其同出的睡虎地《日书》甲种《日夕》所记秦楚月名对照等资料看,秦楚设日应有一定的传承,因此,上述情况的出现恐怕也不是巧合。
根据清华简《四时》的记载,在每月的固定日子,可以通过天象观测来明确四季变化,预测参验天气风候。帛书在“入月七日”等后面紧接着讲“又(有)雺(雾)(茫)雨土,不(得)亓(其)参职”。“雺(雾)”周波先生已正确释出。“职”我认为当读作同从“戠”声的“识”。《诗·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得其参识”意谓“(混乱的天象气候)无法得到准确的参验辨识”,这正是天象不时的又一反映。
总之,以“入月七日”为特别标记的“三十七时”设日方式,现在看来,并非清华简《四时》所独特拟构的模式,它应该已被战国时人广泛使用。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文献所见“入月七日”每每与“地支”称日并举,反映了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帛书兼采“入月七日”与“亡奉”“亡厉”,亦可视为这种天文数术理论影响深刻的反映。
结语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其中“大祥而众忌讳”和“序四时之大顺”是司马谈总结的阴阳家的核心旨趣。从上文讨论的几个问题中也不难看出,它们也是子弹库帛书内容的典型特征。
帛书出土至今已八十多年,过去碍于帛书的残破及其内容的专门,不少句子无法确解,一些关键概念长期得不到准确的认识。新出的清华简《四时》《司岁》《五纪》等战国竹书,为这些内容提供了新的证据,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战国时期阴阳家所关心的“大祥忌讳”和“四时大顺”,背后依凭的是一套系统的宇宙论和极为丰富的天文数术知识。其中既充满了神话色彩和愚人的灾异迷信,但也明显包含着一定的科学要素,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发掘。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