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马鹤逸 信古斋 2025年10月12日 18:54 江苏
戚思悲,愿见忠,君不悦相思,愿勿绝。
戚思甚,悲欲见,勿说相思,愿勿绝。
大意:心里的愁思那么戚切又悲伤,想要再见一面,向夫君展露衷肠;如果你再也不愿与我像从前那样相互爱慕思念,那么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要从此与我永不相见。
铭文体现了一位被抛弃的女性,内心哀愁婉转,希望向爱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即便最终不能挽回爱情,也希望能够守在曾经的爱人身边。
又有几种比较典型的“相思”镜铭如:
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情,长勿相忘。
大意:道路是那么的长远,中间还有关口和桥梁相阻隔;照镜子也不能抚慰我的深情,希望你(远行的恋人)千万别把我忘记了。
秋风起,使心悲;道路远,侍前稀。
秋风起,予志悲;久不见,侍前稀。
大意:萧瑟的秋风扬起,让我的心那么悲伤;你离开家那么遥远/那么久没有见到你,(我不在)还有谁在跟前侍奉你、照顾你呢?
忽以觉,寤不得。但自欺,私太息。
大意:忽然从美梦中醒来,再想回到梦里怎么也睡不着了。(罢了,罢了!)做梦不过是在自欺,梦醒后徒留下深深的叹息罢了!
长勿相忘兮久相思,伏念所欢兮无穷时。
大意:别忘了我呀,让我们相互思念;想到过去相处的欢乐时光,真希望那些日子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在这些镜铭所表达的意境中,女性的地位在两性关系中都处于比较卑弱的地位,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感情来打动对方,与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认识相同。
不过,今天介绍的这面铭文镜,其中所表达的意境却与上述镜铭大不相同。我们来看看这面铜镜的样子。
此镜出土于山西榆次猫儿岭古墓群,系笔者前时参观晋中市博物馆“榆次猫儿岭古墓群出土文物特展”时拍摄的。由于猫儿岭古墓群的发掘报告迟迟未出,因此此镜的出土背景信息与尺寸规格均不得而知,目测大概在13-14厘米上下,大约合汉尺六寸。
镜的形制是非常典型的西汉晚期重圈铭文镜样式,此类镜肇始于西汉中晚期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至西汉晚期非常流行,新莽以后逐渐式微。
圆形,圆钮,连珠纹钮座,主纹饰为两圈环绕式的铭文带,铭文均为顺时针读。内圈铭文八字,每字中间以圆涡形云纹间隔,其铭曰:
见日之光,长毋相忘。
外圈铭文二十九字,其铭曰:
君行有日反有时,端心政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政,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内圈铭文即当时汉镜中最常见的“日光”铭,但外圈的铭文则非常罕见。与之类似的铭文,还见于一面私人收藏的单圈铭文镜,收录于《汉镜铭文图集》一书:
西汉晚期 “君行有日”铭单圈铭文镜
资料来源:王纲怀编著,《汉镜铭文图集》,中西书局,2016年,第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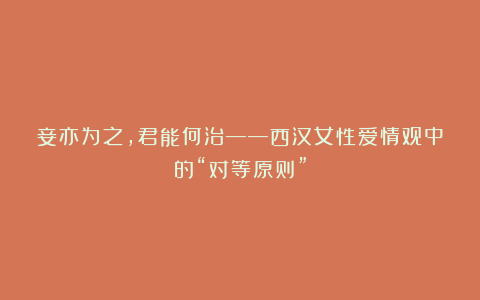
此镜的样式基本与榆次猫儿岭出土镜相同,唯前镜属重圈铭文镜,此镜属单圈铭文镜。镜铭曰:
君行有日毋反时,端政心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政,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二镜的铭文基本相同,仅部分语句的顺序前后颠倒,且前镜铭文作“君行有日反有时”,后镜铭文作“君行有日毋反时”。参考另一类“行有日兮反毋时”铭文汉镜,当以“毋反时”为标准铭文,“反有时”中的“有”当属讹字。
反,即“返”;政,即“正”。因此猫儿岭镜外圈铭文的标准读法应该是:
君行有日返毋时,端心正行如妾在;时心不端行不正,妾亦为之,君能何治?
大意:夫君你这一去就是不少时日,什么时候回家还遥遥无期,请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也要端正态度、注意操行,就像我跟在你身边一样;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我不在的时候乱搞事情,我也会作出和你一样的行为,到时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这段铭文所反映的爱情观念,在今天的人看来不过是很平常的“对等原则”(一方要求对方怎样对待自己,就要以同等的原则对待另一方),但对于秦汉时期女性对于丈夫要“忍辱含垢,常若畏惧”、“虽与夫治,勿敢疾当”的主流社会观念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反抗,可以说是西汉时期女性对“平等权利”的一种朴素追求。
与之文辞相类、上面提到的“行有日兮反毋时”镜铭,与这则镜铭相类,但反抗性就要弱了许多:
行有日兮返毋时,结中带兮长相思;妾负君兮万不疑,君负妾兮天知之!
大意:夫君你这一去就是不少时日,什么时候回家还遥遥无期,我只能束起内衣带苦苦思念你;你千万不要猜疑我会背叛你,至于你会不会背叛我,那就只有上天知道了!
这则镜铭可以视为上则镜铭的“姊妹篇”,疑其撰作者为同一人,俱表达了在家的妻子对远行丈夫的不信任,一则诉诸威胁,一则指天为誓,读之令人感慨。
二、
镜铭中的“妾亦为之,君能何治”,是目前所见存世文物中最早体现女性“追求平等”这一爱情观念的。不过,这种思想的源流,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端倪,那就是《诗经》中的《郑风·褰裳》。
《褰裳》是一首爱情诗,作于春秋早期,是一位郑国姑娘对心上人发出的“最后通牒”: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大意:你如果真的还在想我,就提起衣裳渡过溱水/洧水来找我;如果你不想我,难道没有别的好男人喜欢我吗?你这个小子真是太自恋了!
《涉溱》其绝。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