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在电影《731》剧组的工作照
早在2019年,我就进入了电影《731》剧组拍摄纪录片,但事实上,一开始我并不是纪录片导演。我首先是电影《731》的追随者,其次是学徒,最后才真正成为该影片的幕后纪录片导演。在此之前,我已参与拍摄了两部战争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与这次一样,也同样面临对历史的追问、对史料的理解。但这次的经历又与过往截然不同。
还没开拍,我就陷入了绝望
起初,我并不认为《731》这部电影会重塑一个年轻人的历史观和创作观。2020年,北京朝阳区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赵林山导演,那时他的胡子还是黑的。在我们简短交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吞了两杯冰咖啡,随后就跟美术指导研究纸房子模型去了。那片模型,我后来再熟悉不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下文简称“731部队”)本部六区的模型。
▲ 731部队本部旧址
等进组消息期间是集中前采的时间,我翻阅了市面上与731部队相关的代表性书籍《死亡工厂》《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恶魔的饱食》等。绝望、愤恨、哀默,纪录片还没开始拍,我就陷入了绝望。
这是一段受害范围广泛、影响深远、阴影仍笼罩在当代国人内心深处的悲惨历史。个中细节,越深入解读,越令人不寒而栗——施害者群体代表是日本战时极富盛名的军医——一群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们。他们残害了中、俄、朝等国三千多名平民(仅登记在册),未有一人存活。这些恶魔在战后以人体实验数据为交换条件逃脱审判,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医学院的校长、医院的院长、美国P4级实验室的顾问……
▲ 侵华日军使用的医疗器械
要怎样面对这次拍摄呢?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面前,我感到自己空前的渺小。我把目光投向赵林山导演,他对这段历史探寻了十几年,他会用什么样的故事去呈现?我参加了电影剧本围读会议,117场戏,4个小时,听完了电影故事,我成了这部电影的跟随者。我问导演:“您是怎么将这些受害者刻画得如此真实的?”他严肃地回答:“我常祈求他们来我梦里。即便在梦里相遇,我见到他们也不是可怕的样子。”
这些受害者对于731部队的恶魔们来说,是“马路大”(日语“圆木”的音译,引申意为“试验品”),是编号;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不能只留在统计名单和史料里,应该跟80年后的我们相见,他们是我们未归的亲人。
▲殉难者名单墙
我听到导演的抽泣
在赵导的指导下,我确立了纪录片的主题——当下与历史的对话。以电影《731》采风、取材、考证、拍摄工作为线索和切入点,揭露731部队从建立、实施暴行到败北毁证、战后审判的罪证。通过赵导十几年来求证过程的视角重新梳理731部队的反人类暴行,形成了当下与历史的镜像对话。
▲电影《731》操场放风区拍摄现场
这个主题符合纪录片普遍的创作原则,我也一度自信自己可以真实、理性、客观地完成这部纪录片,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预期发展。
2021年初,我们一行人跟随导演去了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赵导对于那里已然十分熟悉,但我是第一次去。当时,哈尔滨下着大雪,日落之前,我带着摄影师进入当时未开放的冻伤实验室遗址拍摄。进入前,我们还在讨论怎么构图、怎么摆机位,但刚踏进的那一瞬间,一股莫可名状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沉默着环顾冻伤实验室遗址,想象着80年前,受害者们在这里如何挣扎、哀嚎、绝望、任人宰割……我们忘记了机位构图运镜,凭着本能完成了拍摄。天什么时候黑的?不知道,摄影机的ISO(感光度)已经开到了12800,天黑到无法再继续拍摄了,得走了。院子里,雪积得更厚了,两只乌鸦“呼啦——呼啦——”地从雪地上飞起来。我们拖着长步,不忍再打扰长眠于此的人们。
▲电影《731》安达野外试验场深坑部分拍摄现场(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历史的遗骸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没有人可以假装看不到,也没有人可以保持绝对的理性。我意识到了自己从理性到感性的巨大改变,并为此苦恼。作为纪录片导演,应当保持绝对理性,但是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
往后的日子里,随着电影《731》的拍摄,我对主创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彼此间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爱这部电影,爱电影故事中的人,更爱身边这些为了这部电影全力以赴的创作人员们。
我目睹了这部电影3次准备开机却因不同的原因而未能成功;我记录了所有部门的工作,记录了无数个争吵与欢欣的场面;我目睹了工作人员从4名增加至1500名;我了解很多人,认得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脸;我担心自己的摄影师太少,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素材,所以自己拿着相机幽灵一般地游荡;我采访演员,动情之处哭得比他们还大声;我主动了解不同部门的困境,却又不能置身事外,终日在理性旁观与热切共情之间摇摆。基于此,我每天出工前都提醒自己:要沉默,要变成一个透明人——以此来勉强维护创作的客观理性。
▲电影《731》安达野外拍摄现场(青岛胶东机场附近)
这的确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创作经历,内心的煎熬,创作立场的摇摆,乃至人生观的重塑,我感觉自己被卡住了。
直到有一天,电影现场拍摄一场怀孕准妈妈被推进手术台进行剖腹产实验的戏份,需要拍摄孕肚特写。导演组为追求真实,请来一位孕妇躺在手术台上让我们拍摄特写。怀胎八月,这位准妈妈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妊娠纹,在摄影机镜头里表现得很好。
开机,日本演员的手抚在准妈妈的肚子上……监视器前,赵导异常沉默,没有给出任何意见,摄影指导问他行不行,他点头,让大家去吃饭。我在赵导身后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以为他对这个镜头不满意。现场的人都走光了,导演监视器棚安静了下来,赵林山导演僵直的背影懈下来,我听到微乎其微的抽泣……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刚才拍摄的回放,他看到了胎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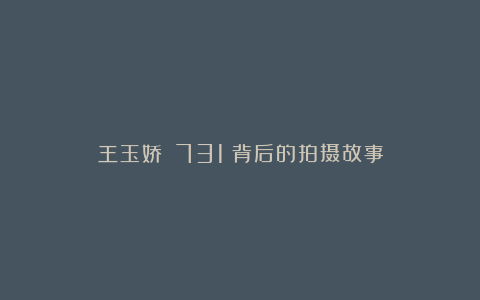
▲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内的活体解剖实验室
之后,我和自己和解了。
自那天后,我只拍能吸引我的。我跟摄影师说:“你们一定要在这部纪录片中投入巨大的爱,以客观、理性的职业操守去记录以电影为媒介、想唤醒国民记忆的这群人,记录他们如何克服一切困难去真实地还原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的。”我们不能为80 年前的受害者做什么了,但记忆就是我们最锋利的武器!
“传下去,直到世界的尽头”
电影《731》杀青后,纪录片拍摄暂时告一段落,我回济南老家过年。
济南有个地方叫“新华院”,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发动细菌战的据点,现在遗址被保护起来,周边居民来来往往上班下班从院门前经过,历史变成了我们而今的习惯。习惯,嵌在生活中,你想起来,不觉得被压垮,而是在心灵某处积蓄着力量。遥远的、宏大的历史,变成了切实可触的日常,这就是历史发出回声的模样。
“向前走,别回头,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别忘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这是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出口播放的离场广播,也是我在电影《731》纪录片拍摄的这段历程中所切实体会到的。“沉重的记忆不会让我们变得愤怒”——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说辞,我们恰恰需要去铭记。铭记是为了明白当下生活的来处,锚定自己的坐标,勇敢坚定地向前走。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我的纪录片还没有拍完,要记录到电影《731》上映之后,才算完整。我非常感激有这样珍贵的创作机会,用纪录片的形式留住电影《731》的记忆。如果说电影是导演构建的无限世界,那么纪录片就是世界坍缩凝结成的微型景观,能让你看清事物里的灰尘。纪录片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者观察世界的方式。
▲笔者在电影《731》剧组安达野外的拍摄现场(青岛胶东机场附近)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解构主义思潮,我们的生活不断地遭遇解构。传统的观念被解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解构,宏大的意义被解构。当一切都被解构,我们的生活只能指向无意义。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解构,而是建构,需要传承我们民族那些优秀的价值观,慈悲的精神,仁者的关怀。那些正义,真理,仁爱的精神,被一代代传承,将我们的精神家园建得更加牢固。受限于阅历和经验,我和我的创作是有局限性的。今后我会继续创作,努力丰盈,争取创作更多的承载民族精神的作品,希望被更多人看到,记住。
正如赵林山导演所说的“传下去,直到世界的尽头”。
爷爷在世时,我在他家翻出一本快要破碎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爷爷说,他尝试着去了解日本。他说,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曾被日军驻济南警备队抓去。“有去无回了”,同村人提到曾祖父时都摇头这样说。后来,曾祖父重新出现在村口,形销骨立,对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他奔波、生产、得癌、自愈、故去。
希望天上的他们也能看到这部电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