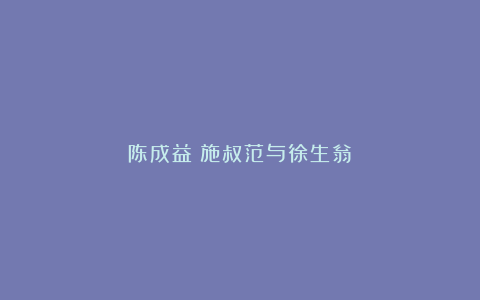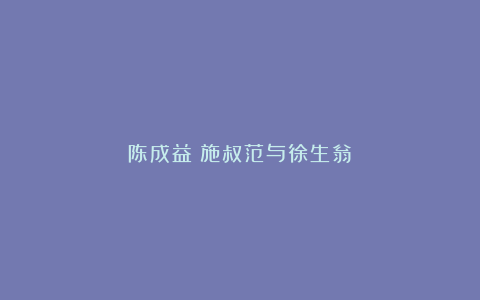|
绝忆城中李,坚如涧上松。雪深断爨火,腕病惊蛇龙。掩袖不东视,洗襟有北风。诗灯阁非远,僵卧倔强翁。
这首《忆生翁》,是施叔范于一九四五年春间所作。说“城中李”,是因为徐生翁一生足迹不出绍兴,住东郭孟家桥。他早年被寄养外家,嗣姓李,名徐,号生翁,中年以“李生翁”署书,晚年复姓徐,署“徐生翁”。而施叔范为姚北乡下坎墩人,同属绍兴。
施叔范把徐生翁比作“涧上松”,以明末清初遗民画家徐枋相譬,更因徐生翁早年有隶书题《明徐涧上先生岁寒松柏图》,并跋曰“清寒孤洁,肖其为人”,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为人写照。徐生翁作为鬻字为生的书家,在抗战时期不卖字给日寇汉奸,处境艰难,时“断爨火”,但他始终以“腕病”为托词,不为所动。施叔范所言“倔强翁”,正是徐生翁人格与艺术的写照。
难怪唐大郎说:“叔范的旧体诗,在我的朋友中,也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近世文人中,他是写得最好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了许多忧国伤时的好诗。”但施叔范是谁?冯其庸曾因几首年轻时读到的诗,记挂“施叔范”这个名字六十年,最终还是没有打听到。时至今日,恐怕知道的人更少了。与徐生翁因其书画强烈的个人风格,不断引起争论,被人模仿,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读郑重《唐云传》,在前半部,“施叔范”这个名字,隔几页就会出现。他是唐云朋友圈的重要一员,若瓢、邓散木、白蕉、唐大郎、桑弧等,他们是肝胆相照的诗文酒友。唐云来上海前,船过余姚,上岸去看望施叔范,脚下一滑跌到河里,朋友没看成。后来施叔范也来到了上海,在旅行社任秘书兼编辑,写了不少律诗散文。施叔范那时候收入微薄,家累也重,一般都是唐云替他掏了份子钱,更把黄宗羲仲弟“鹧鸪先生砚”送给了他。但彼时施叔范最想做的事,却是“印一部《震川文粹》,修一座震川新墓”,真诗人的浪漫想法。唐大郎“则是每首必读,他称施叔范为’施诗师’”。所以,郑重说他“诗文都朴实丰赡,风神秀整,他的诗尤为同辈人所推崇”,并非虚语。
一九三七年施叔范回到余姚,主《浙东日报》政笔。曹聚仁说:“你的标题是律诗,我的标题是散文。”所拟标题对仗精当,尤为人称道,其实这来自于施叔范的家学,去上海前,施叔范曾任国学专修馆教师,后来成为名医的裘沛然是他当时的学生。他身上还有一股侠气,曾营救革命者马承烈,并策动乡勇,成立“姚北抗日自卫大队”,狙击维持会的汉奸,四名为首分子遭击毙。他被悬赏万元购其首级,只得避居四明山,这里是黄宗羲当年结寨抗清的地方。他此时留下了“谁能杀我千金赏,杀贼我先试剑新”之句,比之陆游也不为过。在两浙山水间,他过起了流亡生涯,母亲去世也归家不得,写下“流亡诗草”两百多首。
而在施叔范流亡的同时,年近七旬的书法家徐生翁也在苦苦支撑,靠糊火柴盒、种植园菜度日。他的儿子翁旦被敌寇掳去,被枪杀于龙山,觅尸不得,年仅二十岁,翁旦很有才华,书法诗文俱佳。所以,抗战胜利后徐生翁被邀前往禹庙《唐往生碑》刻字,他写下了“丁丑浴佛日生翁与四子同观”,“丁丑”是在一九三七年,日寇未至,而刻字要在十年之后。巨大的悲痛倾注笔间,这是徐生翁所有字迹中,写得最为端正的一篇,字字泣血。我们至今依然可以在《唐往生碑》上,看到徐生翁的这篇题刻,不能单纯以书法视之。
抗战胜利后,施叔范回到了上海,回到旅行社,回到他的朋友中间,重新过上他的文字生涯。他关心时事,也参与政治,但他的笔下完全是另一番境界了。他在《七日谈》上有一个专栏,名为“白衣集”,别的不论,仅《记李生翁》一篇,鄙意以为是所见记生翁的文字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句句写实,他们在抗战年月里,历经丧乱,所以感同身受,贴近生翁,对其艺术更有知音之赏。文章放在桐城一路的散文中,也毫不为弱。《记李生翁》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因全文不长,也不易看到,索性照录:
李叟生翁,清贞奇苦,战前借砚墨收益,差赡饔飨。迨陷后,端居绍城,不避亦不屈。寇索其书,则辞以腕病;伪新贵求之,更谢以心疾。于是人如不食字之仙蠹,长与白米无缘矣。地不布金,天无雨粟,故其日食二顿,无非是苜蓿、薤菜、南瓜、蕃薯之类。自春徂冬,四阅星霜,骨渐渐高,而墨亦渐渐稀,船友闻者哀之,馈以金换其书画,要仍不过支持三旬之麦粉腐耳。浙西贺培心氏,尝谋迎至天目,安其笔砚,又以家累甚重,而卒不果。
春间余去平水,叩金功亮,审老而弥坚,穷而愈笃,为之慨慕整宵,晤有期矣。会迫于东归,仅留一诗以将意。顷续前缘,想石帆山下之约,乃似梦中之又梦也。
翁住于东郭门,颓栋栉比,霜草上腰,真可谓之陋巷。叩门,老妇来窥,彼不识我,我固知为翁之夫人也。投刺告之,旋即握见。翁高我矮,翁喘我咳;翁发如银,我髯有霜。翁说:“此会难得!”我道:“果然意外!”言时彼此似笑又非笑,惟闻邻儿讶呼曰:“年老人何以亦会哭耶!”五年之别,中杂如许丧乱,从何话起?从何答问?
翁但谓:“吾耳益重听,今以复姓为徐矣,留不久矣,死无憾矣。平水之诗,能大书一过,则拜嘉多矣!”余皆唯唯应之,蘸墨展笺。不管鲁班坐上头焉:七年吾不死,再到石帆山。春雨茶仍绿,废堂燕怯还。凄然长夜话,老矣故人颜。多累田园在,忍能笔共删。 绝念城中李,坚如涧上松。时危甘掩抑,腕病禁蛇龙。傲骨炊三釜,单衣过一冬。还怜诗意苦,为我一书封。翁亦为余署“流亡诗草书”签一,故及之。
时鸦啼有顷,锅中麦香已久,其夫人出告余曰:“翁年来作书益苦,谓笔笔要脱尽碑帖。每成一联,撕而复写,写而复撕,累日不休,如此悲腕益劳,而入益寡,宁不可姓,先生曷稍劝之!且李虽系外家姓,然人诵之已熟,仍旧何妨?乃必归宗,致又损失一二。”我视翁,颇似有所察,喟然微搔其鬓曰:“往年不死,岂谓余生尚难逃饥冻劫耶?吾书吾自乐耳,讵必人知?吾姓固是徐,无可久假?”
出其《复姓说》与近作手卷,如玩原始文字。忆曩与粪翁客吴门,聆萧父蜕庵指定光寺壁上之条幅谓:“生翁之字,真不食人间烟火,吾辈追踪抗手,似须来生。”恨是日所见,未能与萧叟、老铁共之也。
当年小报,限于版面,文不加点,一段到底,信息量着实密集。首先是徐生翁作为一个靠鬻字为生的书法家,在抗战前后的日常处境。他育有八子:朔、己、振、旦、雁、旦、迪、宇,三女:书、雯、素。他的家庭负担沉重,靠笔墨勉强营生,异常艰辛。到了最艰难的时刻,简直吃不饱饭。但也绝不卖字给日寇和新贵,“我不要这造孽钱”,掷地有声。
他住东郭孟家桥,历史上虽为毛奇龄女弟子徐昭华“青未了阁”旧址,但当时已是车夫船友的聚居地。这些人富有同情心,向他买些字画,其实他们哪需要什么书画,无非是看不下去这样一个年近七十的老者忍冻挨饿。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他选择“不避亦不屈”,绍兴专员贺扬灵非常赏识他,为回报知遇之恩,徐生翁为之题写“言论集”。但他从来能避就避,贺当时想要迎他去天目山暂避,他没有答应。
二是施叔范与徐生翁当时相见的情形。在陋巷颓栋之中,两人再度见面,面貌都已不是当年,一个发如银,一个髯如霜,施叔范是胡子美男,在上海一直被友人称为“施髯”,但他也老了。他们似笑又非笑,似哭又非哭,真如八大“哭之笑之”,劫后余生,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出现一个儿童的画外音,“难道老年人也会哭啊?”调皮又贴切。
过后徐生翁又向施叔范说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的重听越来越严重,恐怕活不久了。徐生翁让施叔范录下诗稿,这两首诗是前一年施叔范到平水时所写,既回忆前缘,也写耳闻的徐生翁处境,感时伤世,感人至深,请他当场写出可见徐生翁亦是首肯的。那首《忆生翁》也是由此化出。徐生翁为他的“流亡诗草”题签,可惜后来随着施叔范所有文稿的付之一炬,没能流传下来。
徐生翁有一件大事必须办好,那就是复姓为徐,这是他郑重提出的。他平生唯一一次离开绍兴,就是应族人之邀,回原籍淳安,并作诗三首。现在一般可用署名的不同,来区分徐生翁书法创作时间的早晚,早期“李徐”,中年“李生翁”,晚年“徐生翁”。但也有例外,徐生翁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禹庙窆石题刻“会稽山万古,此石万古”,署为“徐生翁”,位于宋元人之间的这个徐生翁题刻,他知道是要传之后世的,所以直接题为“徐生翁”了。从这个例外来看,他的内心一直有复姓为徐的冲动。历经丧乱,徐生翁正式决定复姓,并写有《复姓说》一文。可惜施叔范当日“如玩原始文字”的这篇手迹,我们目前也没能看到,或已不存。
当然对于职业书家而言,改名意味着受损,所以徐生翁夫人不以为然,并且也很体谅徐生翁的辛苦创作,施叔范记录的夫人这句话,“翁年来作书益苦,谓笔笔要脱尽碑帖。每成一联,撕而复写,写而复撕,累日不休”,后来研究者多有引用。这话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徐生翁晚年的创作状态,他跟一般书家有很大不同,创作对他来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他的作品并非一挥而就,而是苦心经营的结果。他的创作成功率非常低,只有他自己满意,才能让作品出门。他把自己关在门里,几乎谁都没有看到过他写字。这与我们寻常对于书法家的印象,截然不同,徐生翁写字真是苦心孤诣的。
徐生翁窆石题刻
徐生翁对于夫人的疑虑,回答也是斩钉截铁,“吾书吾自乐耳,讵必人知?”对书法这么艰难的创作过程,他却乐在其中,一个“倔强翁”的形象跃然纸上。据他的孙子回忆,徐生翁几乎足不出户,坐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写字,从来不干家务,有时候仅到竹园中走几步。他享受他的书斋生活,虽然穷困,但一直以书写为日常生活。晚年他焚毁了他不少作品,但从四大本集联来看,他的阅读量极大,创作量也极大,幸存的仅是很少一部分。
数年前我曾寓目很小的一页信札,仅留下一张不甚清楚的照片,从没发表过,徐生翁在信中说:“嘱书墓碑两块,楹联一副,画一帧,便面已就,邮奉,希察收。碑字刻好,近地有拓碑者,望各拓一分寄示。如觅不到拓手,摄影亦好。”字写得一丝不苟,是他晚年的日常手迹,正如陆维钊评论其字“简、质、凝、稚”。这个信札内容,可视为徐生翁晚年创作鬻书生涯的一个侧面。写墓碑两块,也说明其字在当时的浙东乡间,是被普通接受的。绝非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他的字被目为“孩儿体”,没有多少受众,实则是一种误解。
嵊县人胡兰成,抗战前也曾访徐生翁,他论生翁书法也极精当:“先生盖老氏之所谓婴儿,得天独厚,书法精湛,饶归真反朴之趣。其造诣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曰’生’曰’拙’……然世俗于先生书,徒见其不受准绳,而不能见其雍容安详之致,固未足与言先生之书也。”确如他所言,我们可从徐生翁这封寥寥数语的信中,见出生拙,更能见雍容安详之致,这种气象弥漫在生翁晚年的日常书写当中。胡兰成又说:“余最钦佩先生之处,为其对于艺术之认真,无一毫苟且心理,意有所未安,不出以示人。盖其作书作画作印,非仅为人,亦以为己也。”这个说法可与施叔范的记录相互印证,他的书法是为自己写的。
回头再看施叔范的文章,他也提到邓散木老师萧蜕庵对徐生翁的评价,他说徐生翁的字,不食人间烟火,要赶上就只能靠来生了。邓散木作为施叔范的朋友,也被深深拜服。他跟着施叔范专程来绍兴拜访徐生翁,还一起回了坎墩家里,用施叔范的笺纸写了四首诗送给叔范。回上海后,邓散木在《新民报》上对徐生翁作了介绍。在他笔下出现的近现代书家,只有三个人,他的老师、梅调鼎,还有就是徐生翁。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声誉日隆的布衣书家徐生翁,被吸收进了浙江省文史馆,开始有了固定津贴。作为职业书家,不再有他的市场,他的创作也跟之前数十年呈现不同的样貌。他的书写进一步趋于楷化,此时他更多抄录诗文,书风也不再那么激烈。经常应公家之请,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王右军将军祠”“徐锡麟纪念馆”“宋天章寺遗址”等,可谓适得其所,整个绍兴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有人说他所题纪念碑,“似乎从字上面就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悲壮和伤痛”。徐生翁写字,有所寄托,极富情感。这时,黄宾虹、宋云彬、柯灵都有向他求字的记录,黄宾虹甚至想邀他到美院任教,但徐生翁依然没有答应。
而此时的施叔范,却遭厄运,他被投入狱中一年,之后被冠以“历史反革命”遣返原籍,被管制达二十多年。《唐云传》的后半本,就再也没有他的名字,友人间甚至传闻他在乡下已经作古。施叔范留有一份《自述》,记录到一九六八年,从文句用语来看,可能是一份交代材料。其中有一句透露:“从六二年写文史稿到本年(一九六四)四月,被政协转省采取的约卅八篇。”实际写作应不止此数。也就是说,施叔范并没有停止写作。笔者手头有一份题作“施叔范遗文十篇”抄本复印件,收稿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并钤有“施叔范”印鉴。打头一篇就是《有骨气的书法家李生翁》,他还坚持用“李生翁”这个名字,可见是不通音讯的。如果说《记李生翁》一文为访问记,那么这篇就是回忆录,对徐生翁有着更为详细的记录。他甚至还保持着他一贯的文风,几乎看不出时风对他的影响。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篇艺术文献,长久以来湮没无闻了。对徐生翁的生平和艺术进行研究,施叔范是一个先行者。
文章先叙徐生翁早年的学书经历:“顾其时挥濡落墨,尚不脱右军风姿。观赏者爱其圆劲秀拔,渠独引以为甚恨,以十之六七犹依样葫芦也。”这类作品,存世稀少,徐生翁书法的出类拔萃,在于不与人同。施叔范接着说:“故在后期,致力于流沙木简、六朝造像,意运笔创,蜕变前体,人无以名之,称为’孩儿体’,实乃彼所戛戛手造之新形象。于时并改署为生翁,有生辣、生动、新生不息之含义……且以曩昔流传人间者,意殊不慊,循户搜换新迹,了不惮烦。”这是对“生翁”名字的一种新解,并未在别处见到。毁旧换新这个举动,看来也是他的习惯。这可与徐生翁弟子沈定庵的经历相印证。他拿着抗战时去世的父亲留给他的徐生翁旧作,去看望徐生翁时被要求换掉。这也是徐生翁对旧作的态度。他的书法一直在探索与转变,其创作抱着“万无一毫苟且心理”的态度,认真而苛刻,以致于其早年作品流传不多。
该文记萧蜕庵、邓散木师徒对徐生翁书法的评价,也远比《记徐生翁》详细,他说:“一九三五年春……一日,同游戒幢寺西园后,过定光寺。步入方丈,见壁上张有李生翁所写之条幅,萧凝注有顷,喟然语粪翁曰:’此公落墨,不着一丝烟火气,自开生面,非可几及,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钦慕之忱,殆过似归震川之于徐文长。临去复回顾再三,若恋恋不置。迨四六年夏,我导粪翁谒见此老时,彼此反复互证,几忘日暮,归途邓告余曰:吾于萧师之外,又得一尊宿矣。”这是两代书家对徐生翁书法的拜服,高手过招,自叹不如。所以,在《记李生翁》一文中,施叔范遗憾的是,萧、邓两人没能一起观看徐生翁的近作。邓散木来过之后,这种遗憾得到了弥补。
后面记录的是当时绍兴文人与贺扬灵的交往,以及徐生翁不同他人的态度。关于抗战中徐生翁的生活,也要详细得多,兹不再录。同时,他那首《忆生翁》又有另一个版本,在字句上有所不同,可见这些诗作,都记在施叔范的心里,时时都在修改。
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有徐生翁对时人书法的评价,因为绝无仅有。文章写道:
余昧小学,又不解六法,然喜举时人墨迹以相叩,翁未尝不娓娓倾告。尝问叶恭绰之笔意如何?答谓:“放而近野。”问余绍宋,则曰:“劲敛中也要有萧疏气,否则便是局促。”问马一浮,讷讷有间,继莞尔曰:“渠自有妙趣,但年来署名’蠲叟’之’叟’字末笔,故作不断波磔,亦是魔道。”惟于沈尹默、白蕉之胡桃行书,齐白石之篆文,誉为难能,终且曰:“室内臧否,不足为外人道也。”
涉及马一浮的部分,被横线划去,个别词被涂黑,但依稀尚可仿佛。鉴于施叔范的写稿时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马一浮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首长对其相继拜访。此时的施叔范在农村老家被管制,让其写稿几乎有一种废物利用的意思。他在《自述》中曾说:“因不服公社书记扣发我稿,冲突至于拍桌辱骂,无法无天。十二月间,县政协副主席叶令民、县文化馆长黄宗正来过我家,为写稿向公社说话,我更翘起尾巴来。”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话虽如此,在其写作文本中,可以做到毫无时代痕迹。就这一点来说,施叔范也是倔强的,他的确可算是徐生翁的知交。马一浮这部分字句上的画线,可能正是相互较劲的结果。
正如徐生翁所言,在几十年后,沈尹默、白蕉式的“二王”书风大行其道,齐白石也一直没有过时。他的判断确实超前,要知道这是四十年代的谈话。虽说不足为外人道,在六十年代初,还是被施叔范毫无保留地记了下来,其文献价值独一无二。因为施叔范是同辈友人,徐生翁跟他的谈话方式,跟学生相比,当然不同,他是言无不尽的。徐生翁甚至还告诉施叔范写字的具体操作方法,这一点连学生都没有记录,尤可宝贵:
亦曾告我以运笔之道,翁谓:“每笔起落,要作∽形势,既熟生巧,自然雄浑蓄力。”“写大字,倾注全身之力,运于右臂,自腕而凝聚拇、食、中三指,乃能墨透纸背。”“唐以前,每字皆密,如北魏之曰,其中一画必然到边,六朝以后便不然。然疏密贵在得宜,不拘拘时代。”“作草书必不能连,手滑,那能掣得蛟龙来?”
这种具体的书写方式,除《我学书画》寥寥数百字外,徐生翁再无只字片语。施叔范也是行家,他很清楚哪部分谈话有其价值。文无定法,书法也一样,本没有秘密可言。那些口耳相传的部分,才是最要紧的,徐生翁可以说是毫无保留了。
施叔范说徐生翁“不常作诗,仅得其手稿三章”,这三章应为生翁佚诗,因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诗。其学生本想成集,但他不置可否。施叔范抄录了下来,但这生翁手稿,怕也化作灰烬了。文章结尾交代,他们的交往始于一九三八年,因缘是施叔范的诗,被此老所见,遂定交。最后附注:“计生翁现年不足九十,想当健在。”施叔范写此稿时,也是生翁的最后一年,他于一九六四年初,以九十岁高龄去世,走之前焚毁了很多作品手稿。他们没有再见面,鉴于施叔范自己的身份,他是不好再登门拜访了。如相见,是该哭,还是该笑。邻家那位儿童,想也已成年。
徐生翁似古松,据说他生前经常去府山,默默观察山上的古松。他真像古松一样,定在了绍兴东郭孟家桥,一意孤行,写了一辈子的字。我们去他老宅,陋巷老屋,墙上挂着他的照片,至今还是老样子。
施叔范如浮萍,“人生才命相妨”。在失去联络二十多年之后,唐大郎再度联系上他,信中他不大谈自身的遭际,倒是更多谈论诗文。没过多久,施叔范悄然在姚北乡下的女儿家去世了,他的诗“全都烂在他的肚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