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园林的幽深与海派文化的交融处,孙永将半生书画修养凝练于方寸玉石之上。
从徐州画案前的墨香少年,到“相王弄”里名声鹊起的玉雕师,再到“香海棠”中静守初心的非遗大师,他用近三十载光阴,打通了文人画与玉雕的经脉,让冰冷的石头生长出诗词的骨骼与山水的魂魄。
墨痕刀影:从宣纸到玉石
七岁的孙永,世界是舅舅画案上的一滴墨。
在江苏徐州的老屋里,画家舅舅吴俊友是他艺术的“原点”。舅舅作画时从不打稿,提笔直取,水墨在宣纸上皴擦点染,顷刻间山河毕现。
“那种专注,那种‘一口气’完成的气魄,像烙印一样打在我心里。”童年的孙永扒在案边,看懂了技艺,更懵懂地感知到一种超越技艺的“气韵”。一本《芥子园画谱》,无数个观墨的午后,书画的种子深埋于心。
命运的转折常在不经意间叩门。九十年代,受爱玉父亲的影响,孙永接触到不少工艺粗糙的玉雕。“总觉得可惜,这么好的一块玉,形神俱失。”源于书画审美的那份“不甘”,驱使着他。
他寻访到曾参与修复“金缕玉衣”的徐州玉雕厂老师傅李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持握吊机,如何理解玉石的“肉”与“骨”。最初,这只是“玩票”,是爱好者的修修补补。
直到1998年,他南下扬州,拜入山子雕名家门下。
当亲眼目睹老师傅们在巨料上构思、开凿,营造出亭台楼阁、近景远岫的深邃空间时,他心中那个关于“山水”的梦,终于找到了更坚硬的载体——玉。“宣纸上的山水是氤氲的,玉上的山水,则是可以触摸的永恒。”自此,一位潜在的画家,正式踏上了一条更为艰辛也更为坚实的琢玉之路。
相王弄的黄金时代
2004年,孙永选择在苏州“相王弄”安顿下来。这条狭窄的老巷,彼时正汇聚着中国玉雕最早期的活力与野心。那是行业狂飙突进的“黄金七年”,市场火热到“作品做好往那一放,就被人买走”。他的工作室一度扩张,日夜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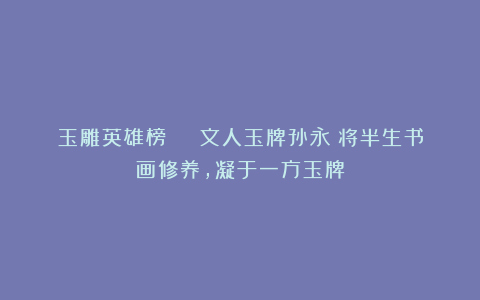
然而,在机器轰鸣与交易喧嚷中,孙永始终为自己保留着一方寂静的天地——他的画案。无论多忙,他从未停止对古代画论、诗词歌赋的研读,从未放下手中的毛笔。
他的工作室里,堆满古籍画册;他的“香海棠”会所中,悬挂着范曾、启功等大家的墨宝。“书画是‘充电’,没有这股‘文气’撑着,玉雕就只是手艺,成不了艺术。”他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充斥的是“产品”与“工艺品”,而他渴望创造的是“艺术品”。
文人玉牌:刻在石头上的立体诗
孙永的“文艺牌”,是一场对传统玉牌的彻底革新。他将玉牌正面视作一幅微缩的立体文人画,运用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与虚实相生,在方寸之间营造出“咫尺天涯”的深远意境。而背面,则成为金石书法与铭文注解的舞台。
代表作《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宛如一场朝圣。他以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巨幅画作为蓝本,将毛主席诗词中的北国风光,转化为玉牌上的巍峨雪山、苍茫天地。正面雕琢,层峦的深浅、云雾的厚薄,全靠刀锋的微妙起伏来表现;背面阴刻《沁园春·雪》全文,数百蝇头小字,字字挺立,气脉贯通。
这件作品耗时数月,仅刻字便凝聚了十数个日夜的心血。后来,它登上了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殿堂“双年展”并获奖,而孙永却坦言创作时“如履薄冰”:“玉雕是减法,一刀下去,永无回头路。”
另一面《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玉牌,则尽显文人雅趣。正面云海翻腾,仙鹤翩跹,意境空灵;背面以秀挺行书刻下对联,并附以考据证书,阐明典故出处与创作立意。他说:“我要不断为这块玉赋予文化层次,让收藏者不仅看到美,更读懂美背后的山河与诗心。”
简约佛像与“一口气”的哲学
在人物题材上,孙永展现了同样惊人的突破力。他对传统佛造像进行现代性解构,剥离所有繁复装饰与写实细节,仅以最简洁、流畅的线条与弧面,勾勒出佛像静谧慈悲的内核。这些极具辨识度的“孙氏佛像”,静谧空灵,充满极简主义美学与当代禅意,甚至获得了国家版权保护。
“我希望回归本源。佛的慈悲与宁静,不在于璎珞的华丽,而在于形态的气韵与神光的收敛。”这种“以少胜多”的创造,正是他“守正亦出新”理念的极致体现:守住传统的精神内核,以全新的视觉语言进行表达。
他常言:“作品之魂,在于‘一口气’。”这“一口气”,既是舅舅当年作画时笔走龙蛇的连贯气韵,也是他自己从构图、雕刻到打磨,贯穿始终的精神凝聚力。“要让一块冰冷的石头‘活’起来,靠的就是创作者灌注其中的这口‘气’。”而这口“气”的养成,他归结为“玉外功夫”——那需要经年累月的阅读、思考、审美积累与文化沉淀。
香海棠里话收藏
如今,孙永更多时间待在名为“香海棠”的私人空间。院内有灵璧石清供,墙上是名家书画,这里是他创作的延伸,也是精神的栖息地。面对当前市场,他显得冷静而深刻。
“玉雕已过剩,未来属于有思想、有文化的作品。”他直言不讳,“’需要’不是‘收藏’。真正的收藏,需要知识、文化、热爱和眼光。
收藏的终极目的,是审美与价值的双重抵达。”他鼓励年轻藏家提升自身修养,看懂工艺背后的文化密码。
从徐州孩童眼中墨染的山河,到苏州大师刀下玉生的宇宙,孙永完成了一场跨越媒介的艺术长征。他以刀为笔,以玉为纸,将中国文人的风骨与诗意,铭刻进不朽的时光。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手艺的尽头是文化,作品的寿命取决于它承载的思想的深度。当一块玉牌能让人吟出一首诗,望见一片山水,感受到一种风骨时,它便超越了物件本身,成为了一种不朽的文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