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的脑血管周围通道网络用于清除多余液体和代谢废物,在包括脑淀粉样血管病(CAA)在内的几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CAA是老年人出血性卒中的主要原因,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常见的血管合并症,也与抗淀粉样蛋白免疫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调控可溶性淀粉样蛋白β(CAA的关键致病因素)从大脑到引流淋巴系统和体循环的脑血管周围清除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这一知识空白对于理解CAA的病理生理学并加速靶向治疗药物的开发至关重要。本综述的作者最近整合了他们在脑血管周围生理学领域的多元化专业知识,在Leducq基金会脑清除跨大西洋卓越网络的框架内专门解决这一问题。本综述讨论了该联盟的总体目标,并探讨了支持或反驳脑血管周围清除受损在CAA病理生理学中作用的证据,重点是将从啮齿动物获得的观察结果转化到人类。我们还讨论了脑血管周围通道的解剖特征以及液体和溶质运输的生物物理特性。本文发表在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杂志。
概要和范围
维持脑稳态和功能不仅需要向大脑持续供应重要营养物质和氧气,还需要持续清除代谢废物。直到最近的发现证明血管周围的脑血管周围间隙对于促进大脑引流至关重要之前,我们对脑清除的了解一直非常有限。可溶性淀粉样蛋白β(Aβ)的脑血管周围清除受损与脑淀粉样血管病(CAA)的病理生理学有关,在CAA中,Aβ积聚在毛细血管和小动脉壁中,偶尔也积聚在小静脉中。然而,脑血管周围清除和血管Aβ沉积之间联系的确切机制仍然知之甚少。这一知识空白至关重要,因为CAA是出血性卒中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认知下降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是阿尔茨海默病(AD)最常见的血管合并症。最近,CAA被认为是一种可能解释接受抗淀粉样蛋白免疫治疗的AD患者出现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ARIA)形式不良事件发生的病症。随着人口老龄化,CAA正在增加,而有效的疾病修饰干预措施尚不存在。揭示脑血管周围清除的机制将对理解CAA以及其他常见痴呆疾病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了解如何通过改善睡眠或其他关键生理驱动因素来增强脑清除,不仅对CAA患者至关重要,对整个老龄人口也至关重要。
两个关键的总体性和基础性知识空白阻碍了我们对CAA中脑血管周围清除受损作用的理解,从而也阻碍了旨在改善Aβ清除的治疗策略的可能开发:
(1)关于脑清除的解剖路径、方向性和机制驱动力,以及它们在CAA早期和晚期如何改变,该领域仍存在重大争议。这些差异部分源于对啮齿动物和人脑中涉及清除的微观解剖结构缺乏详细表征、异质性的实验影像学方法、使用不同的啮齿动物模型和麻醉方案、与局灶性示踪剂注射相关的伪影以及死后固定。这导致了不同实验室之间的研究结果和数据解释的差异,也减缓了转化影响。
(2)尚不清楚啮齿动物模型中的观察结果是否可以轻易转化到人脑。理解人类脑清除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用于脑血管周围清除的非侵入性影像技术。能够测量间质液(ISF)和脑脊液(CSF)流动性以及间隙之间水交换作为脑清除替代指标的新型MRI序列的开发和验证,可能会加速转化工作,并允许研究健康个体和CAA患者的脑血管周围清除。
本综述论文的目标是批判性地评估支持或反驳脑血管周围清除受损在CAA病理生理学中作用的证据。此外,我们旨在为回答现有基本未知问题所需的未来研究提供展望。作者是Leducq基金会脑清除跨大西洋卓越网络的成员。将该联盟聚集在一起的关键动机是,基本的脑清除知识空白和争议无法由任何个人或实验室单独弥合。相反,它需要临床前、临床和计算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辩论,他们使用互补技术从不同角度研究脑清除。其成员具有互补的技术专长和观点,其目标是解决相互冲突的实验发现,并将啮齿动物的观察结果转化到人脑,从而最大化转化影响。因此,总体联盟的目标是: (1)建立对健康和CAA中脑血管周围清除的生理和病理信息化、综合多尺度理解;
(2)将啮齿动物的实验发现转化到人脑,;
(3)确定相关驱动力以在未来临床试验中测试,以增强可溶性废物清除以促进脑健康。
脑淀粉样血管病(CAA)简介
人口统计学
CAA是一种常见的与年龄相关的病理,是自发性脑叶脑出血(ICH)的主要原因,也是与年龄相关的认知下降和残疾的重要促成因素。对代表普通人群的未经选择的老年人进行的尸检研究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报告,轻度至重度CAA的患病率为41.5%(95%置信区间[CI] 33.1-50.2%),中度至重度CAA的患病率为23.0%(95% CI 17.3-29.1%)。这些数字大大超过了脑叶ICH(脑出血)的发生率,而脑叶ICH是CAA最显著的临床表现,表明CAA病理在临床上通常未被检测到。然而,即使在没有ICH等急性表现的情况下,中度至重度CAA也与生前认知功能受损独立相关,使其成为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常见血管促成因素之一。
在存在AD病理(即存在实质性Aβ斑块和细胞内tau蛋白缠结)的情况下,CAA的患病率增加,这可能反映了Aβ积累在这两种疾病中的核心作用。对AD患者进行的尸检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轻度至重度CAA占79.2%(95% CI 72.5-85.3%),中度至重度CAA占47.5%(95% CI 38.8-56.2%)。除年龄外,CAA和AD共有的最明确特征的风险因素是载脂蛋白E(APOE)ε4等位基因的存在和数量,这与更严重的AD和CAA严重程度相关。与Aβ沉积相关的其他因素也促进CAA和AD病理,但通常优先促进其中一种。例如,增加较长Aβ42与较短Aβ40种类比率的淀粉样前体蛋白(APP)基因突变(如London Val717Ile突变)主要引起AD病理,而Aβ编码序列内的几个APP错义突变(如Dutch Glu693Gln突变)强烈倾向于CAA。值得注意的是,严重的CAA是Aβ编码序列内APP突变的常见特征,但临床表现(ICH(脑出血)、认知障碍或两者兼有)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在携带相同突变的个体之间也不同。AD伴CAA的其他遗传原因包括PSEN1和PSEN2突变以及APP的拷贝数变异(包括21三体)。还有另一类CAA风险因素,它们增强了初始血管Aβ沉积下游CAA发病机制的步骤。其中最突出的是APOE ε2等位基因,它对AD病理具有部分保护作用,但会增加CAA相关血管壁破裂和ICH的风险。
神经病理学
CAA的神经病理学特征是Aβ主要存在于皮质和软脑膜血管壁中,而白质中的血管未受累。Aβ首先沉积在中膜和外膜中,从而逐渐取代血管平滑肌细胞。值得注意的是,CAA中的内皮细胞似乎相对完整,表明Aβ来源于脑实质而非体循环,尽管最近的一项RNAseq研究确实发现在存在CAA的情况下人类内皮细胞转录组发生了变化。血管Aβ沉积通常首先在软脑膜动脉水平观察到,随后是下层皮质的穿支小动脉。此外,CAA进展往往遵循后向前的模式,即大脑枕叶区域在疾病过程中较早受到影响。有人认为Aβ沉积的神经病理学模式可能反映两种不同的亚型,其中”CAA I型”涉及皮质毛细血管、皮质小动脉、软脑膜动脉和小静脉的Aβ沉积,而”CAA II型”中Aβ沉积仅限于皮质小动脉和软脑膜动脉,不累及皮质毛细血管(图1)。在有毛细血管CAA(即CAA I型)的尸检病例中,APOE ε4等位基因的频率高于主要有软脑膜和小动脉CAA(即CAA II型)的病例。
图1 来自两例临床诊断为CAA的尸检病例的Aβ免疫组织化学例子,显示广泛的CAA伴毛细血管受累(A,CAA I型)和主要小动脉受累(B,CAA II型)
晚期CAA与大量皮质微梗死的发生相关,最终可能导致血管壁破裂和出血。神经病理学研究发现,在严重CAA病例中,血管壁分裂形式的小动脉重塑(Vonsattel 3级)或纤维素样坏死性变化(Vonsattel 4级)与出血数量之间存在关联。此外,离体MRI引导的个别破裂血管的靶向组织病理学调查表明,破裂部位存在小动脉重塑以及Aβ缺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管重塑可能先于出血,这一过程可能部分由免疫介导,在CAA相关炎症或抗淀粉样蛋白免疫治疗的背景下以ARIA形式加速。血管周围炎症和随后的血管壁破裂是否可能直接由血管Aβ沉积或CAA相关的微妙血脑屏障(BBB)渗漏和血浆蛋白浸润到血管周围组织引发,仍有待确定。此外,远离血管Aβ积累部位的血管壁破裂的潜在机制仍然未知。
CAA患者的神经影像学
神经影像学在CAA的临床诊断中起着核心作用,由波士顿标准提供,最新版本于2022年发布。在年龄>50岁、出现自发性ICH(脑出血)、短暂性局灶神经功能障碍发作或认知障碍,并且在血敏感MRI扫描上有两个或更多严格的脑叶出血性病变(即脑叶脑微出血、ICH或皮质浅表铁质沉着症/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个体中,可以做出可能的CAA诊断。波士顿标准2.0版本所做的更新之一涉及添加非出血性MRI标志物,即白质半卵圆中心的MRI可见血管周围间隙的严重程度和皮质下多点模式的白质高信号(图2)。在有一个脑叶出血性病变的患者中,存在这些非出血性MRI标志物之一提高了可能CAA诊断的敏感性,而不影响特异性。MRI可见血管周围间隙的严重程度定义为一个半球的半卵圆中心可见超过二十个血管周围间隙。MRI上血管周围间隙可见性的增加最近被描述为可能发生在CAA疾病进展的早期阶段,在观察到出血性脑病变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血管周围间隙对CAA并不具有特异性,因为它们也可以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发现,包括涉及小动脉硬化和AD的脑小血管病。
图2 CAA的传统MRI标志物包括脑叶脑微出血和皮质浅表铁质沉着症(A)。最近,白质特征如MRI可见血管周围间隙的严重程度(B)和皮质下多点模式的白质高信号(C,箭头)被添加到波士顿标准2.0版本中,用于CAA的临床诊断。
SWI:磁敏感加权成像,FLAIR:液体衰减反转恢复
除了解剖MRI扫描上的这些发现外,功能MRI扫描还揭示了可能发生在CAA进展早期阶段的更微妙的疾病过程。通过使用利用血氧水平依赖(BOLD)效应的功能MRI方法,可以测量由视觉刺激引起的血流动力学反应。在散发性CAA患者以及遗传性CAA个体中,与年龄匹配的对照参与者相比,通过这种方法观察到更小和延迟的反应。在遗传性荷兰型CAA个体的症状前阶段,就发现BOLD反应减弱。此外,经过5年随访后,这些参与者的BOLD反应恶化,表明刺激诱发的BOLD功能MR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监测疾病进展。
CAA的病理进展
来自实验性小鼠模型、人脑组织的组织病理学分析以及遗传性、散发性和医源性CAA个体的体内影像学研究的互补研究的新见解,最近导致了CAA进展框架和时间线的提出。这个观察驱动的病理生理学框架表明,四个关键阶段似乎在大约2-3十年的过程中依次演变。第一阶段(阶段1)以皮质小动脉壁中的初始Aβ沉积为代表,如上所述,随后是生理性脑血管反应丧失(阶段2)。在CAA小鼠模型中观察到对视觉刺激的血管反应性丧失,其中血管Aβ沉积已取代血管平滑肌细胞,以及在携带家族性CAA荷兰型突变的症状前参与者中也观察到。阶段3的特征是非出血性脑损伤的发生,包括白质半卵圆中心扩张的血管周围间隙、白质高信号(主要呈皮质下多点模式)以及皮质微梗死。在死后人类研究中,这些损伤与血管中Aβ完全取代血管平滑肌细胞层且血管管腔变窄(Vonsattel 2级)相关。最后阶段(阶段4)是出血性脑病变发生时,包括脑叶脑微出血、皮质浅表铁质沉着症和ICH。与出血性脑病变相关的个别血管显示完全血管重塑的迹象,呈Vonsattel 3-4级病理。从这个框架可以得出,在生前符合可能CAA诊断标准的患者代表具有非常晚期或终末期CAA的个体。因此,可能是脑血管周围Aβ清除受损结果的初始血管Aβ沉积似乎发生在疾病可被临床识别之前的二十到三十年。这对开发新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策略可能会因针对的疾病阶段而有所不同。
CAA的啮齿动物模型
表达携带一个或多个家族性AD(FAD)突变的神经源性人APP的转基因小鼠一直是研究CAA最常用的实验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模型过度表达人FAD突变APP,在某些情况下,还含有早老素蛋白的额外FAD突变。通常,这些小鼠模型主要发展实质性Aβ斑块,随后产生不同数量的CAA,因此呈现混合脑淀粉样病理。然而,表达含有一个或多个家族性CAA突变的人APP的转基因小鼠模型已被证明可以特异性沉积血管Aβ。例如,在脑中表达荷兰E22Q突变Aβ的转基因小鼠发展出强大的CAA II型,尽管需要老化至≥24个月才能出现病理。另一方面,Tg-SwDI小鼠系在脑中表达嵌合荷兰E22Q/爱荷华D23N CAA突变Aβ,在几个月内就出现显著的毛细血管CAA(即CAA I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在没有实质性Aβ斑块的情况下独立研究CAA I型和CAA II型发病机制的范例,尽管它们在捕捉完整人类病症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局限性。最近,一个CAA I型的转基因大鼠模型,称为rTg-DI,像Tg-SwDI小鼠系一样在脑中产生嵌合荷兰E22Q/爱荷华D23N CAA突变Aβ。rTg-DI大鼠发展出早发性毛细血管Aβ沉积,捕捉了人类CAA I型的许多病理特征,包括血管周围神经炎症、脑微出血、小血管闭塞、白质退化和认知缺陷。类似地,产生的rTg-D大鼠在脑中表达荷兰E22Q突变Aβ,捕捉了人类CAA II型的许多病理特征,Aβ仅限于小动脉和小动脉,动物发展出脑微出血、闭塞的小血管和认知下降。这个不断扩大的CAA小鼠和大鼠模型集合为进一步研究这种病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机会。
然而,所有上述转基因啮齿动物系的一个显著缺点是,新出现的CAA病理是从”单一神经源”表达发展而来的。然而,神经血管单元的几乎所有细胞都表达APP并可以产生Aβ肽。因此,”单一神经源”转基因模型没有捕捉到CAA中Aβ细胞来源的复杂性,可能不能反映这种疾病的真实发病机制。啮齿动物基因编辑的最新进展有望提供更具生理相关性的平台来模拟人类CAA的真实发病机制。在这方面,正在开发新的基因编辑啮齿动物模型,这些模型以发育和空间正常的方式表达内源性啮齿动物APP,在Aβ结构域中进行特定氨基酸替换,从而在所有生理相关的细胞位点产生人类CAA突变Aβ。这些新颖的基因编辑啮齿动物模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在更生理的环境下评估CAA如何发展,从而规避转基因的许多人工高表达和”单一神经源”条件。
脑血管周围清除
引言和定义
血管周围间隙在历史上被称为Virchow-Robin间隙,以19世纪Virchow和Robin对其解剖描述命名。对血管周围间隙网络、其毗邻的血管和实质组织成分的功能相关性的认识是最近才受到关注的。因此,Cserr在1980年代的开创性工作提出了血管周围间隙对脑清除的贡献及其与颈部淋巴结的连接。大约20年后,Weller及其同事注意到清除受损对Aβ沉积的意义。在Iliff、Nedergaard及其同事2012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研究中,引入了”类淋巴系统”一词,描述了一种脑血管周围废物引流途径,在解剖上由血管和胶质细胞界定,支持脑间质溶质清除到CSF间隙。与随后表征的脑膜淋巴管系统和颈部淋巴引流的功能耦合提供了脑间质废物清除的综合视图。
最初的类淋巴假说包括沿动脉的CSF向心性流入、依赖于血管周围星形胶质细胞水通道水通道蛋白4的液体和溶质通过脑间质的对流运动,以及溶质沿静脉周围流出到窦相关CSF间隙。然而,围绕脑间质溶质转运的一系列实验观察导致了对这一概念的积极辩论和持续修订。Carare、Weller及其合作者引入了”壁内动脉周围引流”(IPAD)假说,该假说认为虽然CSF流入沿动脉周围通道发生,但废物溶质不是通过静脉周围通道流出,而是在动脉壁内逆血流方向流出。另一个流行的废物清除概念,称为”混合模型”,假设从ISF的废物转运是朝向动脉周围通道的,沿浓度梯度(即扩散)发生,并由生理运动(例如血管运动和心脏搏动[即弥散])的振荡”混合”促进。这些模型中容积流与扩散转运的相对作用和解剖范围不同,同样仍然是当前研究的重要主题。
专栏1
本综述中使用的”类淋巴系统”一词的定义=血管周围通道网络及其毗邻的血管和实质组织成分,其功能是促进间质液携带的大脑废物溶质的交换和清除。因此,它是一个工作模型,不仅包括传统的类淋巴假说,还包括IPAD和混合假说。
当前的理解和未知问题
关于小动脉周围转运途径的解剖和方向性缺乏共识;即溶质转运在小动脉壁内或旁边的精确位置,以及这是相对于血流发生顺行还是逆行。在较大血管水平,液体和溶质转运可能沿小动脉壁中平滑肌细胞的基底膜发生,而不是沿壁旁边的血管周围转运(即在平滑肌细胞/外膜的外层与胶质界膜之间)。一种可能性是这两种途径分别作为流出和流入路线存在(如IPAD模型所建议)。或者,只有一种途径,但方法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解释,从而产生了争议。这里重要的方法学考虑因素是示踪剂注射的位置和强度(注入CSF与实质内)、示踪剂的分子量和组成、时机,以及体内与死后分析。这里需要仔细的实验方法来对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示踪剂转运的系统分析,比较不同大小的分子、惰性与生物活性示踪剂、时间点,以及体内与死后数据的一对一比较,可以解决其中一些不确定性。
尽管沿动脉引流的精确解剖路线未确定,但关于静脉周围间隙和流动的数据报道很少,关于毛细血管周围间隙的更少。在人类中,大多数MRI可见的血管周围间隙被发现在动脉周围。假设血管周围间隙仅在病理性扩张时在MRI上可见,这可能意味着静脉周围的血管周围间隙不太容易扩张。其原因尚待推测。也许循环的静脉侧受血管病理影响较小,包括CAA和BBB功能障碍,这可能在血管周围间隙扩张中起因果作用。此外,动脉周围和静脉周围间隙之间的生物物理环境可能不同,包括局部压力梯度和流动剖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数据。关于静脉周围间隙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它们在液体和溶质引流中的作用。使用小鼠脑多光子成像的研究显示沿软膜动脉的搏动性血管周围流动,但关于静脉周围流动的此类数据很少。静脉周围流动更难描绘的原因有几个,包括沿静脉周围间隙的引流。首先,当示踪剂直接注入间质时,即使是小注射体积也容易压倒生理路线。其次,当注入CSF时,示踪剂在沿动脉周围间隙进入脑间质的大体积后被稀释。示踪剂流出的时机是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根据关于类淋巴系统的首批研究,示踪剂从间质的静脉周围流出可能在流入后几小时变得明显,这可能超出了大多数研究的时间框架。尽管存在这些技术困难,注入间质的示踪剂离开大脑到达CSF和淋巴系统的速度比单纯扩散预期的要快。这沿着优先路径发生,包括血管周围间隙以及白质束。动脉周围与静脉周围间隙在可溶性废物引流中的贡献,以及它们如何根据解剖位置、生理或病理状况而不同,是活跃研究的一个领域。
血管软脑膜段和皮质段之间过渡处的血管周围间隙之间的连接值得特别关注。研究表明,小分子和大分子,但不是微球(例如约1μm大小的荧光聚苯乙烯颗粒),从软膜表面进入血管周围间隙,然后沿穿支血管进一步延伸。与此同时,人脑的死后高分辨率解剖数据显示该位置存在软膜层。这些软膜层的功能相关性目前未知,但它们可能根据解剖位置阻止较大颗粒、细胞和注入微球的进入,可能充当某种筛子。缺乏微球沿穿支血管血管周围间隙的渗透限制了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直接观察研究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替代方法来确定沿穿支血管的流动模式。
除了解剖不确定性外,其他基本未知问题包括类淋巴系统的驱动力。源自心动周期的血管搏动是最早提出的驱动力之一。确实,观察到注入麻醉小鼠枕大池的荧光颗粒以心跳频率以搏动方式在脑表面移动。与这一假说一致,与血管搏动受损相关的状况,如衰老和急性高血压,显示类淋巴功能受损。然而,虽然关于血管振荡是否促进类淋巴功能几乎没有争议,但关于它们是否诱导净血管周围流动而不是往复运动的问题仍在持续辩论。建模研究在这一点上尚未达成共识。
除了由心跳产生的心脏搏动外,其他血管振荡来源可能促进类淋巴功能。呼吸影响人脑中的CSF运动,但对类淋巴功能的影响研究不多。然而,一项在自主呼吸大鼠中的研究表明,通过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增强呼吸功能可促进CSF以及类淋巴转运。由于呼吸振荡主要影响循环的静脉侧,这是进一步研究的有趣主题。最近,血管运动作为传统类淋巴和IPAD概念中的重要驱动力而出现。血管运动是指由平滑肌细胞收缩产生的大幅小动脉扩张,它可以在离体灌注动脉中自发发生,并被认为在活体小鼠脑中受神经元活动调控。使用非侵入性感觉刺激以内在低血管运动频率驱动血管反应性被发现可增加小鼠局部染料外渗的清除。由于血管运动期间直径的变化相对较大(与心跳诱发的搏动性振荡相比),振荡的血管周围液体体积也相对较大。有趣的是,血管运动在睡眠的某些阶段同步,主要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这与CSF运动的全脑振荡相关,与血流振荡呈负相关,意味着当脑血容量增加时,CSF被推出颅腔。因此,非常有吸引力的假说是,同步的神经元活动、血流和CSF运动在睡眠期间有助于脑清除。
专栏2
对流是流体的整体运动,其特征是其成分的平均(质心)速度,通常称为”容积流”。对流还表示通过这种整体运动在该流体中任何量(例如废物浓度、热量)的转运。
分子扩散是布朗运动的宏观表现,通过它浓度梯度倾向于根据菲克定律使介质组成均匀化。除了CSF中的自由扩散外,扩散过程还包括跨细胞膜的促进扩散,例如通过通道或载体,以及有效扩散,这是分子扩散在实质的不同成分(ISF、细胞质、细胞膜)及其微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扩散过程叠加在对流运动上,当异质速度场使具有不同浓度的流体靠近时,它们的组合可导致弥散,由于浓度梯度增加,导致比单纯扩散更快的均匀化。
CAA作为类淋巴系统疾病的证据
人类神经病理学研究
人类死后研究表明,毛细血管和动脉壁中Aβ的分布沿着围绕壁内细胞的基底膜。存在不同的模式,表明从基底膜中央部分的Aβ沉积进展到Aβ与中膜基底膜完全共定位,在疾病早期阶段使内皮和胶质界膜基底膜保持自由(图3)。这表明Aβ从实质引流的方向是从毛细血管基底膜进入中膜的基底膜,而不是从CSF流入,因为后者沿胶质-软膜间隙发生。
图3 人脑小动脉示意图,显示CSF进入大脑的建议进入路线以及初始血管Aβ沉积的位置(A)。具有CAA的人脑小动脉横截面的(X40 SP8)共聚焦显微镜图像示例,对Aβ(红色)、胶原蛋白IV(蓝色)和层粘连蛋白(绿色)染色(B)。注意Aβ围绕中膜的平滑肌细胞。SMCs:平滑肌细胞
在有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患者的脑组织中,发现错误折叠的转甲状腺素蛋白(TTR)在软脑膜中积累。在这些患者中,主要由外周和脉络丛产生的TTR沉积遵循这样的模式:软脑膜血管较早受到影响,然后是穿支皮质小动脉壁的沉积和软膜下沉积。由于在这种疾病中淀粉样蛋白首先被引入CSF间隙而不是实质,它可能提供一个有趣的”模型”来研究遵循传统CSF类淋巴流入途径的淀粉样蛋白沉积和分布模式。
另一个为理解类淋巴系统动力学提供信息的人类神经病理学数据来源来自参加首批Aβ免疫治疗试验的AD病例的脑组织。针对Aβ的主动免疫导致Aβ斑块数量和表面积的减少,但CAA恶化,表明Aβ在从斑块溶解后被困在其血管周围引流途径中。此外,Aβ免疫治疗与ApoE从皮质斑块重新分布到脑血管壁相关,因此反映了Aβ42从斑块到血管壁的分布模式。因此,血管Aβ的人类神经病理学分布表明它沉积在IPAD模型提出的存在于脑动脉中膜的途径中。
啮齿动物研究
越来越多来自啮齿动物影像学研究的文献表明,类淋巴系统促进血管周围Aβ转运,CAA形式的血管Aβ积累干扰该系统。研究血管周围可溶性Aβ运动的啮齿动物研究依赖于将示踪剂注入大脑的CSF或ISF间隙,然后进行实时体内或单时间点离体示踪剂流入或流出成像。在依赖将示踪剂注入枕大池的野生型小鼠研究中,一致发现示踪剂主要通过动脉周围而不是静脉周围间隙进入大脑。类似地,注入小鼠枕大池的荧光标记Aβ40通过动脉周围间隙进入大脑。实时体内多光子显微镜成像显示,小分子量示踪剂很容易进入间质,而较大(约2kD)示踪剂仍局限于动脉周围间隙。同样,Aβ40(CAA中沉积的主要种类)从CSF沿动脉周围间隙的流入似乎比Aβ42(主要存在于实质斑块中)更明显。如上所述,尽管有人认为注入枕大池的沿动脉进入大脑的示踪剂沿静脉清除,但缺乏支持这一说法的实时体内成像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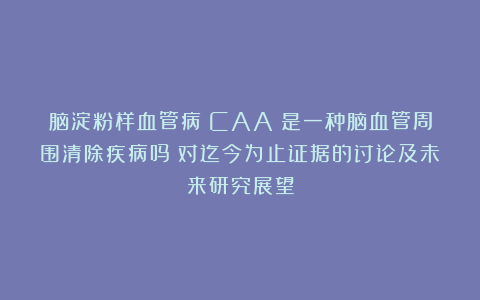
为了直接从间质(内源性产生的Aβ的部位)研究Aβ的清除途径,研究采用了实质内(例如在皮质、纹状体或海马)注射策略,然后进行标记Aβ模式的离体成像。发现放射性标记的125I-Aβ40从间质快速清除,在30-60分钟内清除超过一半的注射剂量。老年小鼠的清除率似乎降低,而睡眠、氯胺酮/甲苯噻嗪麻醉或含有右美托咪定的平衡麻醉剂可能改善清除。直接检查Aβ流出解剖途径的研究发现,注入实质的示踪剂主要最终进入毛细血管和小动脉壁,特别是围绕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基底膜中。有趣的是,一项研究发现,在有CAA的老年小鼠中,示踪剂定位从毛细血管和小动脉转移到小静脉。发现小静脉的葡聚糖标记与非常老的Tg2576小鼠的CAA严重程度成正比增加,因此22月龄小鼠显示小静脉标记显著多于年轻或成年小鼠。
在产生突变人Aβ的转基因小鼠中,观察到示踪剂流入和流出均受损。此外,水通道蛋白4的基因缺失导致Aβ40流入或清除显著减少,表明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上的这些水通道促进大脑中的Aβ转运。
实时多光子显微镜研究帮助阐明了体内脑血管周围清除的驱动力。如上所述,血管搏动早期就被认为有助于促进沿血管周围间隙的示踪剂运动。实时跟踪注入麻醉小鼠枕大池的荧光颗粒表明,沿软膜动脉的CSF流动是搏动性的,由心动周期产生的逐搏小动脉搏动驱动。最近,在未麻醉小鼠中的研究指出血管运动是促进沿动脉周围间隙示踪剂运动的另一个可能候选者。依靠神经血管耦合原理,在小鼠中以约0.05 Hz为中心的固有血管运动频率进行视觉刺激,被发现可显著增加血管扩张以及野生型小鼠软膜表面血管周围间隙的示踪剂清除。值得注意的是,发现有CAA的转基因小鼠中视觉诱发的血管反应性受损,这与这些动物中CAA阳性血管沿线示踪剂清除受损相对应。与这些发现一致,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胡须刺激诱导的功能性充血期间,示踪剂流入显著增加。此外,当使用光遗传学直接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从而绕过神经血管耦合时,发现与无刺激相比,示踪剂流入同样增强。这些发现表明,平滑肌细胞介导的阻抗泵送可能是促进包括Aβ在内的溶质在大脑中运动的关键驱动力。
最近使用动态对比增强MRI(DCE-MRI)结合枕大池内给予Gd标记示踪剂在CAA I型转基因大鼠模型中研究了类淋巴溶质转运和清除。该研究在CAA I型转基因大鼠(rTg-DI)系中进行。观察到高速蛛网膜下CSF流动重新路由远离大脑,导致类淋巴转运下降以及向颅外淋巴结的异常溶质清除。因此,在rTg-DI大鼠中,溶质引流到深颈淋巴结延迟,并”溢出”流出到附属淋巴结。这些CAA大鼠的结果与慢性高血压脑小血管病大鼠模型中DCE-MRI研究获得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rTg-DI CAA大鼠模型不是高血压)。例如,在有慢性高血压的自发性高血压卒中易发大鼠(SHRSP)中,CSF流动”缓慢”,并与类淋巴转运减少相关,这意味着血管搏动和CSF流动跟踪是捕捉神经退行性疾病状态下类淋巴-淋巴系统转运病理生理学的重要指标。
体内人类研究
除了神经病理学发现外,支持CAA病理生理学与脑清除变化相关的证据来自CSF样本测量。与AD患者中观察到的类似,CAA患者的CSF中Aβ40和Aβ42均降低,对应于这些肽在大脑本身的积累增加。在荷兰型CAA个体中,发现与年龄匹配对照相比,五名症状前突变携带者组的CSF中Aβ浓度降低,这种浓度降低比散发性CAA更严重。此外,注意到Aβ42的降低大于Aβ40,这可能表明Aβ42的积累先于Aβ40,尽管这些发现需要在更大样本中复制。在血浆中也获得了类似的发现。
从神经影像学角度来看,CAA患者脑中MRI可见血管周围间隙的发生很突出。半卵圆中心的MRI可见血管周围间隙与死后测量的皮质局部CAA严重程度增加相关,与体内测量的Aβ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阳性增加相关,表明Aβ清除受损与血管周围间隙扩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血管周围间隙的扩张可能是皮质小动脉Aβ沉积的继发效应,导致下游连接间隙中的血管周围液体流动受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其他潜在机制包括白质组织损伤的直接影响或大脑白质内可溶性Aβ的存在。
关于可能影响类淋巴功能效率的驱动力,人脑中研究最多的过程是血管反应性。血管反应性受损被假设由于血管壁僵硬和活动性降低而降低类淋巴功能。在散发性CAA和荷兰型CAA中,对视觉刺激的反应均被发现延迟和减弱。此外,在荷兰型CAA的4年随访中,脑血管功能障碍的这些迹象恶化。这可能诱导自我放大循环:由于清除受损,Aβ开始在血管壁中积累,血管壁变得更僵硬,血管运动减少,这进一步损害清除,导致更多Aβ积累。作为一个真正的循环,当然不知道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这应该是未来研究阐明的一个重要点。
未来研究/知识空白的展望
解剖学
理解类淋巴清除的血管周围途径的解剖结构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它需要以纳米级分辨率对血管系统进行成像以可视化血管壁结构,但需要跨越数百微米以了解沿小动脉-毛细血管-静脉轴的血管结构差异。最近使用连续块面电子显微镜(EM)大规模绘制神经回路的努力已经证明了创建此类数据集的可行性,但创建和分析这些数据的复杂性很大。特别是,由MICrONs联盟创建的皮质MM^3数据集,包含以超微结构分辨率成像的一立方毫米成年小鼠视觉皮质(图4)。数据包含关于微血管结构的广泛信息,包括所有神经血管细胞类型、血管周围间隙和包围血管细胞的基底膜层。它提供了未来绘制脑膜和血管周围3D路线可以实现的一瞥。
图4 来自MICrONs皮质MM^3体积EM数据集的穿支小动脉壁和血管周围间隙(A)。小动脉壁的放大视图显示血管周围间隙随皮质深度增加而尺寸减小并成为不同血管细胞类型的紧密层(软膜表面朝向图像顶部)。具体而言,血管周围间隙似乎与血管周围成纤维细胞层和围绕这些细胞的基底膜连续。EC:内皮细胞,BM:基底膜,SMC:平滑肌细胞,PVF:血管周围成纤维细胞,AC:星形胶质细胞。改编自[101]。来自小鼠皮质的穿支小动脉的2D横截面和体积渲染,显示血管周围间隙的超微结构(B)。黄色=一个星形胶质细胞。蓝色/绿色=两个单独的平滑肌细胞
未来的工作可以从微血管网络所有区域获得神经血管细胞、间隙和非细胞成分的可量化3D形态计量学,并开发用于这些结构自动检测的分割方法。需要这些信息来理解流动路线和CSF流动的屏障或阻力点,这可能无法从局部2D成像中识别。例如,关于脑膜层的解剖仍存在激烈争论,其中包含蛛网膜下腔内CSF灌注的血管周围路线。然而,对这些脑膜血管周围网络如何组织以及它们如何与穿支小动脉的血管周围间隙连接的了解有限。如上所述,一些观察表明存在软膜层,可能限制蛛网膜下腔和血管周围间隙之间的CSF流动。这些层是否造成CSF流动阻力,它们是否存在于所有穿支小动脉上?此外,血管周围间隙内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周围巨噬细胞的大小和位置也会对CSF流动阻力产生影响,应该更深入地理解以准确建模CSF转运。包围血管壁的基底膜的尺寸和连续性也需要在3D中理解,因为可以推测这创造了当血管周围间隙沿较小脑小动脉减少时CSF流动的路线。星形胶质细胞终足的覆盖范围也仍然特征不明确,但对于理解CSF-ISF之间的液体交换是否可以通过镶嵌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之间的间隙发生(除了该水平的水通道蛋白4介导的液体交换)至关重要。关键的是,如下所述,这些解剖数据应该在正常和CAA组织中表征,并与使用新的体内成像方法沿特定血管周围间隙的CSF流动生理测量联系起来。
许多初步见解来自对从正常成年小鼠脑获得的MICrONs皮质MM^3的定性调查。例如,某些但不是所有皮质穿支小动脉都可以辨别血管周围间隙,且仅在上层皮质层。血管周围间隙由软膜和内皮基底膜界定,包含血管周围成纤维细胞和巨噬细胞。间隙逐渐消失并成为嵌入基底膜内的内皮、壁、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层的密集壁。当较小的微血管从穿支小动脉分支时,小动脉-毛细血管过渡区或毛细血管周围没有可辨别的血管周围间隙,但基底膜本身可能作为CSF转运的多孔介质。沿皮质小静脉也没有看到血管周围间隙,尽管有一层基底膜。关键解剖特征的量化,如血管周围间隙的尺寸和基底膜的厚度和连续性,对于建模CSF流动的努力将很重要。
在CAA啮齿动物模型中应用体积EM技术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CAA如何改变神经血管单元和血管周围间隙。血管占总脑组织体积的一小部分,需要广泛扫描然后从特定血管感兴趣区域收集体积EM的成像策略,以捕捉血管间异质性CAA病理。可以将电子密集示踪剂注入枕大池,这些示踪剂可通过EM检测,以可视化CSF能够在血管周围间隙携带溶质的位置。这些努力将深入了解CAA诱导的小动脉扭曲和血管周围间隙扩大如何与神经血管细胞类型和基底膜完整性的细胞/亚细胞水平变化相关。在人类中,扩大的血管周围间隙在脑白质中更普遍。应该在灰质和白质之间进行特定比较,以了解为什么某些组织受影响更严重。需要决定哪些模型最能与临床数据一致。几种大鼠和小鼠模型表达带有不同突变的人APP,导致脑小动脉到毛细血管更多Aβ沉积,这可能有助于区分人类中观察到的CAA I型与CAA II型的特征。
在神经回路绘制中考虑的与组织固定和细胞外间隙保存相关的注意事项也适用于血管/血管周围间隙。重要的是确定体积EM的典型固定和处理是否由于组织收缩或变形而影响血管周围间隙尺寸。这可能需要在用于体积EM的相同样本/区域进行体内多光子成像,以便可以在单个血管水平进行直接比较。此外,需要研究以确定固定程序是否影响引入CSF中的示踪剂的分布。
体内小鼠成像研究
体内多光子显微镜和MRI一直是用于研究小鼠脑清除动力学的主要方法。如上所述,典型研究涉及测量注入脑组织或枕大池内注射后标记CSF的外源示踪剂的清除。荧光染料也被注入枕大池以填充血管周围间隙进行结构成像,或跟踪软膜表面血管周围区域小荧光珠的运动。多光子研究涉及产生颅窗以对小鼠皮质中的染料进行高分辨率局部可视化,而MRI研究通常使用大鼠,因为它们的脑尺寸更大。小鼠和大鼠模型系统之间的差异,更不用说啮齿动物与人类系统,尚不清楚,这使得将来关联多光子和MRI数据可能具有挑战性,此外还有正在检查的不同空间尺度。
使用体内成像研究类淋巴清除的最佳实践仍在完善中,关键问题是麻醉剂、手术程序和染料注射程序如何影响CSF流动和溶质转运。早期研究在麻醉下进行,显示氯胺酮/甲苯噻嗪或异氟烷/右美托咪定组合最适合在枕大池内注射后进入血管周围间隙。正在向成像未麻醉、头部固定的小鼠转变,因为这将最好地捕捉原生CSF流动动力学并允许在睡眠状态期间成像,这可以通过监测脑活动或瞳孔直径来跟踪。然而,对MRI研究来说,成像未麻醉的啮齿动物仍然具有挑战性,一些镇静剂可能作为替代品。多光子成像研究需要创建颅窗以进行光学访问。然而,关于手术引起的颅内压变化、组织压迫和炎症反应如何影响CSF流动知之甚少。在小鼠中,侵入性较小的变薄颅骨颅窗可能是一种补充方法,以验证使用传统颅骨去除窗研究的关键发现。
未来的研究还应该尝试克服急性示踪剂注射对类淋巴清除研究的局限性。例如,研究表明,小套管或针头的急性植入可以抑制CSF流动动力学和类淋巴转运。最近的离体研究表明,通过增加从套管植入到测试类淋巴转运的时间,可以改善针刺或植入造成的急性组织创伤。对于实质内和枕大池内注射,应尽可能保持小体积以减少颅内压增加和组织损伤。另一个基本局限性是荧光示踪剂的局灶性注射从注射点产生人为扩散梯度。为了区分扩散和对流示踪剂运动,并最小化对组织损伤的急性反应,可能可以通过渗透泵将光激活示踪剂分子长期输送到CSF和ISF中。这将允许首先在整个大脑中建立稳态水平的示踪剂,并且可能跟踪光激活染料在组织实质或血管周围间隙中的清除/流动方向。此外,有必要了解血管周围间隙的体积如何随清醒啮齿动物的生理节律(心脏搏动、呼吸、血管运动)变化。然而,理想情况下,这应该在没有外源示踪剂注射的情况下研究,因为这可能改变CSF的体积或粘度。荧光标记围绕血管周围间隙的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平滑肌细胞)的转基因或病毒方法可能是非侵入性研究周细胞间隙尺寸的一种方法(图5)。
图5 使用多光子显微镜体内可视化由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界定的穿支小动脉血管周围间隙。图像在异氟烷麻醉小鼠中拍摄。星形胶质细胞(绿色)由AAV-GFAP-Lck-GFP标记,平滑肌细胞(SMCs;红色)是PDGFRβ-tdTomato小鼠的内源性标记
类淋巴清除的人类成像
由于脑血管周围清除受损是最近提出的涉及CAA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测量人脑中血管周围清除效率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我们关于类淋巴清除的大部分知识来自啮齿动物模型,其中可以应用如通过颅窗的多光子显微镜等侵入性技术,但我们测量,更不用说量化活人脑清除的能力有限。目前人类脑清除成像的金标准是基于鞘内注射MRI造影剂,然后在2天内以3-6小时的间隔进行动态T1加权MRI。这些实验产生了关于类淋巴系统的大量信息,并强调了人类和啮齿动物之间的重要差异。然而,两个重要的缺点将阻碍这种方法的广泛使用。首先,它依赖于鞘内注射,尽管副作用以及造影剂在脑组织中的滞留数量都非常轻微,但它仍被认为是一种高度侵入性的程序。此外,它依赖于造影剂的超说明书使用。其次,这些测量具有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因为造影剂首先需要流入大脑,进入脑组织,然后被清除。这意味着测量在24-48小时内进行,这为广泛使用提出了另一个障碍。尽管静脉注射已被提出作为更友好的患者替代方案,但这些实验也依赖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数据解释很复杂,因为进入组织将取决于BBB的完整性,或造影剂通过其他途径(如进入蛛网膜下腔)进入。
因此,需要非侵入性技术来测量脑清除。正在开发几种方法,其中大多数依赖于测量类淋巴系统不同水平的CSF流动性。一般论点是许多废物可溶于水,CSF是将这些废物运出大脑的通道。Fultz和Lewis研究了CSF流动性以及与血管运动的关系,通过皮质灰质中低频BOLD波动与第四脑室CSF流入的耦合来测量。重要的是,他们还使用MRI兼容的EEG在睡眠期间研究了这些现象以监测睡眠阶段。他们表明,第四脑室的CSF流入与脑活动的低频振荡相关,这些生理过程在睡眠期间增强。同样的方法还表明,这种耦合在AD中受到干扰。与造影剂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这些测量观察血管运动活动和CSF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总扫描时间为5-10分钟。这样的扫描(类似于标准静息态功能MRI扫描,其最低切片通过第四脑室规划)可以很容易地插入临床研究或用于监测随时间的变化。然而,第四脑室距离Aβ产生或CAA中积累的位置相当远。因此,正在开发其他可以测量更接近内源性Aβ产生部位的CSF流动性的方法。例如,通过利用CSF较长的T2,可以通过使用长回波时间来分离CSF信号。这种方法已在啮齿动物模型和人类研究中得到利用。最后,最近有研究测量心脏和呼吸周期期间的脑组织变形,假设这些变形可能有助于驱动大脑的清除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可能应用最广泛的技术是沿血管周围间隙的扩散张量成像(DTI-ALPS)分析,可以在相当标准的DTI扫描上进行。该概念基于静脉周围间隙与脑室旁区域主要白质束的垂直方向。一项研究考察了DTI-ALPS在CAA中的应用,发现DTI-ALPS指数降低,这种降低与基底神经节血管周围间隙扩大、白质高信号严重程度和认知障碍相关。应该注意的是,关于DTI-ALPS是否是类淋巴活动的准确测量正在进行讨论。该分析因仅关注大脑中的一个小区域、未分离CSF信号以及许多研究中未检查静脉周围间隙的方向而受到批评。因此,结果应谨慎解释。
啮齿动物MRI作为人类成像的桥梁
动态对比增强MRI(DCE-MRI)结合CSF给予Gd标记示踪剂被引入作为临床前成像方法来研究啮齿动物脑中的类淋巴转运。当标记有Gd示踪剂的CSF在2-3小时内以独特的空间分布模式进入脑实质时,该方法捕捉类淋巴转运。具体而言,啮齿动物DCE-MRI研究可视化Gd造影剂进入大脑的两个主要”波”:向嗅球移动的”腹侧”波和向松果体隐窝移动的”背侧”波。在区域上,腹侧波包括脑干、下丘脑、额叶和嗅觉皮质,而背侧波包含小脑、枕叶和后扣带皮质、海马和中脑。这种Gd示踪剂在啮齿动物脑中摄取的特定模式已在其他几种动物物种中重现,包括非人灵长类、犬类和猪类,以及在人脑中。到目前为止,基于DCE-MRI的啮齿动物和人脑类淋巴转运研究产生了大致相似的结果:
(1)Gd示踪剂流入脑实质的全脑分布模式相似,尽管时间尺度不同;
(2)Gd示踪剂从蛛网膜下CSF流入沿穿支动脉发生;
(3)脑实质中的Gd示踪剂转运在区域上是异质性的;
(4)Gd示踪剂从脑实质清除需要几个小时;
(5)Gd示踪剂引流到颈部淋巴结。尽管DCE-MRI已成为测量全脑类淋巴转运的”金标准”成像技术,但它是侵入性的,在人类中不适合常规使用。如上所述,继续引入侵入性较小的MRI技术以进一步探索人类CSF流动动力学,其中一些源自啮齿动物MRI。例如,Harrison及其同事使用高空间分辨率扩散加权MRI测量大脑中动脉周围的CSF流动性,随后也在人类中提出。然而,鉴于除水之外,任何这些技术都没有”溶质”转运的明确测量,仍然迫切需要将现在在文献中称为”类淋巴转运”的替代MRI指标与临床前研究进行交叉验证(图6)。
图6 动脉自旋标记(ASL)是一种合适的转化MRI技术,可在大鼠和人脑中非侵入性地捕捉血液到CSF的水交换。通过采用较长的标记持续时间、较长的标记后延迟时间和较长的回波时间,可以捕捉标记自旋在CSF中的到达。较长的回波时间确保来自脑组织的信号已经消失,只留下水样区域(如脑室和皮质CSF)中的信号。注意交换不限于脑室,还存在于皮质周围。
根据类淋巴系统模型,容积流驱动的动脉周围CSF转运促进CSF-ISF混合和通过静脉周围通道的废物清除。其他研究进一步表明,类淋巴系统与脑膜淋巴管系统(mLV)耦合,”脏”脑液的静脉周围流出汇集到mLV中,主要引流到深颈淋巴结(dcLN)。外科方法(例如结扎通往dcLN的传入淋巴管或切除dcLN)使类淋巴系统与淋巴引流途径解耦,揭示了某些啮齿动物模型中神经退行性病理的加速。然而,类淋巴-淋巴系统解耦对脑健康负面影响的潜在机制仍然不完全理解且存在争议。
开发新的综合计算模型
随着研究寻求定义血管周围转运和类淋巴功能,计算建模已成为定义这一生物学并开始理解其在生理条件下如何调节以及在病理状态下如何失调的关键工具。有关计算建模在类淋巴功能研究中应用的更完整讨论,读者可参考Bohr及其同事最近的综述。简而言之,当我们试图理解控制脑废物清除的过程时,计算建模方法可以发挥几个有用的作用。
首先,模型可以作为一个通用框架,其中可以整合不同类型和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以告知生物过程。例如,最近三项不同的成像和组织学研究报告了软膜表面血管周围间隙的形状和大小、这些血管周围间隙内的流速以及皮质内血管周围星形胶质细胞终足尺寸的直接测量,这些方面预计会影响血管周围液体和溶质转运。虽然每项研究都是孤立进行的,其结果不能直接相互关联,但计算模型提供了一个整合这些观察并理解它们对沿血管周围间隙液体和溶质转运的各自和综合影响的媒介。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将这些和其他特征整合到血管周围类淋巴交换的网络模型中,试图定义最可能调节血管周围转运和废物清除的解剖和物理特征。
计算建模的第二个优势是能够跨不同生物相关长度和时间尺度整合数据和过程。考虑长度尺度,脑细胞外间隙以数十纳米为单位测量,血管周围间隙直径范围可达数百微米,血管直径从几微米到几毫米,脑血管网络包含数百公里的总血管长度。对于跨BBB的脑废物,清除发生在分隔相邻毛细血管的特征长度上,通常为几十微米,而非BBB转运溶质的清除在人脑中必须跨越分隔脑室内部CSF间隙和脑池外部CSF间隙和蛛网膜下腔的厘米距离。然而,通常只能在单一长度或时间尺度上通过实验方法处理这些过程。EM提供了脑组织最精细的解剖视图,但通过这种方法分割和注释单个1 mm × 1 mm × 1 mm体积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MRI提供了整个小鼠或人脑中解剖、水和溶质转运的视图,但可实现的分辨率通常在任何维度上都不超过1毫米。计算模型提供了在比实验可实现的更大尺度上详细说明精细解剖细节和物理测量的机会,或者允许将这些细节简化为反映精细实验现实的集总特征,但以简化形式使其能够扩展到与人类疾病相关的解剖和时间尺度。
如Bohr及其同事所指出的,当计算建模研究建立在明确陈述的假说基础上、在报告假设和适用条件范围时透明、能够解释现有观察和实验数据并允许产生可通过实验测试的后续可证伪假说时,已被证明对理解类淋巴功能最有用。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流体动力学模拟来评估有助于动态颗粒跟踪研究捕捉的脑表面血管周围液体运动观察的潜在机制。这些模拟表明,虽然血管周围间隙内颗粒的振荡运动可归因于动脉壁的蠕动运动,但这些间隙内颗粒的净通量更可能归因于稳定的低量级(1-2 mmHg)压力梯度。该研究以实验数据为基础,详细阐述了现有的血管周围液体和溶质转运模型,并提供了明确的可测试假说,即血管周围液体转运的源和汇之间存在低量级压力梯度,并且血管周围转运对该梯度的实验操作敏感,可以验证或使该领域工作模型的这一新部分失效。在第二个例子中,上述网络模型已用于探索可以实现通过脑组织快速液体交换、表现出睡眠-觉醒功能差异并由低量级压力梯度驱动的解剖和生理参数。基于该模型的敏感性分析表明,实质液体转运可能对星形胶质细胞终足之间的间隙大小高度敏感,这些间隙将低阻力血管周围途径与更广泛的间质分开。这些发现表明实验者应采取的可行下一步,以评估这些间隙是否被调节以调节跨生理条件的溶质转运。
定义类淋巴系统变化在CAA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适合利用计算建模的主题。血管Aβ沉积是在单个或小群脑血管水平发生的中尺度现象。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由脑细胞外间隙和血管壁的微观变化以及脑血管网络和CSF流动动力学的宏观、非局部转运特性所定义。最可靠的解剖数据来自在啮齿动物脑中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EM研究,关键的溶质转运见解最容易通过体内动态成像方法(如多光子显微镜和对比增强MRI)获得。然而,在临床上,CAA在更大、更复杂的人脑中发生,时间尺度为数十年。因此,计算建模整合来自血管周围转运和脑废物清除的各种研究数据、弥合这些过程发生的多个空间尺度以及将啮齿动物脑的发现和机制见解与人脑的广阔解剖尺度联系起来的潜力,在CAA背景下可能至关重要。反过来,确定哪些建模假设最适合解释向CAA的过渡可能有助于理解脑中废物清除的一些基本方面,为类淋巴系统当前争议提供见解。
讨论
替代解释
如本文所综述,主要来自人类神经病理学观察和啮齿动物模型测量的几条证据表明,类淋巴功能障碍是CAA疾病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然而,重要的是考虑关于观察到的血管Aβ沉积模式的潜在替代解释,这些解释不一定支持CAA是血管周围清除受损的结果或伴随血管周围清除受损的理论。
首先,在使用标记Aβ作为示踪剂的实验中,如许多啮齿动物研究(以及使用PET的患者研究),应该考虑细胞或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强可能不一定是因为它们参与血管周围脑清除,而是因为它们优先结合示踪剂。例如,在使用Aβ作为示踪剂的啮齿动物研究中观察到的动脉增强可能不一定是因为动脉是主要清除路线。一个合理的替代解释可能是动脉具有某些特征,如血管平滑肌细胞,其具有可能隔离或阻碍Aβ清除的成分。
其次,众所周知,除类淋巴清除外,Aβ清除还依赖于几种其他机制,如酶促降解和跨BBB转运。已显示Aβ积累与BBB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丧失相关,进一步介导大脑中Aβ积累。小鼠研究使用了14C-菊粉,它不通过BBB清除,并观察到与血管周围清除相似的速率。对于跨BBB与通过类淋巴系统清除的比率是否在疾病过程中或随着CAA严重程度增加而变化,仍不完全理解。此外,这一比率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发展CAA的不同风险概况。
第三,Aβ可以与其他蛋白质共沉积。最近的工作表明,Medin(MFG-E8的蛋白质片段)在50岁以上人类的血管系统中沉积。Medin在人脑和APP转基因小鼠中与Aβ沉积共定位,并直接促进其聚集。此外,Medin缺陷小鼠显示血管Aβ沉积减少50%。来自同一组的早期工作表明,Medin聚集也导致衰老小鼠的脑血管功能障碍。其他倾向于”粘附”Aβ的蛋白质是血浆蛋白,如纤维蛋白(原)和IgG。人脑组织中的神经病理学观察确实表明CAA与小动脉壁中的这些血浆蛋白共定位。使用体外测定的额外工作已证明Aβ与纤维蛋白原相互作用的高亲和力,并揭示突变Aβ,包括荷兰型CAA,导致结合亲和力增强高达50倍。因此,血管系统中Aβ的积累可能反映该蛋白质在BBB水平与这些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的亲和力。
最后,如果血管周围Aβ清除受损确实涉及CAA的病理生理学,仍不清楚初始类淋巴功能障碍是否导致血管Aβ积累,或者由于潜在替代机制的小动脉早期Aβ沉积是否导致清除受损。此外,类淋巴系统的参与可能因与疾病过程不同阶段相关的观察病理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
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愿景
关于类淋巴系统的基本生物学机制和血管周围Aβ清除在CAA病理生理学中的作用,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突出的知识空白需要临床前、临床和计算研究者之间的成功合作,他们从不同角度处理这些基本未知问题。我们对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愿景是利用多学科研究人员组的专业知识,他们共同渴望推动该领域朝着理解CAA病理生理学迈进,并朝着开发这种常见且使人衰弱疾病的新治疗靶点迈进。这就是我们启动Leducq基金会脑清除跨大西洋卓越网络的原因。在这个网络内,我们努力开发统一的实验方案,这些方案将与更广泛的科学界共享。希望是具有互补技术专长和观点的参与研究者的独特跨学科组合,他们经常持有相反观点,将通过共同解释和协调实验发现来加速转化影响。此外,我们将努力在啮齿动物中采用微创成像方法,催化开发新的MRI方法以捕捉人脑中的液体流动,并在综合计算模型中跨尺度和模态整合观察。
总之,CAA既代表一种高度相关的神经血管疾病,也是一个有用的”模型系统”,可以利用它来阐明关于类淋巴系统的当前争议。从血管Aβ积累模式和啮齿动物和人脑中CAA相关病理以及实验环境中的实时液体流动动力学得出的见解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目前关于CAA的可用信息还不足以排除其他潜在解释。迫切需要在人类和啮齿动物中进行进一步实验,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关键空白。此外,关于类淋巴衰竭与血管系统中Aβ积累之间关系获得的新见解将与理解抗淀粉样蛋白免疫治疗背景下ARIA形成的机制高度相关,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临床相关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