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住在北京前门外大外廊营,在那一条胡同里,住有许多著名京剧演员。我因不断和他们接触,对于京剧演员的生活就比较熟悉。解放后,我的儿子也入了京剧界,我和京剧演员的来往就更加频繁。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京剧演员的地位变化格外显著。在旧社会,戏剧演员是一直受统治阶级轻视的,而在解放后则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受到人民的尊敬。
最近有个演员向我说:“旧社会,演一天戏,开一天份儿,没有固定工资,挣得多,还是拉亏空。几个月不唱戏,就要当尽卖绝。现在我们每月领工资,谁家里没有存款?”
其实,据我所知,旧社会一般京剧演员,不仅收入不多,而且和其他有些行业一样,还要遭受各种封建把头的剥削。
当时的观众,只看到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谁知道这些演员每天价怎样含着眼泪吞下他的窝头?现在事过境迁,年轻的一代,那就更无法想象。
一
据我个人生活圈子里的见闻,旧北京京剧界里最早的一个把头应该算是余玉琴了。
余玉琴、陆华云之《十三妹》
余玉琴原籍安徽,幼年从原籍来到北京唱戏,专工武旦。有出拿手戏叫《大卖艺》,踩着跷在饭篓上练功夫,轰动了北京城。他小名叫“桩儿”,当时提起余桩儿,人人称赞。后来他被叫进清宫演戏,西太后和光绪都爱看他演的戏。以后就经常在宫里演戏。是清末最著名的武旦演员,后来的阎岚秋(九阵风)、八仙旦等著名演员,都是他的徒弟。
余玉琴是我的邻居,我称他作干爹,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已不再登台演出了。
据著名的丑角演员迟子俊向我说:“在清朝末年,有四个班主。可是在余桩儿盛时,每逢王府演戏,总是由余领班。过去演员唱多少戏,给多少戏份儿,都有一定规矩。可是到了余桩儿这儿,随便由他给。给多少是多少,谁也不敢言语。”
迟子俊说:“我是个唱彩旦的,挣钱最少。人家大筐端银子,我只拿点碎银子,一叠大钱。我们苦哈哈,等着钱买棒子面呢。可是几钱散碎银子,都很零碎,五块里必有一块假的。除了谭老板(谭鑫培),你干爹不敢惹,差不离儿的人,都接过他的假银子。姑娘,人家挣得多,不在乎此。我们多挣一钱银子,为的是活命,他还给一块假的。这个怨气,哪儿说去,只有一个字,认!”说到这儿,这位老艺人总是恨恨地说:“你干爹缺了德,儿女不会好的。”余桩儿的假银子是哪儿弄来的呢?原来有个穆子光,就指着造假银子发财。他盖下了一座望园,还开了东升平、西升平两家澡堂,在当年都是新兴的企业。余桩儿就和穆子光合作,使用假银子,专门剥削穷人。
余玉琴便装照片
民国初年,也有一个名演员垄断了当时北京的戏剧界,那就是俞振庭了。
俞振庭是清末名武生俞菊笙的儿子。俞菊笙外号俞毛包,一般人就称俞振庭为小毛包。民国初年的武生名演员杨小楼、尚和玉都是俞菊笙的徒弟,所以俞振庭和杨、尚齐名,演戏以火炽见长,他演的《金钱豹》耍叉的功夫,十分出色,内外行都很称赞,认为是一绝。
俞和杨、尚有个显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特具办事的才能,善于交际联络,所以经常自己成班。他很有眼力,哪个演员“是块材料”、“有出息”,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京剧的著名演员,有很多是他培养出来的。民国初年,他在文明茶园当班主,梅兰芳就在他的班里唱中轴,逐渐成名的。
俞振庭因为和袁克文争风吃醋,在演戏时下台殴打袁克文,判处三年徒刑。蹲了三年大狱,把肚子蹲大了。出狱以后,舞台上的艺术,已经大不如前。从此,他就很少上台演出,以成立戏班(剧团)作为他的主要业务了。
他一个人经营了两个戏班,一个叫作双庆社,一个叫作斌庆社。下面先说双庆社。
在旧社会里,一个演员要登台演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城里,当时只有有限几家剧场,而且早都被几个戏班常年租用了。要演戏,不能一个人唱,必须有同台演唱的演员,有演剧所用的服装道具一戏箱。所以必须有一个组织,这在当年就叫作“戏班”。
戏班成立的时候,要经当地政府的许可,演出以后也要和当地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还要应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文武流氓,对于一个戏剧演员来说,这当然很不简单了。所以除了几个有名演员自己成立了一个戏班以外,一般都是搭班演唱,即搭入别人已经成立的剧团参加演出。这种剧团的承办人就叫作“班主”,一般人称之为“老板”。
当年北京的演员是没有固定的工资一包银的,一般是演一天给一天报酬,叫作“开份”。
俞振庭自己当老板,手下还用着一批管事的。每天晚上“开份”就由管事的负责,每场在演第三出戏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高级演员是由跟包的代领;一般演员和底包、龙套等人就自己去领。演员演出一场戏,拿多少钱,本来事先说好的,这用行话说叫作“讲公事”。尽管把公事讲好,可是发多少却由管事的临时决定,要看这一天上座儿多少。戏份都事先包好,演员照例不可以打开当面看的。如上座较少,演员的报酬就要打折扣,行话谓之“打厘”。如果上座太惨,甚至可以不付报酬,叫作“拍巴掌”。
龙套演员收入最少,在一般演员“拍巴掌”的时候,龙套也要照付;这似乎是对贫苦演员的照顾了。跑龙套讲究“龙头龙尾”,即头旗、四旗领跑,拿的钱比二、三旗略多。当时头旗每天挣100铜子;末旗挣60个子儿;二、三旗才挣50枚铜元。但每人每天,管事的要扣下1大枚。唱武行的演员,每天的份儿是1块到2块,也扣下1大枚,一律按人计算。
每天开支都由管事的作主。比如园子卖了个满座,收人五六百元,除去开支二三百元之外,余下全属俞的。如果卖了半堂人,演员的戏份打厘,他仍可以剩下一半。而且卖座如何,全凭管事人口头一说。明明戏园子里起满坐满,管事的可以对演员们说:“今天官面上要了几个包厢;某处某处要了多少座,客票(白看戏的)占了不少。看座儿挺多,实际收入不够。”这样,虽然卖了满座,戏份仍要打厘。总之,演员倒霉而已。当时一、二路演员,明说10块钱的戏份,一般只能拿到6块;如果上座不佳,3块2块都是平常的事。
最惨的还是底包们,收入不多,还要应酬管事的。因为底包们收人不多,演一场戏,挣个一块半块的,不够养家活口,必须连赶几处。戏班的管事人都互相通着的,只有经常把管事的联络好了,他才能适当地派戏码,让你可以同时赶几个园子,多演几场戏。
盖叫天、俞振庭之《英雄义》
在俞振庭那时候,管事的都得听他的,唱一场戏分多少钱由他支配。按照当时的规矩,堂会戏开两个半份;出外演堂会,就开三个份。可是由他承办的堂会,一切由他随意开支。不仅班里演员如此,外面邀请的角儿也是如此。
俞振庭凭着一个双庆社,就垄断了北京的戏剧界。只要在北京演戏,谁也不能不买他的账。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当时双庆社的演员阵容非常整齐。头牌是尚小云,还有小翠花(于连泉)配演;须生演员同时有两个名角,谭小培、王又宸、马连良、谭富英、时慧宝都曾先后在双庆社长期演出;小生是朱素云;武生由他自己或他的弟弟俞赞庭担任;武旦有九阵风;花脸有裘桂仙、侯喜瑞。所以在当时能够上座不衰。其实尚小云虽挂头牌,可是每唱一场戏,俞振庭高兴给多少是多少,尚并不争竞。
二
斌庆社是个科班,专收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子前来学戏。
俞振庭所办的斌庆社,远在富连成科班以后,结束又较早,所以它的影响不如富连成,但在斌庆社存在的时候的确可以和富连成并驾齐驱。当时富连成在广和楼演唱,仅唱日戏,而斌庆社在广德楼出演,每天日夜两场。广和不卖女座,而广德则男女都可以接待,剧场也比广和宏敞,所以营业情况比富连成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旧社会的科班制度,非常残酷。小孩进科班,要立下字据:“生死勿论”。学员在学期间生活极苦,教员教戏,动不动用鞭子打。所以当时演员把科班这一段生活比之“六年大狱”。这些地方,斌庆社、富连成都是一样的。可是富连成还有个特殊,传统学生学戏期间,绝对不能和女人见面,连观众都没有女性。斌庆社就在俞振庭家里,这些小孩除了学戏、演戏,还要替俞忙些家务,如揉煤球之类繁琐笨重劳动就照例由学生担任。
富连成学员灌音后合影
斌庆社有一个制度和早年的富连成一样,准许外边学戏的小孩到斌庆搭班演唱。也和一般演员一样,演一场戏开一场戏份。在斌庆社演出正忙的时期,富连成已经不接搭班的小孩了,所以当时学戏的年轻人,都愿意搭入斌庆,可以有实践的机会,积累舞台经验。
有很多名演员早年都曾在斌庆搭过班,例如杨宝森、王文源(当时名叫五龄童)、刘宗杨(杨小楼的外孙、刘砚芳之子)、魏莲芳、李万春、蓝月春等人。斌庆社培养出来的演员有徐碧云(原来学武旦,出科后才改青衣花旦)、徐斌寿(小生)、王斌芬(须生)、朱斌仙(丑)、小奎官(丑)、计艳芬(花旦,艺名小桂花);而俞振庭的儿子俞步兰(青衣)、弟弟俞华庭(武生)、外甥孙毓堃(艺名小振庭,武生),也是在斌庆社出来的。
在斌庆社后期,李万春是主要演员。李万春的父亲名叫李永利,是演武二花的,功夫很好,久在外地演唱;李万春自小跟父亲学戏。李永利还教了一个徒弟蓝月春,专和李万春演对子戏。这两个小孩都是幼功,武功练得很好。
1921年前后,李永利带着这两个小孩来到北京,因为北京是京剧发源地,有名演员都聚集在北京,京剧演员必须在北京唱红,才能全国知名。李永利为了培养儿子,所以带来北京演戏。但他久在外省,北京城里两眼一抹黑,就托人介绍拜了俞振庭的门子。俞振庭知道李的艺术不错,再看两个小孩更是出色。李万春、蓝月春当时都只有10来岁,可是合演《夜战马超》、《神亭岭》、《狮子楼》等戏,起打十分紧凑,演戏也特别精神,俞振庭一看就很喜欢。于是李永利搭入了双庆,李万春、蓝月春就搭入斌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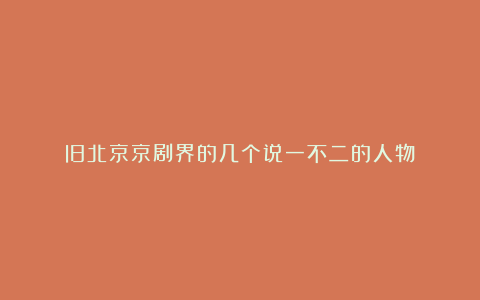
李万春进斌庆,带有配角、下手、场面,好几个人。俞振庭答应每天给开40块钱戏份。没想到,李万春一唱就唱红了。北京城里的观众都很欣赏李、蓝这两个小孩,岁数不大,而起打那么火炽。
李万春、蓝月春合影
李万春、蓝月春之《两将军》
当时正是北洋政府军阀政客腐化享受最甚的时代,这些阔人常约堂会戏。一约堂会,都愿意看李万春、蓝月春的戏。头一个月,两个小孩唱了54个堂会,俞振庭一文戏份也没开,认为全包在那40块钱之内了。李永利最初还算不出这个账来,以为一天40,等于一个月1200块钱的包银,也没争竞。俞又天天请他父子吃两益轩、致美楼等小馆,觉得挺受优待呢。唱过一个月才知道吃了大亏,向俞振庭提出要求,这才说好以后每唱一个堂会给100块钱,而那54个堂会都白唱了。
俞振庭一个人办了两个戏班,他的地盘就是广德楼。他和一般成班的人不同:别人成班,只问公私两面,应酬到了;而开个剧院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剧院要应付一切观众,其中三六九等不说,北京城里专有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到戏园中无事生非,这就更难对付了。俞振庭能够应付自如,不仅是因为他有办事能力,主要因为他和官面、商界都很有拉拢。在官面上,他和历任警察总监吴炳湘、薛之珩都有交情,侦组队的李达三、田德山和一区、二区的署长,都是他一块打牌的朋友。
当时的俞振庭简直成了戏剧界的把头,大堂会都由他承办,他不点头,谁也不用想在北京城里唱戏。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政治中心南迁,北京失去了过去畸形的繁荣,俞振庭也跟着没落下来了。
三
俞振庭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首先是双庆社的主要演员纷纷脱离,自己组班。
头一个就是尚小云。尚小云的琴师赵砚奎,是个很能干的人,戏剧界关系深。哥哥在小荣椿社科班管事,大舅子李玉安给余叔岩管事。于是尚小云就不叫他拉胡琴,专给自己管事。当时的名演员,都不愿意和前后台零碎事务打交道,每人都有一个管事的,等于自己的代表(如梅兰芳的管事是姚玉芙,杨小楼的管事是刘砚芳)。在哪里演戏,演什么戏,拿多少钱,都由管事负责交涉。赵砚奎本来对于后台的事情非常在行,又认识不少官面,当管事的确是把好手。他看尚小云在双庆社声誉很好,可是拿不着多少钱,就鼓动尚自己组班演唱。
从尚小云开头以后,马连良、谭富英、小翠花……都先后离开俞振庭,自己挑班,于是双庆社就垮了。接着斌庆社也因为李万春自己挑班,杨宝森、刘宗杨等先后脱离,也就垮了台了。
这些当管事的人都有一套本事,不但能够对外,而且主要是抱住这个演员,把老板的脾气摸透了,连哄带拍,老板什么也听他的,离开他不行了。一切大权自然就落在管事的手里。管事的大权在握,而且所有管事的都互相勾通,谁要得罪了一个管事的,就很难搭班演戏。
俞振庭的没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市面萧条,光靠北京这块地方,已经不能养这么多的演员了。有名的演员都得跑码头,主要是上海,其次是天津。演员到上海唱一个月戏,就够他在北京一年的生活了。于是北京的京剧界无形中就要受上海的操纵了。
北京京剧后台,归管事的把持,上海各地来北京邀角,也逃不过管事的这一关。这样就造成了经励科的黑暗势力。连俞振庭的外甥孙毓堃也不能不受他们的制。
孙毓堃原在俞振庭的双庆社演戏。他是俞的外甥,当然不买后台管事的账。他在扮戏时,管事的催他“马前”(快点),他一堵气,把脸洗了,重扮。在台上演出,下一出戏没扮好哪,管事的叫他“马后”(演慢一点),他偏赶快演完。管事的心里很不高兴,看在俞振庭的面子,谁也不敢惹他。
等到俞振庭垮台,孙要搭班演戏了。经励科的人彼此赌咒:“谁约他唱戏,如何如何。”这一来,孙一直搭不上好班。经励科宁可约那些艺术远不如他的,也不约他。孙很生气,后来就和他女婿宋德珠合演,自己成了一个班。可是这样他也逃不过经励科的手,演出结果,不够开支,场场赔钱。有时他大卖力气,唱重头戏:《铁笼山》、《艳阳楼》,唱完之后,浑身大汗。台底下很欢迎,上座不坏,可是还是一文见不着。经励科总说不够,查细账也查不出来。原因就是经励科有两本账,他只看了“明卡子”,哪里能摸清细底呢?
经励科虽坏,可是谁也坏不过佟瑞三去。大家把他恨透了,给他起个外号,叫作“戏霸天”。佟瑞三,就是前面所说赵砚奎的徒弟。
四
佟瑞三原来是唱小花脸的,因为艺术平常,就拜赵砚奎为师,入了经励科。他和上海、天津、汉口、济南、南昌、西安……各个码头都挂上了钩,手底下用了一群人。过去的经励科都是名演员管事的,佟却并不单独给哪个演员管事,可是马连良、谭富英、程砚秋、荀慧生……这些剧团的管事底包,都得走他的门路,好像他包下了一样。
他常洋洋得意地说:“我不傍角,你说马三爷(马连良)、程四爷(程砚秋),我还佟三爷呢。”因为他这种气焰逼人,所以才有了“戏霸天”的绰号。
佟瑞三能够在戏剧界气焰万丈,是在北京沦陷以后。主要是他和日寇方面有勾结。
有个拉胡琴的,姓赵,这天晚上到长安戏院演出,他去得较晚一点,戏已经开演了。恰好这天有日本大官看戏,门口有日本兵把门。赵不敢冒然进去,日本兵看见赵探头探脑,以为形迹可疑,过去给他几个耳光,踢了一脚,不让他进去。被票房看见,进去把佟瑞三找出来一说。佟赶紧进去,找着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立刻向门口的日本兵说明,日本兵知道是误会了,居然给赵道了个款。于是前后台都知道了,还是佟瑞三威风大,能叫日本人道歉。
在敌伪时期,佟瑞三凭借日本人势力,又和汉奸有勾结,他还利用各种流氓帮会势力,所以才能独霸北京京剧界,并和各个码头流氓组织拉上关系。轮船、铁路、关卡,对他都有个面子。他就自己吹牛:“凭我一个人,分文不带,走遍全中国,到哪儿哪儿得好吃好喝款待我。”
当时盛行跑单帮,带私货,戏剧界的人也常利用到外地演戏机会,做点走私买卖。其实都是佟瑞三和他的手下干的。因为他和水陆码头脚行都有勾结。鸦片、白面各种毒品随便带。
当时演员的出路,还是指着跑上海演戏,而上海戏院,都和佟有关系。例如上海的董朝斌(更新舞台老板,混血儿)和佟是把兄弟,董来北京约人全凭佟一句话。
上海如此,北京更是他说了算了。谁要得罪了他,就别想在北京唱戏。须生演员迟世恭在富连成出科以后,声誉很好。他自己订了一张价目表,演出《四郎探母》20块,《失空斩》15块,《捉放曹》10块……邀角的去找他,他就把价目表拿出来,有点言不二价的意思。邀角的都是佟的手下,向佟一报告,佟把眼一蹬说:“放他妈的屁,敢跟我讲价,永远不许约他。”于是迟世恭好几年唱不着戏,只好到外码头去搭班了。
迟世恭
花脸演员苏连汉功夫很硬,主演演员都很赞成他,愿意叫他配戏。只是因为不甘受佟瑞三的挟制,佟就向经励科说:“不许约他。”苏在家闲了两年,穷得吃尽当光,最后托了很多人情,才搭入了李万春的剧团。
前面说过,佟瑞三手下有很多人。这些人平时在他家里,听他驱使,给他干活。到有戏的时候,就跟他上园子。演员演出一场,该给多少,当然凭佟瑞三随便决定了。他还改变了过去的规矩,当天不开份儿,第二天派人送去。送,当然不能白送,还得给点车钱。积少成多,这些人光是车钱,每天就能挣个三四块。这些人在佟手下,不挣工资,全凭这些收入来维持。他们家里有什么红、白事,也由佟出头代办。
佟瑞三不但从剧团的“暗卡子”里弄钱,有时还在明处拿一份儿。如他在荀慧生的剧团里,拿的戏份儿和二牌老生一样多。到后来甚至比主演还拿得多。
外地戏院来北京邀角,总是先给佟瑞三一个电报。到时候,他就派手下人到车站去接,旅馆也准备好了。邀角的来到北京,住旅馆、逛窑子,吃喝玩乐一切费用都由佟给开支。这些人可以不用自己掏腰包,白吃白喝,自然非常高兴。表面看来,佟的手笔十分阔绰,其实他不但没有花一文钱,还从中赚了不少钱呢。因为邀角的来到北京,除了主演的演员以外,跟其他演员根本见不着面,而主演演员照例自己不谈公事的。所以包银多少,如何开销,完全由佟支配。他花了许多钱应酬邀角的,其实这笔钱全是演员们间接负担的。
由于佟对各地都有拉拢,所以他们有句常说的话,叫作“闲话一句”(上海话,意思是一言为定)。有一次,天津有个戏院约角,约了李洪春等人。这个邀角的,初出茅庐,没有买佟瑞三的账,也没有给佟什么好处。于是佟到天津,通知李洪春立刻把全班人马带回北京。戏院一看,慌了。这才知道是佟捣鬼,准备请客送礼,仍留李再唱几天。这个老板去找佟,遇见欧阳昭,欧阳去见佟一说,佟说:“你就说,我已经回北京了。”这天晚上,佟在南市听落子,被戏院里的人知道了,以为是欧阳昭在耍什么花样,就派人到落子馆找欧阳,把欧阳带到一个小胡同里,按在地下饱打一顿。把欧阳打得鼻青脸肿,爬着上楼,向佟说:“这都是你照顾我的。”佟一气,第二天早晨赶回北京,在梨园公会开会。那个戏院老板慌了,赶紧请出有头有脸的人来说合,点蜡烛,泡和气汤,这才一天云雾散。而不打不成相识,佟瑞三和这个戏院老板从此又成了自家人了。
佟瑞三和《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甚好,和那些写稿“捧角”的无聊文人,都有勾结。如果一个女演员走了佟的门路,不仅可以上台演出,而且在演出之前,就可以将相片登在画报的封面,并在画报里登上许多肉麻的捧角文章,把这个女演员说得如何“色艺超群”。在演出的那一天,佟瑞三又把他的喽罗分别安置在剧场的楼上楼下,前后左右,一出场立刻有人叫“碰头好”,随后是“彩声不绝”。这样一来,就显得声势很不寻常了。于是打泡三天,就给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佟瑞三还和广播电台有联络,当时广播电台多数是私营的,经常要请演员放送戏曲,他们照例通过佟瑞三来约人。于是哪个女演员能够在电台放送,这个命运也掌握在佟的手里。一个女演员由于佟的捧场,有画报的宣传,又在戏园里演出几次,再加上经常在广播节目上出现,于是这个女演员就算在北京唱“红”了。然后才有机会,由佟介绍,到天津、上海“淘金”。
由于佟瑞三有这样左右一个女演员命运的能力,他就利用他的地位,侮辱女演员。
他侮辱过很多女演员,而受侮辱的女演员就更逃不出他的魔掌。不仅演戏的收入大部入了他的腰包,平时还要像奴婢一样伺候他。解放以后,这个恶棍曾经遭到一些女演员的控诉,经人民法院将他逮捕治罪。据他坦白,他曾侮辱过50几个女演员。但据知道内幕的人说,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