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有点类似旧文重发,两年前曾写过有关夏宗寺的文字。但我相信经过两年的沉淀,再次提笔(敲击键盘)成文,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对自己亦是。
旧文重发的缘起是看北京台的大型专题片《紫荆城》,说到故乡青海的瞿昙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隆国殿是重檐庑殿顶——这是古建最高等级啊。一时间心情兴奋起来。瞿昙寺是去过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是对于那个年纪的我,虽然说起来已经皈依,对古建等业已感兴趣,但毕竟年少,还没有经过任何系统学习,看古建不知道从何处着眼。那个年代照相机还是奢侈品,只记得在瞿昙寺门外,同行中负责照片的人给拍过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还得等整卷交卷拍完了,相机主人才拿去冲洗,两三个月后才得到一张成品照片——如今早不知道遗失在何处。后来我还买过一本瞿昙寺的画册(内含壁画照片)。
也就想到前年2023年夏秋之际的故乡行,不到一周时间去了玛什藏(海东市互助县,汉文名白马寺,后弘期下路佛法之肇始寺院之一,另一为丹斗寺)、夏宗寺(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隆务大寺(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和塔尔寺(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街道),都是藏传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寺院。故乡,经得起一次又一次思念、一次又一次书写。就再次整理被两年时光重新冲洗,再次显影的照片,和大家一起来看岁月还会揭晓什么样的谜底给我们。
去过很多次夏宗寺。
第一次还记得,是小学五年级。我们当年是没有六年的,五年级就是毕业班。因为这个原因,班主任决定来一次远足郊游,权当是同学一场,大家分别际的一次团聚和告别。最后决定去峡群林场(夏宗寺所在地)。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冒了很大险。记得当时是通过班上某位同学家长的关系联系了一辆大轿车,学校出面道谢。后来班主任老师说起“招待”司机师傅的费用,颇有微词,说花了三十多元。
我们自然只顾着兴奋。只记得从学校出发,经过一两小时后,车拐进了一条土路时,我们跟鲁迅先生从闰土那儿得知西瓜原来不长树上一样惊奇:原来还有这样的路。不光要停靠在路边和对面驶来的车小心翼翼地错车,每次过桥,同学们都要下来。所谓桥,就是用用树桩横竖两层搭建而成。年幼的我们都替司机叔叔捏把汗。一路上这样那样的险情不断,而且几乎所有的女生全都晕车呕吐,一半的男生也是同样症状。我们早就没有了兴奋劲儿,霜打的茄子样耷拉着头。等终于行驶到峡群林场,才开始第二轮兴奋——我们自我怀疑,货真价实的怀疑:这还是青海吗?青海的山上不长草,何况这满目青翠的松柏。这是林场嘛,自然有森林。班主任老师言简意赅地回答。不过我们的疑虑依旧存在,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来,我们在班主任老师的指挥下,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登山,抵达一个悬崖峭壁下方,一处平坦的地方开始野炊(现今夏宗寺大殿所在地)。班主任老师应该是旧地重游,他指给我们看悬崖上依稀可辨的建筑遗迹和一间完全用木板搭建的小屋说:“这以前是个很大的寺院,就叫’峡群寺’。”峡群寺是以讹传讹,其实就是夏宗寺,被冠以所在林场之名。我们看着那些遗迹,再看看几乎算是无路的路,舌头根都快吐出来了。后来不知是哪位同学问到,小木屋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阿卡(僧人之意,属于安多藏语音译)住,守寺的。
像是为了回应班主任老师的回答,说话间,木屋里走出一位僧衣根本看不出颜色的阿卡,身形一闪又回到了屋内。那吱呀作响的开关门声提醒我们刚才看到的不是幻觉,而是真实一幕。
后来,班主任老师和司机叔叔以及另外一位成年人(记不清他的身份了)一起登山,说要去木屋和遗迹所在悬崖峭壁最高处。他们态度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几个男生跟随上山的要求。班主任老师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几个点心包(就是那个年代用麻纸包住,再用麻纸挫搓成的线捆住的点心包裹,国营商店里买的;看来,他早有准备),开始上山。
我们眼看着三个大人进了木屋,不大一会儿又从另一端出来,继续朝山顶进发,然后就是抵达山顶,他们蹲在那儿指点江山,样子并不伟岸,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想到了孙大圣。不过仍然是羡煞了我们。若不是作为班干部的我“肩负”不许同学上山的职责,我估计最起码会上到小木屋里,近距离看看阿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一个人在这样的荒野中,是如何一种存在。
这就是佛缘吧?总之自幼就对有关的一切有着强烈浓厚的兴趣。后来还未等班主任老师他们下山,那位阿卡先下山了。他提着一把壶,径自走到班主任老师他们三人的摊点,给他们的杯子里续上了茶。是青海熬茶,除了我们十分熟悉的茯茶味外,还有我在当年并不喜欢的桔梗味。阿卡许续完茶后把壶留了下来,然后朝另一侧的山道走去。他经过我身边时,伸出手在我头顶轻轻拍了几下,微笑着走开。
等我明白这是加持,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奇怪:他认识你呀?
不认识啊!不认识怎么会拍你?我也不知道啊……
那是一位五十多岁(我此时年纪)的阿卡。多年后,当我第一次见到照片上弘一法师清瘦的面庞,记忆深处这位老阿卡的模糊印象又变得清晰起来:他和弘一法师有几分相像,或者说神似。那件看不出颜色的僧衣,实际上就是极为普通的绛红,经年累月的尘埃落在上面,看上去发暗。
第二次去,是六年之后的高三。那时的高考生没现在这么辛苦,是校长亲自带队。我还记得因为是高三,所以不参赛校运动会,但参与;我们是护旗方阵,统一着装。我们去郊游的时候就还穿着护旗方阵的统一运动服,仪式感十足。我们选择就餐的地点是峡谷,而非六年前的那处平台。旧地重游的我自然是向导,领着几个同学去朝夏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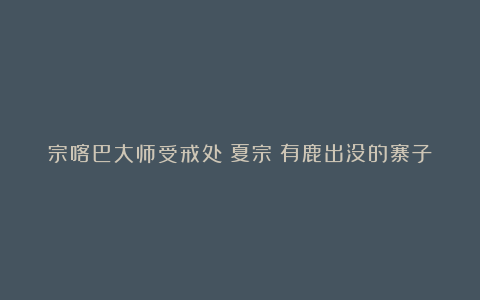
夏宗寺已然重修了大殿,但也就只有一个大殿,别无他物。半山处的小木屋不见了。大殿里有三四位年轻的阿卡,对我们很友善。我特意问那位老阿卡是否还在寺内?几位年轻阿卡显得很茫然,仿佛不曾有过这样一位前辈存在过,后来他们含糊地回答说应该是回到塔尔寺了。这一回答让我知道夏宗寺是塔尔寺的属寺。
当下的年轻一代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我们,想获取书本以外的知识,有多难。我们的知识贮备就是这样一点一滴,通过只字片语慢慢积攒起来的。除了自身因果,还有时代因素,获取知识的渠道有限。而且,这类知识还属于与学习无关,甚至很敏感的范畴,学校和家长最起码不提倡。
我还记得当我购买了第一本属于我自己的佛教典籍《布顿佛教史》一书时,父亲脸上的古怪神情。
再后来去的次数就有点记不清了。其中有一次是当媒体人的时段,女票同行,虽然不记得,但一定有过“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两情长久”之类的祈愿。每次去都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夏宗寺日渐规模,直到2023年最近这次。不过夏宗寺仍未完全恢复之前的规模,我当年见过寺内保留的一张被毁之前的照片,对比照片可知道之前的规模(照片所显示出来的部分)最起来是目前的一倍。
前年的夏宗寺之旅,也是迄今唯有过的一次登山(登顶)经历。之前的几次都因为处于重修工程期,为安全起见,上山的道路封闭,禁止游客踏足。当我终于踏上山路,来到位于半山处的宗喀巴殿,每挪动一步都会想:“这里,杰仁波切(故乡人对宗喀巴大师的特有尊称)当年有没有涉足过?”
夏宗寺是宗喀巴大师受戒的地方。当时年仅三岁的洛桑扎巴被父亲鲁本格领着,来到夏宗寺;在奉召前往元大都,在夏宗寺驻足的噶玛噶举派四世活佛若佩多杰处受戒。狭窄而崎岖山路,年幼的大师是被父亲牵着手走过,还是在父亲宽厚结实的背上陪着父亲一起路过?
现今宗喀巴殿所在的位置,是否就是当年若佩多杰大师驻足休憩之处?一切细节都是如此令人着迷……
夏宗寺,藏语为夏哇日宗,意为有鹿出没的地方。如今是否还有野鹿的踪影不得而知。而在四川阿坝州阿坝县,依旧有鹿可寻:2020年秋,三位方外之友特意带我去看一只被年幼僧人救护的野鹿。
野鹿被救护时还很小,是头小鹿,小师父尚可以双手抱起。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位年纪很小的师父和一头小鹿睡在一起,小师父整理床铺时,小鹿就乖乖等着。有没有可能就是同一只小鹿呢?可能性很小,毕竟这样的护生行为在藏地不胜枚举。
几年过去,小鹿已经长大,就在护法殿所在的院坝草地上放养。时不时都会有香客上前摸一摸他的头顶。我也大着胆子和它亲近了一把。
(未完待续)
一方伽蓝
十方常住
关于作者|舒放,力求避免油腻的中年男子。流浪各地,但定型于高大陆青海。写诗多年,一直坚持着,哪怕诗歌从大众变成小众乃至现在的旁门,喜欢不减,且欢喜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