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江汉平原毛家场的通顺河边,河南岸有集市。塆子依堤而建,房屋前后栽有杨柳,树上鹊窝很多。河水清澈,鱼虾嬉戏。全塆人吃河水,故称“母亲河”。所以,偏僻村庄的姑娘,都爱请媒婆去说吃河(活)水的婆家。
我家老屋是在“土改”时,分得的“翻身屋”,是志愿军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地主的“翻身屋”是三间布瓦房、全杉木,铺楼板,七柱九檩带拖院,隔墙嵌有鼓皮。与另外一名志愿军伯伯同住,公堂屋,共厨房,合用一个矸檐头,房间各开门。
一九六九年,那位志愿军伯伯折走了一半,搬到了上塆。父母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在拆走的原址又加盖上了。虽说是薄方砖的“挂墙”,柳树柱头木门槛,土坯“京墙”刷石灰。在我的心目中,也算是一个砖瓦三间屋。
记得那年新添的一间半屋,在落成时,亲朋好友来恭贺时,由于当年农村市场物质的困乏,买什么都需要票证,来客也只是喝了几口油盐豌豆酒,每人吃了二碗胡萝卜饭,就算是请了“屋酒”。母亲娘家给我们送来了方桌、衣柜,还有一乘用枣树打的独轮车。
独轮车是一种原始的运输工具,诸葛亮发明,农人生产、生活少不了它。我刚学推独轮车时,总是翻车。父亲告诉我:其实,“推车无巧,只要屁股扭得好”。
小时候,对老屋的印象,不曾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除了父母、兄妹和塆里的小伙伴,就是每天吃饭、做作业、睡觉的三间青砖瓦房。那时候,我从来就不曾离开过塆子,放牛、上学、打猪菜、捡柴火、打鼓泅、捉知了……始终是围绕着塆子在转,只知道前塆和后塆,禾场和队屋,菜园和庄稼地。还有五月的槐花,六月的荷花,七月的菱果。一年看一场露天电影,如年成好,过年还会看几场难得的皮影戏、花鼓子,根本不知道村子里的那条路,会通向哪里。
后塆的王三妈与母亲娘家是一个地方的人,她们是结拜的“干姊妹”,我叫她姨妈。有一天,姨妈提来在她家桃树上摘下的十几个“五月桃”,抱走了我家喂的大公鸡。毛桃换公鸡,明摆着是吃亏,我不肯,与母亲吵了起来。母亲回答我说:“姨妈家要孵小鸡,没有公鸡,过几天就还的我们。”我更是想不通了,孵小鸡是抱鸡母的事,怎么却抱走了我家的大公鸡?
放牛场上,村老告诉我:小鸡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的,无论是自然孵化、还是人工孵化,都需要先受精,才能长成鸡。受精卵存在于蛋黄中,所以小鸡的主体是蛋黄,蛋清主要起保护作用。没有受精的鸡蛋是不能孵化的,否则会孵成“寡鸡蛋”,只有受精的鸡蛋才会孵化雏鸡。
后来,看到母亲在给抱鸡母上窝时,总是检查瓢里的鸡蛋是不是受过精的蛋。其做法是在罩子灯下看蛋里是否有黑点,有黑点的就是可以孵化小鸡的蛋。过了几天,姨妈果然归还了我家的大公鸡,又端来了半柳簸子的甜大枣。
通过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成双成对的道理。
稍稍长大一点,我离开塆子、离开了老屋,去了七、八里外的乡上读中学,走到学校得一个多小时,天朦朦亮就得往学校赶,中午吃带的饭菜或是一个火烧粑,上完晚自习还得家人提马灯去接。为节省时间,只得周一至周五在学校住宿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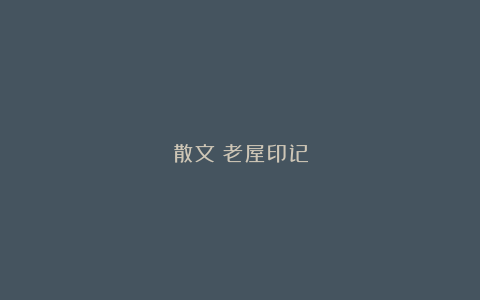
刚开始当住读生的日子,每当晚上入睡之后,眼前浮现出父母劳作的样子,兄弟姐妹的逗闹声,早晨大公鸡“喔喔”的叫声,还有房前屋后鸟雀的欢唱,烟囱那袅袅的炊烟……到了星期六的下午,我背着那个空罐头菜瓶子,沿着通顺河堤边的小路,归心似箭地跑回家的时候,见到母亲靠着门框,笑盈盈地迎接着我,此刻,那种说不出的感动,至今不曾淡忘,这也许是我对“家”最初的认知。
我弟兄两人,弟弟小我七岁,他是我们姊妹中最小的一个,正在读小学。每次星期天回家,父亲总是唠叨着我和弟弟:要好好读书,做老实人,长大才说得到姑娘。如祖坟冒青烟,你们都弟兄俩考出去了,这老屋就卖掉,卖的钱供你们去上中专,上大学;考不出去,你们一人一半,跟你们“娶亲完辈”后,各自单立门户地过日子,我和你们的姆妈在河坡上去搭个棚子,在一边过,生老病死不要你们管。因为父亲有几个钱的志愿军补贴,虽不多,但每月买盐巴是足够的。
恢复高考后,我和弟弟都参加过中考和高考,可“一颗胡椒籽都没有辣”,只好住老屋,种责任田。其实,我和弟弟在老屋里也没住上几年,改革开放后,弟兄俩走南闯北外出打工,糊里糊涂赚了几个钱,买了商品房后,养儿育女,就各自在大城市里定居了。前些年,有父母在,我们弟兄俩逢年过节都按时回家,在老屋坐坐,到老屋前后转转,邻居家走走,亲戚家做好事去喝酒。特别是每年的除夕晚上,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到坟墓给祖宗去上灯。
老家上灯习俗,代代传承,极具传统性和地方特色。土话里的“灯”和“丁”读音相似,所以,上灯意味着“添丁”发财。再则,过年活着的儿孙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团聚了,正好借机去看看已经“睡去”的祖先,一者告诉他们,后辈们很平安,并且没有忘记他们。让他们看看,他们传下的这一血脉香火有多旺,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全赖祖先的保佑。所以,老家每年的大年三十,正月十五的晚上,村里坟墓处都是灯笼,恰似银河落人间,遍地星光闪烁。
我们弟兄俩外出打工后,老屋一直是父母在开门关门、在守护。“人要衣衬,屋要人衬”,有父母的打理,老屋也没有半丝的蒙尘,瓦缝里也没有树叶。所以,老屋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尽管那四季的风吹雨打,一年又一年,但还是安然地挺立着。我和弟弟也没有回去给老屋检过一个漏子,换过一片的布瓦,挑过一箢箕的土去帮台坡。
不几年,父母相继过世后,老屋只好用家里的一把旧锁锁了起来。
一年的清明,我回了一趟老家,大门上缠满了蜘蛛丝,归来的燕子在屋外廊檐筑巢,矸檐头青苔覆盖,房前屋后杂草、野蒿遍地,储藏红苕的窖里积满了水。树上的喜鹊窝还在,洋槐开花,蜜蜂采蜜,丈高的竹子一节复一节生长着。老屋外的蓝天白云飘过,家里摆设的杂物依旧,油灯、水桶和土灶还在,四条长板凳还挂在老屋的串板上。可就是再也见不到在老屋转悠的二老了!半生回首是感动,一股辛酸入喉来!
人有情,屋有感。昔日的塆子五十多户,三百多人,还有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丹江水库的移民。当我走进塆子,如今只见几位老人拄着拐杖,缓步走到我们身旁,喊我乳名,问这问那。和他们一样慈祥的爹爹婆婆们,有的也相继去世了,知青、干校都返城了,丹江移民又搬回了,塆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小也没有了,孩子们都到了镇里、市里去念书,寒暑假就往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去开展“亲子活动”。就连塆子里,没有主人喂养的,但不愿离开的,几条忠诚的狗,看见我这个“生人”的到来,也是安静的,不住地摇着尾巴“欢迎”着我。
近看我家老屋,已在岁月中成了雕塑。撬开门锁,走进老屋,抬头看去,老屋托瓦的床橼已腐朽,布瓦散落一地,像是开了一扇天窗,留下仅存几根柱头、横樑和门槛。多年的风暴雨侵,尽管伤痕累累,千疮百孔,饱经沧桑,但它仍旧没有倒下,全靠着列架的支撑。
前年冬天,弟弟打来电话,他听村干部说老屋被暴雪压塌了。按乡俗,雪把房屋压塌,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于是我们就没有及时回家去收拾,又不能变现,随它去罢。
人是有根的,老屋毕竟是我的根,往后的日子,于是我关注起老屋来。那一场暴雪过后,我叫村里当妇女主任的侄媳妇,发来老屋的视频,看完,心情就像隐匿沧海的沉船,我哭了!老屋有父母的身影、我童年时光,更是我襁褓之地,顿时,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愧疚和忧伤的心情,犹如那场暴雪,久久挥之不去。于是,我对侄媳妇说:叫她把哪些烂破瓦清理后,收拾起来,也许你们以后会用到。
我家老屋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三间的老屋场,前后台基有个篮球场大。侄媳妇他们除去瓦砾、瓷碗片当菜园,栽些洋姜,种些丝瓜、南瓜等藤蔓植物,吃不完就送人。
去年,侄媳妇打来电话,说国家将闲置的土地重新归集整治,重新利用,应收尽收。我家的老屋台基,就在轰隆隆的挖掘机声中,成了村里新农村建设的健身广场,极大地改善村民的休闲环境。
吾心安处是老屋。梦中的老屋,它像门前那条多年为伴的通顺河,流淌着一股汨汨滔滔、打着旋涡的忧郁,流淌着社会变迁的轨迹,也流淌着我的乡音、乡情和乡愁。(9月14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