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理解为一种学习哲学的进路,即“哲学-实践-真理”。
“他的演讲是某种形式的哲学宣传,能够太过容易地被用来忽视更全面和有趣的哲学观点,后者是科耶夫提出的关于圣者和真理的本性的,即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创造物,而是更需要行动才能变成现实。正像科耶夫在其战后的写作提纲’黑格尔、马克思和基督教’中所提出的,黑格尔哲学是唯一尚未被驳倒的哲学,因为他的哲学计划的本性恰好在于它是一种试图付诸实践的计划。这里的口号——可以肯定是一种相当陌生的——是一个人必须行动或劳动以创造真理;哲学的任务是真理的工作,去产生真理。”
这样的观念或许超越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他所强调的或许是“认识”必将逻辑地导致“实践”的诉求,只有“实践”才能令我们接近或产生“真理”。因此科耶夫不是借助于黑格尔“发现智慧”,就像它早已经在那里一样,而是“带来智慧”。
“智慧因此是哲学家的一种言语上的创造,一种哲学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他的目的看起来跟那些典型的与评注或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献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并不相同。科耶夫的评注带有公开的政治目的:创造一种条件来建立一种政治现实性,它能够让哲学的努力完成在圣者的形象之中。因此,科耶夫不是向我们展示一种正确的解读,展示在文本中有些什么;毋宁说,他在阅读原文时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将其理解为一种指引,指引着一种完善的计划,该计划会被那些愿意倾听并追随的人执行,从而实现向真理的’转变’。”
“哲学家是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相应地,也是唯一有可能接受智慧挑战的人,智慧在此被理解为彻底的自我意识。因此,如科耶夫所注意到的那样,哲学家就是一个寻求对他所涉足其中的所有行动都给予全面说明的人,一个寻求在这种意义上全知的、满足的,并且道德上完善的人。”
科耶夫说:“人只在他进行思考的范围内才是人;他的思想只在它并不依赖于是他在思考这一事实的范围内才是思想。”因此哲学家是最配的上人的称谓的人,他们就像蛰伏在苹果树下的十七年蝉,在阴暗、潮湿、寒冷的地下侦测、感知、寻求思想的破土而出的时刻,并不在乎生命的长度是一周还是两周,因为思想已经带来了永恒。
但科耶夫一定与海德格尔对尼采或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态度不同,后者将哲学视为隐微的、封闭的产物,科耶夫则在公开的、实践的角度宣告他的哲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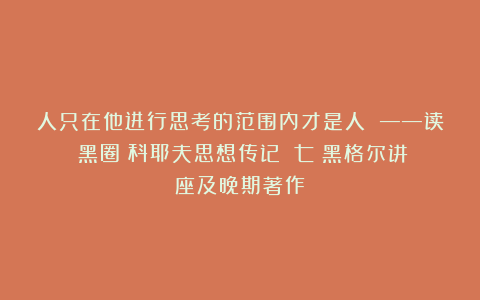
“海德格尔以一种高度自我指涉的方式指出,思想家会隐藏自己的真正思想,仅仅允许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给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一点亮光。海德格尔认为,一个思想家的真正思想应该保留给少数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把握住那种思想的人,这一观点对科耶夫的朋友施特劳斯来说似乎也很重要。所谓的施特劳斯学派很有名的一点是公开赞成一种’封闭的’或’隐秘的’学说,这一反讽只有施特劳斯的个别信徒直接表达过。对施特劳斯来说,每一个配得上哲学家称号的人,都有一套隐秘的或者只有内行才懂的学说。隐藏这一学说的理由在于它对于城邦或社会来说具有内在的危险性,因为哲学家是一个思考超越了城邦事务的人。”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在我看来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除非经过《存在与时间》《尼采》和尼采著作的思想洗礼之后。至于施特劳斯,我们至少要承认,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理想国》等对话中都仿佛在寻找少数可以真正理解自己的人,正如查拉图斯特拉也在寻找类似的人,这一事实仿佛在暗示:确实存在隐秘的学说,大多数人一是不屑于了解(他们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他们忙于操劳),二是也没有能力理解;但对于少数人而言,既有能力也有欲望(甚而至于,如果没有能力,他们会意识到要培养这种能力),他们就像格劳孔一样,就算苏格拉底没有提供无懈可击的论证,就算他竟然编出一个灵魂中转站的寓言,也宁愿相信他。
“科耶夫很难说乐见此种哲学幻想,⋯⋯科耶夫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摆脱了人们在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那里发现的哲学暗语。科耶夫打趣二者说,与世隔绝的哲学家更像一个疯子而不是对城邦的威胁,更荒谬而不是更危险。真正危险的哲学家是一个鼓吹行动的人,而且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是公开的教导方式,以吸引不仅仅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对科耶夫来说,所有针对少数人的教导都带有标志性的排外性缺陷。相反,哲学家会贴近大众,寻求他的教导的普遍化,并认为这是其价值的唯一体现。一种无法获得大众——如果不是全体——支持的教导肯定是荒唐的,某种私下的教导喜欢自封高级的或只适于少数人的,而拒绝承认无法在成为大众的教导上取得成功,这样的教导所标示的,除了其根本性的无能之外,没有更具戏剧性的东西了。”
如果说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尼采、施特劳斯们对哲学对象的选择有清醒的认识,科耶夫想要做的就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在启蒙与行动的意味上,他要比他们更为勇敢,但或许表象就是假象,因为苏格拉底早说过自己甘愿做一只牛虻,一条电鳗。
科耶夫的勇气或反讽气质在对他的一次采访中表露无遗,他说自己“乐于嘲笑哲学家”,“声称官僚制度是一种更高贵的游戏”。如果不是讽刺,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科耶夫求助于官僚制度作为一种带来新社会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的终结。”或多或少,这可以成为他在战后于法国政府内任职数十年的一个哲学解释。
评价:4.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