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探讨恩斯特·潘诺夫斯基(Ernst Panofsky)图像学方法的理论建构,聚焦其三阶段阐释模型——前图像志阶段、图像志阶段与图像学阶段——的内在逻辑、方法论特征及其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应用价值。通过梳理潘诺夫斯基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渊源,分析各阶段的具体任务、操作方式与认知目标,本文揭示其方法论如何实现从形式感知到文化阐释的递进式理解。文章进一步论证三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图像学阶段作为“综合阐释”的核心地位,指出其对艺术作品深层意义的揭示依赖于前两个阶段的严谨积累。最后,本文评价该方法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重申图像学作为人文主义阐释范式的持久价值。研究旨在深化对潘诺夫斯基理论体系的理解,为艺术史方法论提供系统性反思。
关键词: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学阐释;艺术史方法论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建立起自身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在这一进程中,德裔美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潘诺夫斯基(Ernst Panofsky, 1892–1968)以其系统化的图像学(Iconology)方法论,深刻影响了现代艺术史的研究路径。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从传统的图像志(Iconography)中提升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阐释方法,其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三阶段阐释模型:
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与图像学阐释(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这一模型不仅为艺术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清晰的操作路径,更在哲学层面回应了“如何理解艺术意义”的根本问题。本文旨在系统解析潘诺夫斯基图像学方法的三重结构,阐明其内在逻辑、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并评估其在当代学术语境下的意义与挑战。
二、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思想渊源与理论背景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学术传统与现代哲学思潮的交汇之中。其思想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德国艺术史学派、新康德主义哲学以及现象学与符号学思想。
首先,潘诺夫斯基继承并发展了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尤其是阿洛伊斯·李格尔与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对艺术“内在意义”(innerer Bedeutung)的关注。李格尔强调艺术形式的自主性与历史发展逻辑,而施洛塞尔则注重艺术术语与图像传统的语义研究,这些都为潘诺夫斯基区分“形式”与“意义”提供了基础。
其次,新康德主义哲学,特别是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区分,深刻影响了潘诺夫斯基的方法论建构。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的任务不是归纳普遍规律,而是理解个别现象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意义。潘诺夫斯基据此提出,艺术史的目标不是描述风格演变,而是“理解”作品所承载的文化精神(Geist)。
最后,现象学与符号学为潘诺夫斯基提供了分析“意义”结构的工具。他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性”概念,强调艺术作品是意识对世界的表达;同时吸收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将艺术视为人类符号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 1939)与《意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1955)等著作中,潘诺夫斯基系统阐述了图像学作为“文化征候学”(symptomatic significance)的功能,即通过艺术作品揭示其所处时代的世界观与精神结构。
三、图像学三阶段阐释模型的结构与内涵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以三阶段递进模型为核心,每一阶段对应不同的认知层次与研究任务,共同构成一个闭环的阐释体系。
(一)前图像志阶段:形式感知与事实性描述
前图像志阶段(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是图像学阐释的起点,其任务是对艺术作品进行“事实性”(factual)或“自然意义”(primary or natural subject matter)的描述。这一阶段关注的是观者对视觉形式的直接感知,包括线条、色彩、构图、空间关系、人体姿态、表情、服饰、器物等可识别的视觉元素。
潘诺夫斯基强调,此阶段要求研究者具备“正常人”的知觉能力,即在不依赖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客观描述画面中“出现了什么”。例如,面对一幅文艺复兴绘画,前图像志描述可能包括:“画面中央站立一位女性,身着蓝色长袍,怀抱一名婴儿;背景为室内空间,有拱门与柱子;左侧有一位老年男性手持书卷,面露关切。”这一描述不涉及人物身份或故事内容,仅记录视觉事实。
该阶段的关键在于区分“感知”(perception)与“识别”(recognition)。前者是生理性的视觉接收,后者则已涉及文化知识的介入。潘诺夫斯基指出,前图像志描述必须避免“意义预设”,即不能将后一阶段的知识投射到当前阶段。例如,不能将“蓝色长袍”直接描述为“圣母的象征”,因为这已属于图像志层面的解释。
(二)图像志阶段:主题识别与传统追溯
图像志阶段(Iconographical Analysis)是在前图像志描述的基础上,运用文化、历史与文献知识,识别作品中的“主题”(subject matter)与“故事”(narrative)。此阶段的目标是确定画面中人物、事件、象征物的具体身份及其所属的传统系统。
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志定义为“对艺术作品主题内容的研究”,其核心是建立“图像志文献”(iconographic literature)的对应关系。研究者需借助文学、宗教、神话、历史文献等资料,将视觉元素转化为可理解的文化符号。例如,前一阶段描述的“蓝色长袍女性怀抱婴儿”在此阶段可识别为“圣母玛利亚与耶稣基督”,而“手持书卷的老年男性”可能是“圣约瑟夫”。进一步,若画面中出现百合花、鸽子或光环,则可确认其属于基督教圣像传统中的“圣母领报”或“圣家族”主题。
图像志分析依赖于三个子步骤:1)识别主题(ident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2)追溯图像传统(tracing the history of types);3)分析构图模式(analysis of composition and style in relation to meaning)。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志研究》中系统整理了西方艺术中常见的图像母题(motifs)与类型(types),如“三博士来朝”“最后的审判”“维纳斯的诞生”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工具性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图像志阶段仍属于“外在意义”(secondary or conventional subject matter)的范畴,其解释具有相对确定性,主要依赖于文献证据与传统惯例,而非深层文化阐释。
(三)图像学阶段:综合阐释与文化意义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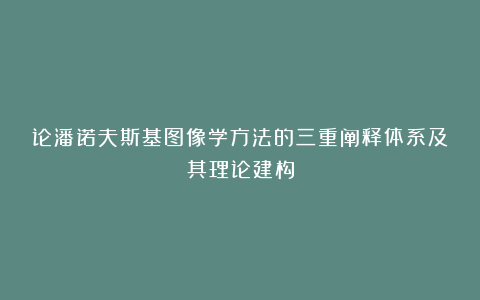
图像学阶段(Iconological Interpretation)是三阶段模型的最高层次,其任务是揭示艺术作品的“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或“象征意义”(symbolic meaning)。潘诺夫斯基指出,此阶段的目标是“理解一件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仰之征候的表现”(Panofsky, 1955, p. 45)。
图像学阐释超越了对主题的识别,转而追问:为何这一主题在此时此地以这种方式被表现?其背后反映了何种世界观、价值观念或精神结构?例如,对一幅15世纪尼德兰的《圣母子》进行图像学分析,不仅要确认其主题,还需探讨:圣母的服饰为何如此华丽?背景中的日常物品(如窗台、水壶)是否具有象征意义?画面整体的静谧氛围是否反映了北方文艺复兴对“道成肉身”的神学理解?这种理解又如何与当时的市民宗教情感相联系?
潘诺夫斯基强调,图像学阐释必须基于前两个阶段的严谨成果,避免“过度阐释”或“主观臆断”。它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学科视野,综合艺术史、哲学、宗教、社会史、心理学等知识,进行“综合性直觉”(synthetic intuition)的判断。图像学不是“猜测”,而是“有根据的推论”,其结论需能解释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整体一致性。
四、三阶段模型的逻辑结构与方法论特征
潘诺夫斯基的三阶段模型构成一个严密的阐释闭环,其逻辑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递进性与依赖性:三个阶段呈线性递进关系,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前图像志提供“事实材料”,图像志提供“文化语义”,图像学则进行“综合阐释”。脱离前两个阶段的图像学分析易沦为“空谈”,而止步于图像志的描述则无法触及作品的深层意义。
辩证性与整体性:尽管阶段分明,但潘诺夫斯基强调三者在实际研究中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图像学阶段,研究者可能需要返回前图像志层面,重新审视某些形式细节是否被忽略;而在图像志阶段,对主题的识别也可能受到对整体意义的预判影响。因此,该模型并非机械流程,而是一种动态的、反思性的理解过程。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平衡:前图像志与图像志阶段强调客观描述与文献证据,体现科学性;图像学阶段则承认阐释的主观维度,但通过“有根据的推论”保持学术严谨。潘诺夫斯基反对相对主义,主张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检验达成“可验证的理解”。
人文主义取向:该模型将艺术作品视为“人类精神的表达”,而非孤立的形式对象。图像学的最终目标是“理解人”,即通过艺术揭示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信仰与情感结构。
五、案例分析:以扬·凡·艾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为例
为验证潘诺夫斯基模型的实践价值,本文以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 1434)为例进行三阶段分析。
前图像志描述:画面中一对男女站立于室内,男性抬手似在宣誓,女性右手提裙,左手轻触腹部。背景有凸面镜、念珠、拖鞋、狗、枝形吊灯等物品。光线来自左侧窗户,墙上悬挂装饰物。色彩细腻,空间逼真。
图像志分析:结合15世纪意大利与尼德兰风俗,此画可能描绘商人乔瓦尼·阿尔诺芬尼与其妻子的婚姻场景。抬手动作可能象征婚誓,提裙姿态为谦恭礼节,狗象征忠诚,拖鞋脱于床前暗示神圣空间,凸面镜反映见证者(可能包括画家本人)。此画常被视为“婚姻契约”的视觉记录。
图像学阐释:潘诺夫斯基在《早期尼德兰绘画》中指出,此画不仅是肖像,更是“道成肉身”神学观念的象征表达。室内空间象征“童贞女之殿”(Hortus Conclusus),凸面镜象征“神圣之眼”与“完美”,光线象征“圣灵”,女性提裙的手势暗示“接受”与“孕育”。整幅画将世俗婚姻提升至神圣仪式,反映北方文艺复兴时期市民阶层对宗教与日常生活的融合理解。其精细写实不仅是技术成就,更是对“可见世界作为上帝象征”的信仰体现。
此案例清晰展示了三阶段如何层层深入,最终揭示作品超越表象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六、理论评价与当代反思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方法自提出以来,既获得广泛赞誉,也面临诸多批评。其贡献在于:1)为艺术史提供了系统化、可操作的阐释框架;2)提升了艺术史的人文深度,使其从风格史转向文化史;3)强调跨学科研究,促进艺术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的融合。
然而,该方法亦存在局限:1)三阶段模型可能被简化为机械流程,忽视艺术理解的非线性特征;2)图像学阐释易受研究者主观立场影响,存在“过度阐释”风险;3)其人文主义范式在后现代语境下面临挑战,如对“作者意图”“文化统一性”的质疑;4)对非西方艺术的适用性有限,因其基于西方基督教图像传统。
当代艺术史研究在继承潘诺夫斯基遗产的同时,亦发展出新方法,如视觉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等,强调权力、身份与观看机制。然而,潘诺夫斯基的核心洞见——艺术是文化的“征候”——仍具启发意义。其方法论提醒我们:真正的理解需从形式到意义,从表象到精神,保持严谨与开放的平衡。
七、结语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三阶段模型,是20世纪艺术史方法论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前图像志、图像志与图像学的递进结构,他构建了一个从“看见”到“理解”的完整阐释路径。这一模型不仅为艺术作品的解读提供了方法论工具,更确立了艺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认知尊严。在图像泛滥的当代社会,潘诺夫斯基的深刻启示在于:真正的“看”,不仅是视觉的接收,更是意义的追寻。唯有通过系统的、批判性的阐释,我们才能穿透图像的表层,触及人类精神的历史深处。因此,图像学不仅是研究艺术的方法,更是一种理解文明的方式。
文章作者:芦熙霖
声明:本人账号下的所有文章(包括图文、论文、音视频等)自发布之日72小时后可任意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如需约稿,可联系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