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主奴叙事,是科耶夫在这里的关注重点,前者深深地植根于他有关哲学家与奴隶相似性的观念中。以此为出发点,主人和奴隶的区别,完全不同于尼采的高贵和低贱的划分,或许相反,成为一个“奴隶”,过奴隶的生活,或许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科耶夫以为主人是一种陷入困境的存在者。“一个主人确实无法做出任何有着根本重要性的事情,因为主人的本质在于保持原样,也就是说,不去改变。主人已经通过他的死亡意愿向我们表明,他对变化毫无兴趣。为了将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奴隶而情愿去死,这是他不愿改变的最严酷的表达。”
所谓“保持原样”或静止,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完满、完美的存在才能够做到,或许就是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或上帝。上帝不需要变化,因为变化意味着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完美一旦转变了状态,就变成了不完美。我们说人可以成长,从一个说谎者变成诚信者,从一个暴虐者变成怜悯者或秉持善意者;但上帝不需要成长,它反而是我们成长的基础或前提。主人这个角色误以为他的本质就是保持原样,这就像那些独裁者把自己当成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一样荒谬,上帝的为所欲为体现了创世者、完满者的意志,独裁者则暴露了他的本性或者终将覆灭的结局。主人不如说是独裁者形而上的代表,他从所追求的东西中已经消解了自己的存在——正如独裁者将覆灭于权力的狂欢和黄金的饕餮——并从对立面的角度证成了奴隶身份的现实性与进步性。
与主人对变化毫无兴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奴隶“让自己向变化敞开”。在最原始的意义上,奴隶无非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一件工具,其身份由主人根据他要求奴隶去完成的任务来确定,其存在就在于“适应主人的欲望并用那些欲望置换自己的欲望”,但“奴隶不会满足于、满意于一直保持那样的地位”。
“科耶夫坚持认为,主奴关系自身会根据主人逐渐增长的对奴隶的依赖而成比例地改变。”一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即主人由于对奴隶的依赖而逐渐奴隶化——不将自我意识、纯粹理性当作唯一需要听命于它的人注定摆脱不了奴隶化的宿命——而奴隶在服务于主人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时候,将逻辑地开始培育自己的主体化,也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平等不可能永远保持其自身。”奴隶面对的问题或许可以总结为:“缺乏孕育了欲望,后者试图战胜缺乏。”主人无此问题,因此主人是一定会被尼采所唾弃的虽生犹死的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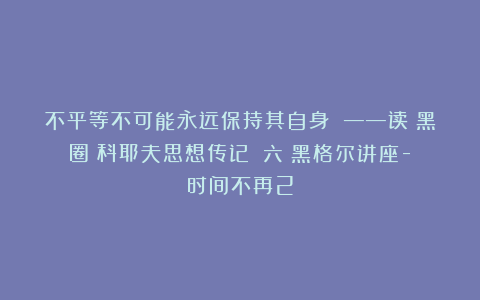
“什么是奴隶的缺乏?它仅仅是身份吗?主宰着奴隶的、创造了他如此这般的身份的,是那种创造了他的最初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作为奴隶生命之起源的缺乏是一种重要的缺乏,一种由死亡来表现的永久性的缺乏。奴隶实际上是认可了非永久性的存在者,在这一意义上,奴隶的可变的、暂时性的存在是对有限性、无法保持其自身存在的存在者,无法将自身从临时转向永恒的存在者的最好表达。”相比于主人的自负或盲目,奴隶是清醒的,后者至少承认了人的有限性。
按照科耶夫,历史的本质体现在奴隶所制定的“计划”,即“改造世界和他的主人”。“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建立其平等认可的社会斗争,主人和奴隶由此战胜了原来的关系,建立了新的,也是最终的关系,如’公民’一词所指的那样,这是一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奴隶与世界的不同形式的改进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思想的不同形式,描述和解释它们,对科耶夫来说,是《精神现象学》的主要目标。《精神现象学》宣告了奴隶的自我意识,这一宣告会带来对奴隶之依赖于外在于他的世界的克服,方法是表明外在世界是奴隶的一种产物——实际上,它之依赖于奴隶就像奴隶依赖它一样。”
思想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基本问题,更不要说终极问题。在科耶夫关于主奴叙事的解读中,奴隶对世界和主人的改造不能被理解为“散播终极真理、和谐的完满的计划”,原因在于“奴隶内在于自我保存和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之间的张力不会轻易得到解决”。我们或许只能得到一点仿佛离题的观念——“哲学是奴隶意识的表达”。
“《精神现象学》中的伟大运动记录着奴隶自觉地发现了自己是一个奴隶及其转变,即把奴隶的存在转化为一种超越了主人和奴隶的存在:圣者。《精神现象学》因此是一部非常特殊的著作,既是哲学的又超越了哲学的界限。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可以说《精神现象学》从一种再也不存在临时性的限制、超越了哲学迄今为止之所见的角度出发,给由观察而来的作为临时性对话的哲学带来了终结,因为它完全和绝对地终结了、’赦免了’所有不现实的可能性。”
评价:4.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