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印象里,安史之乱是什么样子?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歌,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仓皇出逃,是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名将的力挽狂澜,还是一个强大帝国由盛转衰的无奈拐点?
人物脸谱鲜明,情节跌宕起伏,这些画面,构成了我们对那场八年战乱的基本认知。我们习惯了从这个宏大的叙事框架里去理解它:昏君误国、红颜祸水、奸臣当道、忠良救国。
然而,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它像一把精巧的手术刀,冷静地剖开了这层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外壳”,露出了内部复杂而惊人的肌理。这本书告诉我,我们过去所以为的许多“史实”,很可能是在当时、乃至后世,被各种力量精心塑造过的“故事”。历史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更是后来被讲述、被传播、被不断改写的故事。
这本书没有推翻宏大的历史走向,但它邀请我们做一次“历史侦探”,去审视:关于安史之乱,我们究竟知道的是什么?这些“知道”又是从何而来?是谁,出于何种目的,讲述了这些故事?而那些被刻意遗忘、修改或神话的部分,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盛世华袍下的虱子——被“开元盛世”掩盖的暗流
在故事正式开始前,我们必须回到那个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前期,年号“开元”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杜甫那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国力强盛、百姓富足的完美图景。长安城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僧侣,大明宫中上演着最绚丽的歌舞,诗歌、绘画、书法艺术臻于极致。
这袭盛世华袍,光彩夺目,以至于千年后的我们,依然为之神往。
但《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这本书,却首先引导我们去留意这袭华袍之下,那些令人不安的“虱子”。它提醒我们,任何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闪电,而是早已埋下引线的地雷。安史之乱不是755年冬天突然爆发的“意外”,而是开元天宝年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
那么,这些“虱子”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太宗、高宗时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民,中央手握重兵,对四方形成绝对威慑。但到了玄宗时代,均田制逐渐瓦解,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为了防御吐蕃、契丹、奚等周边势力的侵扰,玄宗在边境设立了十个庞大的“节度使”军区。节度使们手握当地行政、财政、军事大权,俨然一方诸侯。他们招募职业军人,这些士兵长期驻守边关,与中央联系薄弱,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天宝年间,唐朝全国总兵力约57万,而边境十大节度使的兵力就占了49万!中央直辖的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长期缺乏战事,武备松弛。
这就好比一个巨人,把绝大部分血液和肌肉都输送到了四肢,躯干和大脑却变得异常脆弱。节度使们力量雄厚,中央却外强中干。安禄山,正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近二十万精兵,才有了发动叛乱的资本。
其次,是错综复杂的民族与身份认同。 唐朝以其开放性著称,大量异族精英进入帝国体制内任职。这本是帝国活力的源泉,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安禄山本人就是杂胡(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他麾下的将领士兵中,有大量粟特人、契丹人、奚人、同罗人等。他们形成了一个以安禄山为核心,具有强烈地域和族群色彩的军事集团。
这个集团与以关中为本位的唐朝中央朝廷之间,存在着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他们既为帝国效力,又可能因文化差异、利益分配或政治上的猜忌而感到疏离。安禄山起兵时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主要指杨国忠),这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那些对中央抱有不满的情绪。
最后,是信息管道的淤塞与失真。 玄宗在位后期,尤其是得到杨贵妃后,逐渐倦于政事,将朝政先后委托给李林甫和杨国忠。李林甫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朝为相的可能,大力主张重用蕃将(他认为蕃将文化低,不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宰相位置),这客观上为安禄山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更重要的是,李林甫和杨国忠都善于操控信息,报喜不报忧,构筑了一个围绕玄宗的“信息茧房”。尽管不断有人警告安禄山有异心,但这些声音大多被压制或无法传到玄宗的耳中。玄宗沉溺于“盛世之主”的幻梦之中,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丧失了警惕。直到叛军攻克洛阳,他才真正相信安禄山造反了。
由此可见,755年的渔阳鼙鼓,敲响的是一面早已布满裂痕的墙。开元盛世的辉煌是真实的,但其下的危机同样真实。《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一书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叛乱归咎于某个人的道德缺陷(比如玄宗昏庸或安禄山狡诈),而是冷静地展示了帝国系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一个高风险结构的。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切,再去看安史之乱,就不会再觉得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剧情反转”,而更像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系统崩溃”。而接下来,关于这场崩溃的“故事”是如何被讲述和加工的,则更加引人入胜。
叛乱的“人设”——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
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正史记载中,几乎是“贪婪”、“残暴”、“狡诈”的代名词。尤其是安禄山,一个三百多斤的肥胖胡人,形象滑稽,包藏祸心,通过装傻充愣骗取皇帝信任,最终反咬一口。这个形象如此深入人心,几乎成了叛贼的标准模板。
但《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看到的这个安禄山,是真实的他,还是他的敌人(唐朝中央)希望后世看到的样子?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安史之乱最终的结局是叛乱被平定,唐朝中央政府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因此,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去系统地“塑造”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形象,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进行“妖魔化”处理,以此证明自身平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第一,“憨直”人设的解构。 正史中喜欢描绘安禄山在玄宗面前如何憨态可掬,甚至假装不懂礼仪来讨好皇帝。例如,他拜见太子时故意不下拜,问“臣不知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何官?”这种故事听起来很有趣,似乎显示了他的愚蠢和玄宗的老糊涂。但仔细一想,一个能周旋于幽燕复杂地缘政治、统领十几万骄兵悍将、将河北地区经营得铁桶一般的人物,怎么可能是个单纯的傻子?
这本书认为,这种“憨直”叙事,很可能是一种双重的宣传策略。一方面,它被唐朝中央用来讽刺玄宗的昏聩,竟然被这样一个“小丑”所蒙蔽,从而将玄宗时期的政策失误部分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它也将安禄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欺骗”,而非其个人能力或当时制度赋予他的巨大能量,这间接维护了唐朝体制本身的“正确性”——不是制度有问题,只是坏人太狡猾。
第二,“残暴”叙事的放大。 关于叛军,尤其是安禄山、史思明部的残暴行为,史书中有大量记载。我们必须承认,战争必然带来破坏,叛军的行为确有残酷之处。但问题在于,历史的记录是不对等的。
唐朝官军的行为,尤其是平叛过程中对百姓的劫掠、对降卒的处理,往往被轻描淡写或刻意美化。而叛军的每一次暴行都会被详细记录并大肆渲染。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录,旨在激发人们对叛军的恐惧与仇恨,凝聚己方士气,同时将叛军定义为“非人”的兽性集团,从而使得任何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都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
第三,对叛军集团内部合理性的彻底抹杀。 安禄山能在河北地区迅速站稳脚跟,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绝不仅仅靠武力恐吓。他很可能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收买人心、争取支持的政策。例如,妥善安置流民、任用本地豪强、维持商业秩序等。但这些内容在唐朝官方记录中几乎完全消失。
历史记录只强调他的“反”,而绝口不提他任何可能存在的“治”。因为承认叛军有任何治理上的合理性,就等于动摇了唐朝中央统治的法理基础。必须将安禄山集团描绘成一个纯粹以破坏和掠夺为生的恐怖集团,才能彻底否定它。
通过这样的宣传,安禄山和史思明被成功地“符号化”了,他们不再是复杂的历史人物,而是变成了“叛乱”、“野蛮”、“邪恶”的抽象符号。这个符号如此强大,以至于掩盖了所有历史细节,一直影响我们到今天。《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所做的,就是尝试剥开这层厚厚的符号油彩,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凭借个人能力与机遇崛起的军阀形象,而非一个简单的恶魔。
红颜祸水?——杨贵妃之死的宣传效用
马嵬坡,公元756年七月十五日。禁军大将陈玄礼带领士兵哗变,诛杀宰相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一代绝世佳人,香消玉殒。
这是安史之乱中最富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场景之一。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将这一幕渲染得凄美缠绵:“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在这个经典叙事里,杨贵妃是“红颜祸水”论的终极牺牲品。她的美丽和得宠,导致了杨国忠的专权,引发了安禄山的嫉妒(另一种说法是为了争夺她),最终招致了这场滔天大祸。士兵们认为,只有杀了她,才能平息天怒人怨,才能保证玄宗的安全和军队的稳定。
这个故事逻辑清晰,情感冲击力强,但它经得起推敲吗?《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首先,杨贵妃有无可能参与朝政? 几乎所有严肃的史料都表明,杨贵妃对政治毫无兴趣。她与她的姐姐们,追求的是艺术享受和物质奢华。真正掌握大权、引发朝野普遍不满的,是她的族兄杨国忠。杨国忠的崛起确实得益于贵妃的受宠,但贵妃本人并未直接介入政治决策。将国家的灾难归咎于一个不同政事的后宫女子,这在逻辑上是牵强的。
那么,为什么士兵们一定要她死? 本书提出了一个更冷酷也更可能的解释:杨贵妃必须死,并非因为她有罪,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最合适的“替罪羊”和“献祭品”。
诛杀杨国忠是兵变的第一步,但这远远不够。杨国忠是具体的施政者,他的死可以平息士兵对具体政策的不满。但杨贵妃代表的是更高一层的符号——她是玄宗晚年怠政、沉溺享乐的象征。不摧毁这个符号,兵变就不彻底,士兵的愤怒就无法完全平息。更重要的是,诛杀贵妃,等于向天下宣告玄宗时代那种“浪漫而腐朽”的统治风格彻底终结,标志着流亡朝廷决心改弦更张(至少表面上如此)。
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政治表演。陈玄礼等军官和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很可能心照不宣。贵妃的死,一方面满足了士兵的情绪,保证了玄宗的暂时安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削弱了玄宗的权威,为太子不久后的灵武自立铺平了道路。玄宗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他的统治权威事实上已经在马嵬坡走到了尽头。
因此,“红颜祸水”的故事,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宣传案例。它将一场复杂深刻的政治-军事危机,简化为一个香艳而悲情的道德寓言。它让所有人的责任都得到了开脱:
玄宗的责任被转移了,他成了被“女祸”迷惑的受害者。
军方将领的责任被掩盖了,他们的兵变被赋予了“清君侧”的正义色彩。
新朝廷(肃宗)的责任被洗清了,他们通过否定贵妃,与父亲的错误划清了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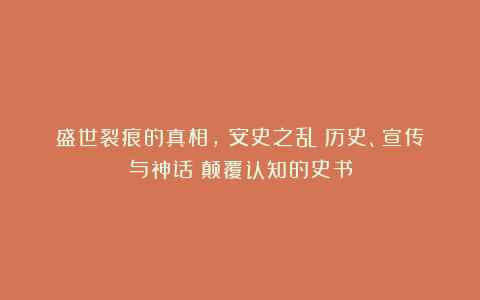
杨贵妃的悲剧在于,她不仅在现实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历史上更成为一个被长期利用的宣传工具。她的真实面貌早已模糊,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被无限言说、承载了太多道德批判的“祸水”符号。《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帮助我们看透了这个符号的生成过程,让我们对历史中的女性命运多了一份深刻的同情和理解。
忠臣的模板——郭子仪与李光弼的神话滤镜
有奸臣叛将,自然就有忠臣良将。在安史之乱的叙事中,郭子仪和李光弼无疑是光辉的顶点。他们被塑造成临危受命、忠心耿耿、力挽狂澜的帝国守护神。尤其是郭子仪,“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得以善终,成了“忠”与“智”的完美化身。
他们的功绩是真实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没有他们,唐朝可能真的就亡了。但《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提醒我们,即便是这些正面人物,他们的历史形象也经历了精心的塑造和打磨,以满足战后重建权威的需要。
“完美忠臣”的制造。 唐朝中央在战后迫切需要树立道德楷模,来冲刷叛乱带来的精神创伤,重建对朝廷的忠诚和信心。郭子仪和李光弼就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的故事被强调和聚焦于以下几个层面:
绝对忠诚: 无论遭遇何种猜忌(郭子仪确实曾被剥夺兵权),他们都毫无怨言,随时听从朝廷召唤。
力挽狂澜: 他们的军事胜利被大书特书,如郭子仪收复两京、李光弼守太原之战,成为乱世中的希望之光。
个人品德: 郭子仪的宽厚大度、李光弼的严毅果敢,被突出描写,使他们成为人格上的完人。
这种塑造,使得他们超越了普通将领的身份,变成了国家正统和儒家忠义精神的象征。
然而,滤镜之下亦有裂痕。 本书并未否定他们的功绩,但它引导我们注意历史记录中被淡化的部分。
例如,李光弼与郭子仪之间并非一团和气,他们作为平叛的两大核心统帅,存在着明显的竞争甚至矛盾。李光弼对郭子仪的某些用兵策略不以为然,二人在协同作战时并非总是默契无间。这些内容在正史中被尽量淡化,因为“忠臣内斗”不符合宣传的基调。
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中央的关系远比“主不疑”的传说更为复杂。肃宗、代宗皇帝对他们这些手握重兵的功臣,始终怀有深刻的戒心。朝廷一方面倚仗他们,另一方面又处处掣肘,派宦官鱼朝恩等人担任观军容使,进行监视和干预。九节度使相州大战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统一指挥,各方将领(包括郭、李)互相猜忌,而宦官监军又瞎指挥造成的。
但最终的历史叙事,将郭子仪塑造成一个能完美处理君臣关系、化解皇帝疑虑的智慧长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当时紧张、猜忌的君臣现实。这个“神话”告诉后来的武将:只要像郭子仪一样绝对忠诚和谦卑,就能得到善终和荣耀。这无疑是对骄兵悍将的一种规训。
因此,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形象,同样是一种“有用的过去”。他们的故事被提炼和纯化,用来服务于战后的秩序重建和思想教化。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宣传机器精心打磨后的“忠臣模板”,一个激励后人、巩固统治的榜样。了解这一点,并非要贬低他们的伟大,而是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是如何被时代需要所塑造的,从而看到一个更立体、更人性化的英雄,而非一尊毫无瑕疵的神像。
沉默的大多数——战乱中普通人的声音在哪里?
我们读历史,目光总是聚焦于帝王将相、英雄奸佞。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历史叙事的主干。但《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一书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落:在那八年的血火烽烟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农民、士兵、工匠、商人——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声音在哪里?
答案是令人沮丧的:他们的声音几乎完全消失了。历史记录是由精英阶层书写的,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作为背景板上一串模糊的数字,或者用来衬托英雄伟业与叛军暴行的抽象符号。
被忽略的视角。 官方史书会记载某次战役斩首数万,会记载收复某座城池,但不会记载战线反复拉锯之下,农田如何荒芜,村庄如何化为废墟。它会记载名将的丰功伟绩,但不会记载一个普通士兵的恐惧、思乡和创伤。它会宏观地描述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但无法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家破人亡的农民的绝望。
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惊人的,估计在三千到四千万之间,这不仅是直接死于战乱,更多是源于战乱后的饥荒和瘟疫。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和无声的悲剧。但这些,在宏大的“平叛叙事”中,被极大地边缘化了。
“民心向背”的复杂性。 传统的叙事习惯于“唐朝中央得民心,叛军失民心”的简单二分法。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安禄山起兵的河北地区,叛军建立了政权(国号“燕”),并且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河北地区没有立刻群起响应王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叛军的统治?
本书提到,这可能与唐朝中央长期的政策有关。河北地区在唐前期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有时被视为“化外之地”,与关陇贵族把持的中央存在隔阂。安禄山在那里经营多年,或许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央的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使得一部分当地精英和民众并未将燕政权视为必须推翻的邪恶存在。
然而,所有关于燕政权如何治理、当地民众真实态度的记录,都因为其“伪朝”的身份而被唐朝官方系统地清除和篡改了。我们只能从胜利者的史书中看到一片“人心思唐”的图景,而那片土地上的沉默和复杂选择,则被永久地埋没了。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沉默”,并让我们意识到历史记录的这种巨大局限性。它提醒我们,在关注那些被大声讲述的故事的同时,更要思考那些被刻意遗忘、被迫沉默的角落。真正完整的历史,应该包括庙堂之上的决策,也包括江湖之远的呻吟。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听到后者的声音,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故事的余波——中晚唐如何讲述这场创伤
安史之乱在763年以史朝义的自杀告终,但它的影响远未结束。对于一个差点灭亡的王朝来说,如何解释、消化和讲述这场巨大的创伤,成为了中晚唐朝廷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历史叙事”的构建,揭示了其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
定性:一场“平定叛乱”的胜利。 首先,朝廷坚定不移地将事件定性为“叛乱”而非“内战”或“分裂战争”。这意味着唐朝中央自始至终是唯一合法政权,安史集团是罪恶的、以下犯上的叛逆。这个定性至关重要,它奠定了所有叙事的基调——这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任何对此的质疑都是不允许的。
在这个框架下,所有参与平叛的官兵都是忠义之士,而所有曾服务于燕政权的人,则被打上“贰臣”的烙印,即便后来投降,其道德污点也难以洗清。这种叙事有力地强化了朝廷的合法性和对忠诚的要求。
归因: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道德化。 如前文所述,官方叙事将乱因高度集中于个别人物的道德缺陷上:玄宗的怠政、李林甫的奸诈、杨国忠的蠢坏、安禄山的包藏祸心。这种解释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能有效地引导公众情绪。
但它刻意回避了那些更深刻、更系统性的制度根源,比如节度使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张力等。讨论这些问题会动摇统治根基,因此必须被掩盖。通过将悲剧归咎于几个“坏人”,体制本身的责任被巧妙地卸掉了,仿佛只要除掉坏人,一切就能回归正轨。
利用:塑造集体记忆以服务当下。 安史之乱的故事成了中晚唐皇帝和朝臣们手中一件灵活的工具。
当朝廷想要削弱藩镇时,就大讲安史之乱的故事,强调藩镇跋扈的危害,激发人们对分裂动荡的恐惧,从而支持中央集权。
当需要表彰忠臣、激励士气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故事就会被反复提及和颂扬。
当内部出现政治斗争时,对手可能会被隐晦地比作“杨国忠”或“安禄山”,从而在道德上将其污名化。
于是,关于安史之乱的历史记忆,不再是冰冷的过去,而成了一个活跃的战场,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和利用它,争夺对这段历史的话语权。官方通过修史、诏书、纪念活动等方式,努力将一套固定的、利于自身统治的叙事植入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安史之乱的许多记载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实”,更是经过中晚唐政治需求层层过滤后的“产品”。这本书帮助我们穿透了这层滤镜,看到了历史书写背后的动力和机制。
历史是真相,也是故事
合上《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这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它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基本史实,却彻底改变了我看待历史的方式。
历史,不仅仅是时间、地点、人物的堆砌,也不仅仅是因果规律的呈现。它更是一场绵延不绝的“讲述”。每一次讲述,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讲述者的立场、目的和时代烙印。胜利者讲述它,是为了巩固胜利;统治者讲述它,是为了教化人心;文学家讲述它,是为了抒发情怀。
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层层讲述叠加后的结果。其中有坚硬的真相内核,也有厚厚的宣传与神话包裹层。《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这本书,正是一把出色的刻刀,它没有否认内核的存在,而是精心地、富有洞见地为我们剥离那些包裹层,让我们得以窥见内核更原始的光芒。
它让我们明白:
要警惕简单的道德叙事。 红颜祸水、奸臣误国、忠奸对立……这些故事听起来很爽,但往往掩盖了复杂的真相。
要追问“谁在说”和“为什么说”。 看到一段史料,一个故事,不妨多想一步:是谁记录了这个?他希望读者产生怎样的看法?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要同情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数。 历史不仅是英雄的史诗,也是无数普通人的悲歌。他们的声音微弱,但他们的苦难同样真实。
最终,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是怀疑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审慎、更加深刻的历史观。它让我们在阅读历史时,能同时感受到两种魅力:一种是探寻真相的乐趣,另一种是剖析“故事”的智慧。
安史之乱早已尘封于岁月,但关于如何讲述它的博弈,某种程度上从未停止。读懂这场博弈,或许能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待过去,也更智慧地面对当下这个信息爆炸、各种叙事纷至沓来的时代。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