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九年级组
银湖实验中学 九(7)班 梁舒越
爷爷去世那年,我八岁。那个夏天格外燥热,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我却再也不能牵着爷爷的手去买冰棍了。他总爱把二十元钱对折两次,小心翼翼地塞进我的掌心,然后拄着拐杖,拖着不太利索的腿,一步一步陪着我走向巷口的小卖部。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永别,只是懵懂地意识到,往后那些酷热的午后,再也不会有人为我留下那张被汗水浸得微潮的纸币了。
爷爷走的那天,是我从海南回来的第三天。母亲红着眼眶告诉我,爷爷在病床上留下的最后一滴泪,是听说我还在回来的路上。我永远错过了他的最后一次呼吸与心跳,也永远错过了与他最后的告别。葬礼上,我望着棺木中安详的睡容,忽然想起那双曾经苍劲有力的手——它们曾稳稳地握着我的小手,在烈日下举着快要融化的冰棍。泪水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涌出,打湿了胸前别着的白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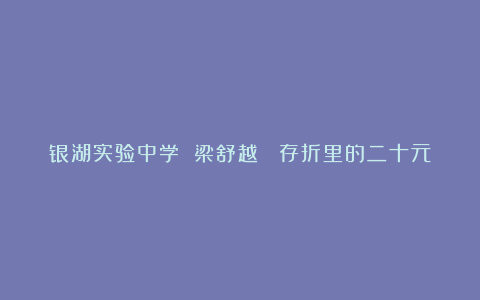
奶奶总爱在藤椅里摇着蒲扇,絮絮地讲起爷爷的故事。他本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万卷,却恰逢文革动荡,不得不中断学业,背起行囊下乡插队。在炼油厂的岁月里,他的手掌磨出厚厚的老茧,却始终没放下对书本的眷恋。退休后,凭着国有企业的稳定退休金,他在海南安度晚年。可命运总爱开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不仅让他的腿脚不再利索,更让他主动切断了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奶奶说,从那以后爷爷就把退休金分成三份,只留最少的那份给自己。
十一岁那年暑假,我又回到海南的老屋。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布满灰尘的旧书架上跳跃。我随手抽出一本泛黄的《三国演义》,却从书页间滑落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拂去封面的浮尘,“存折”两个字渐渐清晰。翻开内页,最后一栏工整地写着:余额20.00元。墨蓝色的字迹微微晕开,像是被什么打湿过。
奶奶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她枯瘦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沉默在空气中蔓延,只听见老式挂钟滴答作响。良久,她深吸一口气,从紧抿的唇间挤出三个字:“走,买冰棍。”我的视线瞬间模糊,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爷爷总爱把化了的冰棍水滴在衬衫上,却始终笑着看我舔食甜筒的模样;他走路时微微倾斜的身影,在烈日下被拉得很长很长;还有他掏钱时总要摸遍所有口袋,最后变魔术般把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币放在我手心。
那本存折终究没有换成冰棍。它被装进透明的保护袋,立在我的床头。每当台灯亮起,昏黄的光线总会为它镀上一层暖意。后来我才懂得,爷爷取消手机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不愿成为儿孙的负担;他分配退休金不是出于无奈,而是把爱意都化作了最实际的守护。
如今我渐渐明白,有些告别看似是永远的错过,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就像存折上永远定格的那二十元,它再也不能换来一支清凉的冰棍,却让那个夏天的温度,跨越时空永远留在了我的生命里。爷爷的爱从未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记忆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倘若没赶上最后一次心跳,何不在往后的岁月里,继续寻找他留下的影子。那些藏在旧物里的温情,那些刻在习惯中的惦念,都是爱的延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珍贵的馈赠,更好地走下去。
喜欢点个“在看”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