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烟袅袅升起时,总觉得那不是水汽,是心湖里漫上来的雾。你执壶的手悬在半空,看沸水注入紫砂壶,茶叶在壶中舒展如蝶——先是蜷着身子抗拒,旋即被烫得坦然,慢慢在滚烫里打开自己。这多像你啊,在人间这壶沸水里,从最初的惊惶,到后来的沉静,终是学会了在翻滚中护持那一点澄明。
初学时总信,做人当如茶青,要在日光下晒得坦荡,摇青时抖落尘埃,只留一身干净通透。那时的茶盏里盛着理想,茶汤要浓得见底,叶底要绿得发亮,连注水的手势都要练到分毫不差。你说“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一杯确定的茶”,便真的像守着一座茶山般,把“不争不比不求”刻在茶席的竹帘上。可茶席外的风总带着沙,有人碰倒你的茶荷,有人嫌你的茶汤太淡,你攥着茶针的手慢慢收紧,才忽然懂:茶要在沸水里滚过,人要在世事里磨过,哪有永远干净的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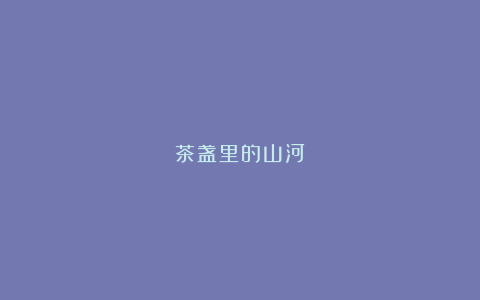
后来你爱上炭焙的老茶。那些在火塘边熬过整夜的茶叶,表皮带着焦糖的温顺,内里却藏着山场的风骨——就像你,嘴上说着“悲喜自渡”,却在朋友摔门而去时,默默把他的茶盏擦得锃亮;心里念着“知足常乐”,却在不公的事面前,忍不住拍案而起。你曾怕这矛盾是种分裂,直到某次冲一泡老枞水仙,见茶叶在壶中沉沉浮浮,忽而想起茶经里说“茶性俭,不宜广”:原来真正的通透,从不是只有一面的澄澈,而是能容得下浓淡,也守得住刚柔。
茶过五泡,茶汤渐淡,却有回甘从舌尖漫上来。你不再执着于“完美”二字。给哭闹的孩子递过一杯温茶,看他小手捧着盏底,忽然明白“温润”不是强装的平和;听千人说“这茶太苦”“那茶太淡”,才懂得“千人同茶不同味”原是人间常态。就像你曾用“温和”当盾牌,把想说的话咽成茶沫,直到学“关公巡城”的匀茶技法——公道杯要稳,分茶要匀,既不能让谁多喝了苦涩,也不能让谁少尝了甘醇。原来人际间的温润,从不是一味包容,而是像炭焙茶师控温那样:既要让茶叶褪去火气,也要留着那点山骨,在“容人”与“护己”间,找到刚好的力道。
此刻壶中茶已七泡,叶底在水中摊成温柔的掌。你举杯时,茶雾里浮出初见的自己:那个捧着茶青说“要干净通透”的少年,和此刻握着老茶盏笑“淡而有味”的你,竟在茶烟中慢慢重叠。窗外的月光落进茶盏,茶汤里盛着半盏清辉,半盏人间——你终于懂了,茶道从不是求一杯无瑕的茶,而是在七泡浓淡里,照见自己的棱角与柔光;人生也不是追一场完美的修行,而是在千般滋味中,守着内心那盏不灭的温光。
茶凉了,你添了些炭火。壶底的红焰明明灭灭,像极了这半生的起伏。而茶烟依旧袅袅,漫过茶席,漫过窗棂,漫过你望向远方的眼——那里有山,有茶,有未说完的话,和终将在茶汤里沉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