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重悲剧中诞生的安魂曲
音乐是什么?在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这里,音乐是时代的墓志铭,是个人无尽悲恸的呐喊。当我们在谈论他的《e小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Op. 67)时,我们谈论的是一部在双重悲剧的阴影下写就的杰作。
时间回到1943年的春天,作曲家已近不惑之年。此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刚刚和他家人从被德军围困的列宁格勒搬到莫斯科。在故乡,他曾亲身经历战火,甚至担任过一名消防员。尽管他从三十年代那场由斯大林亲自发起的、针对其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批判风暴中幸存了下来,但朋友与同僚们在“大清洗”中接连消失的记忆,使得他的生活从未真正轻松过。
在完成了充满战争反思的《第八交响曲》后,他将目光投向了钢琴三重奏这一体裁。这并非他的首次尝试,他早年就写过一部同体裁作品,但直到他去世也未曾发表。而从1943年12月持续到次年8月完成的这部新作,无论在构思的宏大性还是情感的深度上,都与前作有着天壤之别。
这部作品承载的,不仅是那个悲剧时代的回响,更是对一位挚友的沉痛哀悼。1944年2月,他最亲密的知己、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伊万·索勒廷斯基(Ivan Sollertinsky)突然离世,年仅41岁。肖斯塔科维奇的世界崩塌了。在给索勒廷斯基遗孀的信中,他写下了可能是最无助的文字:
“当我收到这个消息时,我的一切都被痛苦所撕裂,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我所受的一切教育都归功于他。没有他的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艰难。”。
于是,他决定将这部新的三重奏,题献给索勒廷斯基的亡魂。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19世纪末柴可夫斯基、阿连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以来,俄罗斯作曲家以钢琴三重奏来纪念逝者的传统。
然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超越了先前的范式,它直面了战争末期德军撤退时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联报纸上揭露的,在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死亡营,党卫军强迫犹太囚犯挖掘自己的坟墓,并在其上跳舞的故事,深深刺痛了作曲家。正是这一发现,催生了作品终曲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之舞”的音乐形象。
一场穿越四个乐章的灵魂拷问
这部三重奏的开篇,堪称整个室内乐文献中最具独创性的神来之笔。它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开始: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大提琴在高音区的泛音上,奏出一段缓慢、飘忽、如泣如诉的旋律。这幽灵般的哀歌,被小提琴家罗斯季斯拉夫·杜宾斯基(Rostislav Dubinsky)精妙地描述为“一种对不幸的焦虑预感”。随后,加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和钢琴弹奏的苍白八度音,在较低的音区模仿并重复着这段旋律。音乐在逐渐的加速中,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内心的不安,它在愤怒、反抗与荒芜、凄凉之间令人不安地摇摆。
第一乐章(Andante – Moderato): 一首由大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鬼火”般的旋律开启,它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悲鸣,预示着一场无法逃避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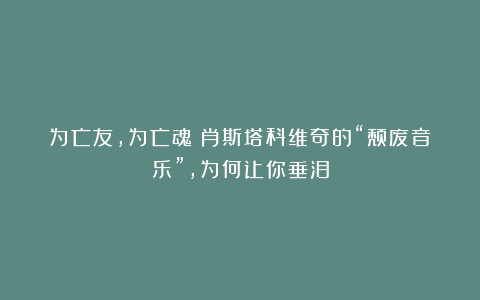
第二乐章(Scherzo: Allegro non troppo): 紧接着的谐谑曲转入了大调,却丝毫没有带来慰藉。这是一个快速、粗暴、毫不留情的乐章,弦乐部分充满了愤怒的咆哮,并穿插着庸俗马戏团音乐的怪诞回响,令人心神不宁。
第三乐章(Largo): 肖斯塔科维奇用一首帕萨卡利亚慢板来回应这种狂乱。乐章的基础,是钢琴奏出的八个冷酷、严峻的和弦。杜宾斯基将这个构思比作“集中营里,锤子敲击铁轨的声音,告诉囚犯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又一天’开始了”。当这“邪恶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时,小提琴与大提琴则在“为那些逝去的人们哭泣和祈祷”。
第四乐章(Finale: Allegretto): 终曲与上一乐章无缝衔接。在钢琴重复的八分音符之上,小提琴用拨奏(pizzicato)的方式,奏出一个带有怪诞犹太音乐风格的舞蹈主题。这种催眠般的旋律模式随着乐章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偏执和疯狂。当不和谐音的强度达到顶点,肖斯塔科维奇将音乐推向了一个狂暴的高潮,并在其后释放出山洪般的声音,让我们回想起第三乐章的帕萨卡利亚和弦与第一乐章的悲歌。最终,在纯粹的精疲力竭中,音乐崩溃了。加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以幽灵般的方式,奏着犹太舞蹈主题的变奏,最终消逝于虚无。杜宾斯基对此的描述字字泣血:
“仿佛在临死的剧痛中,一声哀号从一只被铁手扼住的喉咙里挤出。”。
一场令人垂泪的首演与被压制的呐喊
1944年11月,这部作品在莫斯科迎来了它的首演。肖斯塔科维奇亲自担任钢琴演奏,与他合作的是小提琴家德米特里·齐加诺夫(Dmitri Tsyganov)和大提琴家谢尔盖·希林斯基(Sergei Shirinsky)。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听众完全被这部作品的力量与大胆所震撼 。杜宾斯基后来回忆道:“音乐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人们在现场公然哭泣。而肖斯塔科维奇则显得尴尬而紧张,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笨拙地鞠躬”。
然而,群众的眼泪,并未能软化苏联当局冰冷的神经。他们对这部作品深切的悲观主义感到极度不满,并拒绝批准其任何后续的演出。毫无意外,在1948年那场针对作曲家的、更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中,《第二号钢琴三重奏》被加入了不断变长的“禁演”名单。给出的罪名是,作曲家创作了被认为是“颓废”和“形式主义”的音乐。
一部杰作,诞生于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苦难,在首演时让听众潸然泪下,就这样被雪藏。但历史证明了真正的艺术如同那从被扼住的喉咙里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即便微弱也无法被彻底抹杀。
当政治的铁幕落下,历史的考验换成了一种更为微妙和无形的方式。市场用无形的金钱之手,将这类深刻、沉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艺术,悄然推向边缘。在西方国家,古典音乐的生存,高度依赖于赞助人与基金会的慷慨。这使得艺术的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向商业价值与大众娱乐性低头。艺术不再因为“形式主义”而获罪,却可能因为“不盈利”而被放弃。
与此同时,我们正身处一个被即时满足感和碎片化信息所定义的网络时代。这是一个崇尚短、平、快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肖斯塔科维奇这部需要近半小时的专注、需要听者直面痛苦与沉思的杰作,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它的复杂结构、它的痛苦呻吟、它的深刻诘问,与算法推荐的流行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立。当人们习惯于将情感简化为点赞或分享时,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无法被简单概括的巨大悲痛,又将如何被理解和接纳?
或许,答案正在于它的“不合时宜”。在一个试图用噪音覆盖一切、用娱乐麻痹神经的时代,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恰恰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抵抗。它强迫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去聆听那些被遗忘的哭声,去感受超越个体的不幸,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
它如同一座冷静的纪念碑,矗立在信息的洪流之中,提醒我们历史的伤疤从未远去,人性的挣扎未曾停止。只要还有一个灵魂愿意在它的旋律中停驻、沉思、为之垂泪,这首诞生于双重悲剧中的安魂曲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在新的时代,它为所有需要慰藉且仍在求索的心灵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