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讲台,从“细雪”到“星光”
——第41个教师节感怀
文|钱祥峰
秋风裹着桂香撞进教室,粉笔灰轻轻落在备课笔记上,像细雪覆盖着三十载春秋。我正弯腰捡学生掉落的上面写着“教师节快乐”的纸屑,指尖触到地砖,忽的一丝凉意,蓦然想起我刚踏入教师行业的那年教师节——我攥着磨破边角的教案本,站在漏风的土坯教室后门,泥水正从瓦缝滴落下来,在斑驳的黑板上蜿蜒成歪扭的小溪,桂花树枝在窗外凄楚地摇曳,丝毫闻不出花香……
那时的学校是几间漏风的瓦房,讲台是块裂了纹的木板,黑板擦到边角会掉渣,一节课下来手上全是白灰。我带着五十多个孩子,课本是用了几年的旧书,粉笔要省着用,晚上批改作业全靠一盏昏黄的台灯,可没人觉得苦。孩子们眼里的光比台灯亮,他们会把家里种的橘子偷偷塞给我,会在作业本上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我常想,这三尺讲台,就是我要守的“阵地”。冬天上课裹着棉袄,晚上改作业,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把暖水瓶揣进怀里焐着。
一次批阅作文,对着满桌画满红勾的作文本忽然慌了心神:在深圳打工的发小寄来照片,西装革领端坐办公室,喝着咖啡,一脸的灿烂。而我指甲缝里嵌着难洗净的粉笔灰,袖口沾着拍不掉的板书末——那晚我把备课本压在枕下,竟真的动了改行的念头。可第二天走进教室,后排的小林忽然举起冻得通红的手,掌心托着个温热的烤红薯,小声说:“老师,您吃,我妈烤的。”红薯皮蹭着他的袖口,沾了圈黑灰,那股甜香,顺着冷风钻进心窝,一时竟让我鼻子发酸。昨晚的那点念头像阳光下的晨雾一下子散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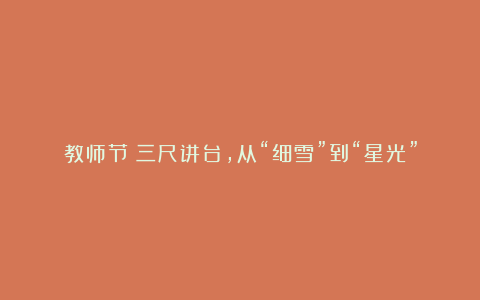
后来的日子像支被拉长的粉笔,一笔一画都是细碎的日常,一晃三十余年。一次和校长抱怨条件苦,他指着墙上“教书育人”四个大红字,说:“苦不苦,看你把心放在哪儿。”校长揣着个搪瓷缸,里面盛着温好的玉米糊糊说“你看西头的小林,上次爬树掏鸟窝,摔破了腿还瘸着来上课,就为听你讲《王二小》”。我想起那个总缩在后排的男孩,总偷偷把橘子塞给我,说“我喜欢听钱老师讲课。”也是那天才懂,有些“放不下”,从来不是因为什么“使命”,而是学生眼里的光,是同事递来的三两枚土鸡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土坯房换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教学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带学生在教室用多媒体上第一节公开课,投影仪亮起的瞬间,前排的瘦小男生突然站起来大喊:”老师!课文里的长城真的会动!”在学生的哄笑中,我的眼里似乎揉进了沙。
如今,黑板都变成了能触屏的电子屏,学生上课用上了平板电脑,但我依旧习惯还用粉笔再写几行字——看着白色的字迹在黑板上缓缓铺开,像看着一颗颗种子落在地里。改作业时依旧逐字逐句画红圈,和学生谈心仍会蹲下来,就像当年蹲在煤炉边,听那个瘸腿的男孩说“我以后也要当老师”。也依然会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走进校园;依旧会和同事为了一堂课的设计争论——只是现在,我们争论的是如何用AI更好地因材施教……
有人问我,卅年重复做一件事,腻吗?我笑而不语。从破旧瓦房到智慧课堂,变的是学校教学条件,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份踏实。
2018年教师节,在市“名教师”表彰会上,遇到当年的羊角辫姑娘,她现在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她替我别上奖章,激动地说:“当年您教我们’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班五十朵’苔花’,现在都开成了牡丹。”大厅的水晶灯璀璨如星,恍惚中又看见那盏灰黄的台灯,一跳一跳的,照亮了半间土坯房。
看着自己学生成了医生、老师、科研人员,看着他们像当年的我一样,为事业全力以赴,一瞬间明了,我们坚守的不仅是讲台,是无数孩子的未来,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凉风又徐徐吹来,桂香漫满了整个校园。站在教室里,指尖划过可以触控书写的屏幕——“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跃然弹出,我认真地把这句话抄写下来,放在备课笔记首页。有学生把亲手折的纸桂插在我的笔筒里,说“老师,这是永不凋谢的桂花”。我又突然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攥着教案本的年轻人,粉笔灰落在柔软的肩头,像撒了把细雪,却眼里有光。所谓的“初心”,无非是坚守。望着校园内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忽地觉得,这些年粉笔灰,落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