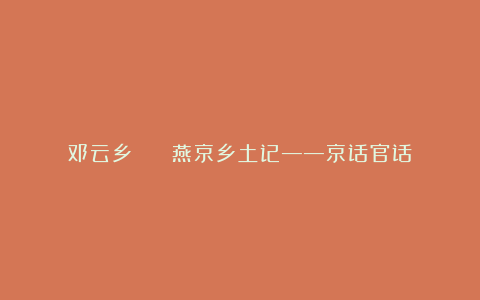上海人笑外地人说不来上海话,曰“洋泾浜”,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人到上海住在洋泾浜一带。当年中国人学两句上海腔的外国话,外国人又学两句外洋腔的上海话,这样就出现了“洋泾浜”。另外北京人嘲笑别人口音不纯,一曰“怯”,二曰“南腔北调”。如果随便说说,那也罢了。如果叫叫“真”,“怯”还可以解释为乡下人不懂北京音,胆小,不敢说等等。那“南腔北调”呢?如果问一声什么“南腔”,什么“北调”,这就回答不出来了。如果细想想这话,也和北京是几百年的首都有点关系。
首先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梨园歌管,日新月异。北曲衰而南曲兴,“临川四梦”,尽是南声;“燕子”“桃花”,亦作北调。就是著名的戏剧院本,不但都是南方人编的,而且昆腔、弋阳腔,一直到后来的徽腔,无一不是南方的腔。再看著名的演员,南明直到康照时代,南京秦淮河的名手自不必说了。直到清朝末年,享盛名的伶人,大都还是南方人,如大名鼎鼎的程长庚,就是安徽人;余三胜是湖北人,有伶界大王之称的梅博士的祖父梅巧玲是江苏泰州人。这些著名人物都是南方人,而他们一生在北京唱由南方腔变化出来的西皮二簧,这不就是标准的南腔北调了吗?
过去的北京,唱昆曲,一定要会说苏州话,这就像其他地方学评弹一样,不会说苏州话是无法唱的。萧长华唱《请太医》,拄一根大杠棍当拐杖,戴一副特大茶晶眼镜,说的就是一口苏白。韩世昌唱《游园惊梦》样样都好,就是苏白不好,真是毫无办法。因为白云生、韩世昌等都是冀中高阳人,唱的是高腔的昆曲,也就是后来演变为“北昆”的剧种。昆山腔而用北音唱,就更是南腔北调了。吴癯庵老夫子当年教韩世昌唱曲子,一个苏州音教来教去教不会,萧重梅(劳)老先生说起这段故事,边学边讲,极为引人发笑,可惜我文字上无法表现声音,不能记下来,太遗憾了。
明清两代行科举制,三年一赶考,各省举子到北京去会试,南方文风盛,赶考的举子多,而他们的口音自然十分复杂。如果闽南人说闽南语,广东人说广东话,杭州人说杭州话,四川人说四川话,苏州人说苏州话……这便大家统统不懂“话”了。怎么办?于是当时真正流行了一种南腔北调的话,谓之“官话”,又叫“蓝青官话”、 “月白官话”,也是以北京调为基础的,这种话专门流行于官场,在北京各衙门中盛行通用这种话。有些跟官的长随、听差也说这种腔调的话,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官儿,回到家乡却爱仗着官气去欺侮人,谓之“打官腔”,人们对此更是十分痛恨的。至于南腔北调,看来比打官腔还是好得多了。
再有北京是几百年的都城,一些老住户惯说京话,自然伶牙俐齿,轻薄之徒,难免就要嘲弄外地人,常常在语言上编了不少笑话,拿操各地土音的人开玩笑。如嘲笑山西人为“老西儿”,编笑话云:
“三个客人,两个茶碗(读如瓦),掌柜的不是外人,使个大碗吧 (音如’是个大王八’)。”
嘲笑定兴人怯音:
“这个黄天霸儿,拿着个修脚刀儿,说:贼儿,贼儿,我给你剃个头儿。”(因那时剃头、修脚师傅都是定兴人)
嘲笑绍兴人为臭豆腐,编笑话道:
“臭豆腐,酱豆腐,五香的豆腐干呀!”
我十来岁才到北京,一口乡音,不知受过小朋友多少嘲弄,现在想想还好笑,可惜现在没有人这样嘲弄我了,有谁再这样笑笑我该多好呢?
阅读链接
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陈红
审校: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