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壶,便唤作“德钟”了。名字是顶好的,不张扬,却自有分量,像古寺里沉沉的钟声,听着便教人心下肃然。壶身是饱满的,却又不是那等蠢笨的圆,线条从微侈的壶口下来,一路收敛,到底座处却又稳稳地停住,像一位端方的君子,拱着手,默然立在那里。那一种从容的、收敛的气度,竟让我想起《考工记》里的话来:“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眼前这壶,怕便是那“述之守之”的功夫了,不是奇技淫巧,乃是一种规矩,一种传承。
我将它捧在手里,竟是微凉的,沉甸甸的,是一种安心的分量。指腹轻轻抚过壶身,那紫泥的肌理,细腻中藏着沙砾的质感,竟不像是在触着一件器物,倒像是在摩挲一段被光阴浸得温润了的旧木,或是一块溪水里长年累月冲刷着的卵石。这凉意,这沉实,仿佛将书斋里那一点虚浮的燥气都压了下去。我想,王国维先生当年于案头摩挲他的那些金石拓片时,指间所感的,大约也是这样一种与往古相接的、微凉而坚实的慰藉罢。
壶总是要用了,才见得它的好处。捻一撮铁观音,投入壶中,簌簌地响,像是雨打竹叶。沸水冲下去,那声音便闷住了,只在壶腹里回荡着,嗡嗡的,果然是钟磬的余韵了。顷刻,茶香便一丝丝地从那壶嘴里逸出来,不疾不徐的,是那种被紫泥滤过的、格外醇厚的香。这香气,混着书卷的霉旧气,在静寂的空气里盘桓着,竟酿出一种特别的氛围来。我忽然无端地想起静安先生的词句来:“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眼前倒没有山寺夕曛,只是这茶香与墨香缭绕的片刻,心里也仿佛有了那种“微茫”的、远离尘嚣的幽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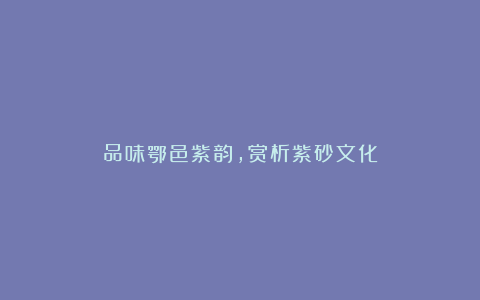
一盏茶在面前,汤色是琥珀样的,澄澈得很。呷一口,舌尖先是一点清苦,随即化开,便是满口的甘润了。这苦与甘的转换,竟也带着些人生的况味。我摩挲着温热的壶身,看它默然无语,只以周身的光泽与掌心的温度应和我。它不像玻璃那般通透,将内里的一切都坦露给人看;它是有涵养的,将一壶的春色与暖意都蕴藏在敦厚的躯壳里,只在你需要时,才从那小小的嘴里,给你一线温润的滋润。这何尝不似古之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呢?
夜渐渐深了,窗外的市声也仿佛沉了下去。我收起壶,用清水细细地涤荡,那紫玉般的光泽,在灯下愈发地温润可爱。想起静安先生在《此君轩记》里赞美竹子的“凌寒暑而不易其色”,这小小的德钟壶,不也如此么?它不言不语,只是安然地居于案头一隅,任是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它只以它那份固有的、从泥土与火焰中炼就的沉静,度着它的岁月。这份“不易”,在如今这光怪陆离的人世间,怕是比什么都来得珍贵了。
壶已净,水已干,我将它轻轻放回原处。它便又成了那个沉默的、端方的影子。我知道,明日,后日,无数的日子,它仍会在那里,用它那“德钟”般的雍容与古朴,镇着这一室的清寂,也镇着我这颗时而浮躁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