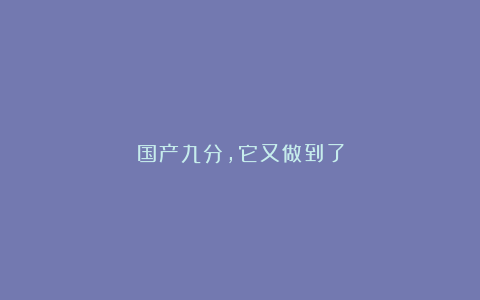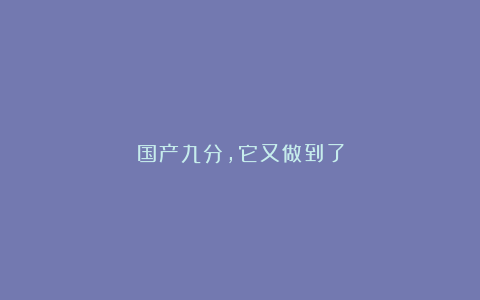|
不再局限于大部头翻译、图书馆建造,而是增加了具体人物的游历:
以前,我们看《但是还有书籍》,是围观着一盏烛火,看它的灯芯怎么打磨、怎么迸出火星子。
而这次,这盏灯回到生活的原野,试图照亮四周的山坡。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要读什么样的书、怎么督促自己开始读书?
在没有灯的屋子里,她说:“我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意义,这种近乎于本能的东西,你是挡不住的。”
12岁那年的暑假,史然的先天性青光眼突然加重,三五天之内就完全看不见了。
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暮年几乎失明,口述完成了这部自传体小说。
靠着长期阅读,史然考入了中国盲文出版社,成为了一名校对。
盲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如果不做好句读,很容易产生误解。
比如“翁同龢、光绪”,只靠读音,会被以为是“翁同、和、光绪”。
史然就这样,一点点通过句读,把盲眼人脑海中那个黑暗的世界,变得清晰可感。
只是,盲文书的制作费时费力,每年只有不到10%的图书是以盲文格式出版。
他因病失明的少年时代,是被院子里一声声新闻广播叫醒的。
1987年,长春大学创办了特殊教育学院,还破天荒地开办了中文系。
入学后,何川想了个法子,和明眼人朋友做一个浪漫的交易——“以歌易书”。
何川还是没法读到完整的《百年孤独》,因为朋友的转述,总把一些“少儿不宜”隐去。
千禧年,何川加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开发组,和同事们发明了听书机,这台长得像“小灵通”的机器从此改变了盲人的阅读生态。
一天夜里,何川收到了一位老人的电话,他激动地说自己通过听书机读完了《水浒传》,那是他第一次读到这本名著。
接下来,又一声叹息:“只是我现在已经70岁,这幸福还是来得太晚了。”
孩子们像过去的诗人一样登高望远,在风中听着《小王子》。
或许每个盲眼的孩子,都是生活在612星球、孤独数着几百次日落的小王子。
好在,“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
镜头外,人们在纷繁的现实中,往往要绕好大一圈的路,才找到最终的答案。
除了光明的指引,书籍,还成了很多人“出走的决心”。
一位在出走中写字的异乡人,震动了国内的非虚构写作圈。
范雨素,一名20岁就从湖北襄阳来到北京打工的家政工。
因为2017年的一篇点击400w 的自传式文章《我是范雨素》广为人知。
她是一位疲于生计的单身母亲,一名遭人冷眼的家政工,一个从地狱般的家暴中逃离的中年妇女。
自由、平等和外面的大世界,就通过文字,根植在小范雨素的心里。
12岁,这个看着《堂吉诃德》长大的小女孩留下了一句“赤脚走天涯”,就一路逃票,从湖北出走海南。
但,范雨素从未停止自己的出走。20岁来到车水马龙的北京,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家暴的丈夫。
范雨素在东五环的出租屋里,把一个以纸板作桌面的木桌放在床上,就开始了书写。
他们也开始写关乎底层的文字,哪怕只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微弱共鸣。
因非虚构成名的她,却开始了很多人不看好的虚构创作。
她的新书《久别重逢》,写家乡的荒诞迷梦、鬼神传说。
特德·姜的科幻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中,语言学家通过外星文字,解读了自己的命运。
让“自我”在文字手术刀中被雕刻得鲜血淋漓又无坚不摧。
采访时,她刚从一场漫长的环岛骑行中结束,笑着给骑车的摔伤涂药。
回忆道:自己的写作,是从童年时期广西的一间小黑屋开始的。
11岁的林白学会了自己做饭,怕黑的她每夜用被子蒙住头,在孤独和恐惧中睡去。
青春期的她,只能在日记本上写下血肉模糊的孤僻文字。
抗拒着母亲、乡亲们对她“写诗无用”的嘲讽,林白逃离家乡了考入武汉大学。
书里浓烈阴郁的情感,对肉体欲望的追逐,成为了一颗文坛的深水炸弹。
林白没有获得文坛的认可与荣誉。相反,是持续八年的失业。
《说吧,房间》,一本详细讲述女性流产和鸭嘴钳阴影的小说。
从大众避之不及的先锋创作者,到如今的女性主义热门文学家。
最新小说《北流》,是她童年那座广西小城的名字,她终于开始触碰那个母亲经历过的大炼钢铁年代。
童年时面貌模糊的母亲,变成了小说中切实的罗医生,一个坚韧的生活战士。
或许这不是真正的和解,林白最后也对没对母亲说出“爱”这个字。
但是她已经用文字,拥抱了这个最遥远的陌生人的存在。
第三季的《但是还有书籍》讲述的故事更加平凡。又为什么让观众屡屡落泪?
Sir想用一个成语的字面意思来解释,“凿壁偷光”。
时代的墙壁太厚了,我们急需书籍这点光芒照亮贫瘠的人生。
也是因为,我们明明知道如何才能精神得救,却苦于惰性和生活的糟烂而一路下沉。
再厚的障壁,也能以一种崎岖的方式,透出些微光亮来。
《三诗人书简》,保存着上世纪20年代,三位白银时代诗人的信件交往。
里尔克宁静玄妙、帕斯捷尔纳克拘谨隐喻、茨维塔耶娃热情倾泻。
身体病痛与政治迫害,都让位于信纸上的抒情诗交流,三个人的精神拥抱着彼此,近乎柏拉图之爱。
最有趣的,是《三诗人书简》的翻译被刊载后,一封来自贵州山区的读者来信。
“我不喜欢大海,大海是躁动的,是冰凉的。我喜欢山,山象征一种稳定,我可以去依靠。”
就是这句话,让这个一直厌恶贵州的大山、想要走出去的读者意识到,山也有山的好,不如,我就安然地在这里待下去吧。
但,这和白银时代文学倡导的“现实之外,还有更理想更审美的生活”不谋而合。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他不会知道,自己在书简中留下的刹那光芒,已经照向了百年后的山海之间。
观众们赞美,说做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是“不合时宜”的勇气。
实际上,主创也好,纪录片中的人物们也罢,他们只是走在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不问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