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西玛长老
(续前)《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中的英雄们面临着一个核心困难,即“理性与自由或者理性与意志之间的冲突,都被证明是无法调和的——人们必须选择自杀或者地下室人的混乱,他无力解决任何问题”。他们追求某种自由,想要从某种“令人蒙羞的自然之力”中解放出来,但找不到努力可以为之有结果的必然性。
佐西玛长老作为另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转化混乱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他的做法是进行下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转换:从一种自由,它唯一导向了一种从来自其意志的或胡说的英雄们的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梦想的限制中摆脱出来的自由;到另一种自由,它认可某种生活方式,后者是作为一种实际上的计划任务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强调的重点不在终极或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据其定义在此生此世毫无立锥之地——而是这样的自由:它的实现主要是作为一种与他人之间的、并在他人之中的关系。这种类型的自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意志英雄所追求的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性或不一致性作为其可能性的条件⋯⋯”
无论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那种政治形式的乌托邦,还是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的形而上学形式的乌托邦,他们专注的都是自我在自由的终极目标之下可以达到的状态。到了佐西玛长老,自由必须在一种基于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可能,这仿佛拓展了自由得以实现的疆域和可能性。在行将就木之际,佐西玛长老说明了这一观点:
“一个修士⋯⋯只有当他意识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坏,而且应该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为人类的一切罪恶——不管是全体的或是个人的罪恶负责,那时我们才算达到了隐修的目的。因为你们要知道,亲爱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
佐西玛长老提出了对修士的道德或信仰要求,即使我们不是某种宗教信仰者,我们也能够、应该理解这种“每个人都有对彼此的责任”的基本假定的真理性。“其他人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与此相反,他人之所以是’为我们而在’的,仅仅局限在我们确定自身是有责任的或者要回应他们的范围内。”
因为,在最低层次的功利主义的层面,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的肯定,他人所遭受的不义之事,某个时候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否认这一点不但可笑,而且近乎自欺欺人。这就像一头当屠夫进入羊圈时躲在最里面角落里的羊,以为轮不到自己,不知道那只是迟早之事。
还因为,在道德层面,一种尊严、崇高感和康德的“绝对命令”“逼迫”我们不得不将他人和我们自己同等视为“人是目的”的范畴之内,因为如果我们将某人视作实现自己某种目的或规避某种风险的工具,那么逻辑的推论就是:我们也会成为工具。一个互害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其中,为牛肉贩修冰箱的维修工故意留下后门,以便不久还可以再次赚一笔维修费;牛肉贩将过期牛肉作为礼物送给对方,既表达了谢意,又处理了变质牛肉。但是二人却谁都没有得到好处,冰箱需要再次维修,维修工进入医院。作为工具化的人不但已经脱离了人的本质属性,更是权力最喜欢的形式,因为后者这样就可以为所欲为——其典型形式是,将工具人纳入到每个宏大的“我们”当中,但其实只有作为代价的时候,“我”才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好处,“我”就在“我们”当中难以察觉的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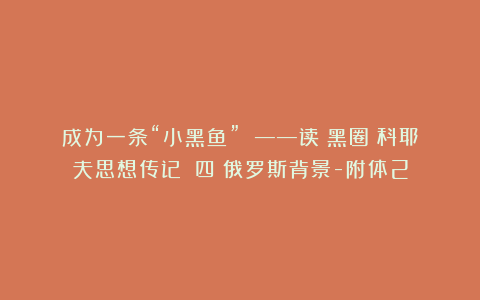
佐西玛长老的出发点是对神的忠诚,但这种忠诚体现在我们对他人的忠诚上。“与他人的关系定义了一个人的虔诚和信仰。”
费拉庞特神父是佐西玛长老的对立面。在他那里,“神必须先于任何其他的人。与神的关系胜过了与其他人的关系。个体的救赎是核心,而不是作为拯救群体的计划,或者建立一个诸如此类的群体”。费拉庞特神父仿佛更加虔诚,但可能反而暴露了他或许是在演戏,让我们看到在这种过于招摇的虔诚面具下,“人不会跟上帝相连,而是跟人的虚荣相连,正是这一虚荣驱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其他英雄们去挑战上帝”。佐西玛长老或许体现了真正的虔诚,他让自己在他人面前保持谦卑,因此不会有费拉庞特神父“将自身置于他人之先”的虚荣。
经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张力就在于他没有明确站在上述二人的任何一边。“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于他人和为了他人也为所有其他人的责任”,佐西玛长老的思想好像对大多数人更有吸引力,但是它仿佛马上就被前者发臭的尸体所证伪了。因为没有奇迹发生——奇迹说,圣洁的人死后尸体不会发臭——而我们最愿意相信奇迹,这种一厢情愿源于不用思考是最轻松的生存方式,我们喜欢轻松。费拉庞特神父因此成了质疑佐西玛长老圣洁性的代表,它也有信仰上的理由。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而且为了众人而有罪,这就意味着“我们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偶像而且担负起为了全体的责任,然而这责任会逐步侵蚀上帝的权威,尽管是以细微的方式”。“费拉庞特神父再次确认了个体救赎的重要性是首要的,高于对一个彼此平等的群体的全体成员的救赎——我们是上帝的奴仆,不是人的奴仆。”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不同的意志英雄,但都是柏拉图朝向美的爱若斯的对立面,他们朝向的是“美的残缺、破坏、丑陋、不和谐”。地下室人的意志优先性是确保完成或完善不可能实现,拉斯柯尔尼科夫试图治愈创伤,基里洛夫试图任其如此。
“柏拉图的神圣疯狂所寻求的自由是从此生此世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从如此之多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臣服的侮辱和必然性之中摆脱出来。这一自由在意志英雄中发现了自己的对立镜像。意志英雄的核心不是建立新耶路撒冷的欲望,也不是超越所有人类限制,变成一个神的欲望。毋宁说,意志英雄是一个纯粹的反抗者,一个追求嘲弄或贬低创造的人。他是所有人中最具攻击性的疯人或罪犯,因为意志英雄只有一个意图:否定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上被视权威的任何东西。意志英雄是批判者,他超越语言直达行动——他进行否定,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必然带来好处(正如《浮士德》第一部中梅菲斯特所说的:’我是那种力量的一部分/总是向往着罪恶,但做的却是好事。’)。在此出现的大问题是:这一意志英雄关注着个体的救赎,关注与上帝合一的努力,关注变成一个与俗世和其他所有相对立的神,但他是否是那个最危险也最暴力的罪犯呢?与这一引人注目的人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我牺牲或虚已的英雄,这个社会性的英雄最英勇的行为不是最高的自我肯定,而是其直接的对立面:最高程度的自我弃绝,后者实现在某种接近于对他人的、对全部人类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他人、为了全人类的责任之中。”
柏拉图追求的是理念世界所体现出的本真,是肯定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现世的和否定性的,既否定自我,也否定世界;他从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和斯塔夫罗金一直上升到佐西玛长老,让我们看到了否定的最高项,一种可行的生存模式——将对于他人、对于全人类的责任纳入到自身生存本质当中的模式。在其中,我们感受到陌生、疏离、艰难、痛苦,很少会感受到幸福,一想到佐西玛长老发臭的尸体就会感到如芒在背,就算康德为我们在彼岸世界预备的幸福都不能起到安慰作用。
但我们喜欢将自由建立在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中的想法,喜欢成为李欧·李奥尼笔下的那条“小黑鱼”,它成为了无数小鱼组成的大鱼的眼睛,他们因此终于吓退了那条想要将大海变成杀戮战场的凶狠的大鱼——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想要利用、蹂躏我们,想要让我们相信丛林法则是生存的唯一法则的作为利维坦的权力。
我们因此更喜欢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苹果,就像一个终于明白学习真相的高中生一样,开始学会享受一种艰难的幸福,这是那种喜欢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到苹果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也永远无法享受到的。
评价:4.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