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原任职或者上下级单位在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利用开办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收取“咨询费”“顾问费’的,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咨询费;顾问费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某,1954年9月生,先后任A省保监局副局长和B省、C省保监局局长,2013年7月退休。
谢某退休后,成立或者实际控制了7家从事保险业务的咨询、投资公司共聘用员工13人,员工月工资3500元至6000元不等,均无保险教育及从业背景,不具备提供保险领域专业服务的能力。2014年至2017年,谢某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保险监管干部职务上的行为,帮助相关企业违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申筹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代理公司升格,或获取监管底护谋取保险市场不正当竞争优势,以其实际控制公司收取请托人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支付的 1251万余元钱款。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请托具有行政许可管辖权的监管干部,帮助某保险代理公司牌照升格及2家公司申筹保险经纪公司,并收取“咨询费”“顾问费”共计250万余元。
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谢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分别与A保险代理公司及其他2家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为A公司牌照升格及其他2家公司申筹保险经纪公司提供咨询服务。2016年2月,A公司和另外2家公司考虑到谢某曾担任多地保监局的领导,且与A公司所在地的银保监局副局长江某某关系密切,遂请托谢某帮助牌照升格,帮助其通过属地保监局、保监会等审批,并支付“咨询费”50万元。同年7月至8月,谢某多次请托江某某及原保监会高层领导,帮助其他保险经纪公司通过属地保监局、保监会批复。后公司牌照升格,另外1家经纪公司申筹通过属地保监局和保监会批准,另外1家经纪公司申筹通过属地保监局审批,但未获保监会批复。其间,A公司和另外2家公司向谢某控制的公司支付“咨询费”“代理费”200余万元。
(二)请托具有行政许可管辖权的监管干部,帮助相关公司申筹保险公司,并收取“顾问费”“申筹费”625 万元
2015年至2016年,谢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与B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协议,约定提供“准备申筹材料、协调审批部门关系”等服务,帮助申筹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并收取“顾问费”“申筹费”共计625万元。随后,谢某请托B公司属地保监局局长等人帮助申筹健康保险公司并出具同意意见函,请托保监会发改部有关领导干部同意接收上述健康保险公司筹建材料,请托保监会财产险部有关领导干部关照养老保险公司申筹等。后包括B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的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筹建均获属地保监局同意,但未获保监会批复,谢某实际控制公司收取的“顾问费”“申筹费”也未退回。
(三)请托具有行政许可管辖权的监管干部,帮助3家保险中介机构获取监管庇护,并收取咨询费合计376万元
2014年11月至2021年9月,谢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分别与C、D、E等3家保险中介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协助建立良好监管生态圈,指导开展管理机关的沟通汇报工作,必要时对接适当外部资源等”,以“咨询费”等名义每月收取1万元至3万元,共计376万元。其间,谢某帮助C、D、E公司主要做了以下事项:
一是应C公司实际控制人梁某某请托,通过向C公司属地保监局领导说情、打招呼等方式,帮助因被监管处罚停业的C公司申请复业及升格为全国代理牌照,收取C公司支付的“咨询费”120万元。
二是应D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某某请托,通过向D公司属地保监局领导打招呼的方式,帮助D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获得监管庇护,减少或减轻行政处罚,收取D公司支付的“咨询费”126万元。
三是应E公司请托,在其原任职地等设立分支机构及减少、减轻行政处罚,收取“咨询费”130万元。
【争议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取“咨询费”“顾问费”等行为的性质认定。
【问题解析】
2009 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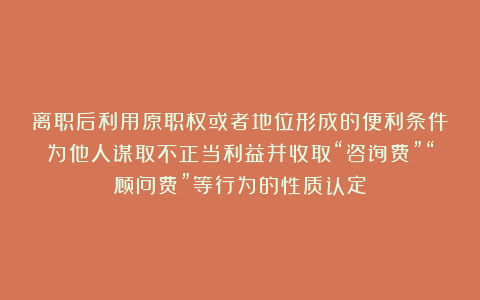
该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款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实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案件,即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较为常见,在处理与认定时争议较少。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势之一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由于实施行为时已经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手段上具有隐蔽性,方式上往往具有公司经营等“合法性”外衣,在认定时往往存在争议。本案即属于此类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对于谢某离职后向其非原任职地的监管部门领导或者上级部门领导打招呼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产生了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谢某作为保险监管部门的领导,其影响力主要在任职地,离职前对其他省份或者上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形成实质上的制约关系,离职后影响力更是有限,故不宜认定谢某利用原职权或术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我们认为,对谢某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理由是:对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所规定的“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应当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所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作同质理解,即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谢某长期在保监会系统工作,曾任A省保监局副局长和B省、C省保监局局长,离职前系正厅级实职领导干部,其任职保监局辖区内保险市场体量位居全国前列,在保险监管系统内陆位较重,在保险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对任职过的3地保监局具有较强影响力,同时对任职期间有过工作交集的保监会、各保监局监管干部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二)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
总体来看,谢某应请托为相关公司谋取的利益均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不正当利益”。该条所规定的“不正当利益”应与受贿罪、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作同一理解与认定,即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等。具体到本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帮助相关保险代理公司谋取不公平、不公正的市场竞争优势。一是从审批权看,保险代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备案制、其高管实行审批制,即经属地保监局同意可申请备案并报批高管资格,取得合法代理资质,否则无法开展代理业务。二是从保险代理牌照价值看,保监会对代理公司审批实行“窗口指导”以来,代理牌照审批难度加大,甚至出现“加盟制”变相出租牌照等现象。三是从被检查及处罚情况看,保险代理市场存在机构存量多同质化竞争严重且失序、违规问题突出等普遍情况,各保监局每年会选取部鳛臣粘保险代理公司进行检查,并针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罚。本案中,与谢某实际控制公司“合作”的保险代理公司,有的顺利在多地设立多家分支机构有的长期未被监管部门检查或处罚,有的虽被处罚但相对较轻,谢某涉嫌利用影响力干扰相关保监局正常的审批、检查、处罚等监管履职,帮助相关保险代理公司谋取审批便利、监管庇护等“不正当利益”。
2.帮助股东资格受限制、未按要求实缴注册资金等相关保险代理公司牌照升格、保险经纪公司申筹通过监管审批。一是从审批权看,保险经纪公司设立,需报属地保监局受理并通过初审后,上报保监会批复;保险代理公司申请升格全国性牌照,需属地保监局受理并审核后向保监会报告,保监会同意后由属地保监局批复。二是从牌照价值看,保险经纪牌照很难获得,2016年以来全国仅批复62家保险经纪公司,即包括谢某帮助批设的1家,互联网企业进军保险业后保险经纪公司牌照“水涨船高”;全国性保险代理牌照需实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代理牌照升格被严格控制,2016年以来全国仅批复20家升格为全国性代理牌照,即包括谢某帮助审批升格的1家。本案中,与谢某实际控制公司“合作”的保险中介公司,有的股东不符合监管要求,有的在申筹过程中存在注册资金来源不真实、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违规行为,但能够通过审核、批复,谢某涉嫌向保监会、属地保监局监管干部打招呼,帮助其谋取“不正当利益”。
3.帮助相关公司运作保险公司申筹,疏通各级监管部门关系试图通过审批。从牌照价值看,保险行业属于特许经营行业,保险公司牌照属于稀缺资源。对很多地方投资平台、大型企业集团、地产企业、新兴互联网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有的上市公司以能够参股保险公司作为重大利好提升股价。鉴于此,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牌照的控制十分严格,一个省最多申请1家到2家保险公司。从审批权看,拟筹建保险公司的股东除具备《保险法》规定的条件外,还需属地省政府出具支持意见函,省政府一般需征求属地保监局意见,如省政府及属地保监局不予支持,保监会一般不会接收申筹材料。本案中,与谢某“合作”的相关公司能够取得属地保监局等出具支持意见、保监会发改部能够同意接收申筹材料,充分说明谢某利用影响力干扰监管部门正常履职,帮助请托人获取了不正当竞争优势。
(三)关于谢某收取的“咨询费”“顾问费”的性质认定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于谢某收取的“咨询费”“顾问费”的性质认定亦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谢某收取的“咨询费”“顾问费”属于离职人员违规兼职收人,应按违纪处理。理由是,谢某在保险监管部门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保险业务经验,其为相关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行为虽然有违规之处,但在无相关证据证明谢某在离职前与相关公司通谋,意图在离职后收取其输送的利益的情况下,不宜将离职人员违规兼职的行为按犯罪处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谢某利用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公司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审批便利和监管庇护,收取的“咨询费”“顾问费”实质上是未提供基于市场活动的正常咨询、顾问服务而获取的不正当收益,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的离职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
一是谢某实际控制公司不具备提供保险专业金融服务的能力。如前述谢某实际控制的7家公司仅有13人,10人无保险教育背景或从业经历,且比较金融领域从业人员工资收入等,基本不具备为保险机构提供专业咨询、顾问业务的能力,且相关经营支出主要是餐费、差旅费、员工工资等,未见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的费用支出。
二是谢某实际控制公司与相关公司签订咨询、顾问合同,约定服务事项无实质内容。约定服务主要为“协助建立良性的监管生态圈,指导开展管。机关的沟通汇报工作,必要时对接适当的外部资源;及时提供保险行业信息发展动态、监管政策等资讯,提供有关行业交流平台,为发展战略及经营提供专业建议;根据需求,不定期为合规经营、牌照管理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专项培训及问题解决方案”,其合同约定事项主要体现在协调监管关系,未见要求提供实质性的专业法律咨询、公司财务顾问等金融专业服务此外,根据有关规定,保监会及各保监局均公示行政许可材料目录、格式求和服务指南等,并设置专门窗口接受咨询及受理申请,在保险中介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设立保险经纪公司、筹建保险公司过程中,均可通过公开、正常渠道获取信息;保险中介机构经营过程中,主要围绕保险客户开展保险代理、经纪、公估业务,相关保险中介机构也具备相应专业能力,所谓的行业数据资料在原银保监会网站及一些公开媒体均可以查询。鉴于此,保险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及获取行业信息、设立保险经纪公司、筹建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办理,不需要通过其他公司提供所谓的咨询服务。
综上,谢某离职后以开办咨询公司为幌子,以收取“咨询费”“顾问费’为名义,实质上是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郭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 金纪)
(审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赵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