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穆尔】
Roger Mühl
“美”这个字,打眼一看就招人喜欢。这是最近直播晚霞,看到大家打出“美”时想到的。
小时候在田字格里写它,歪着脑袋看,总觉得这字在笑。上面两点像一对小眼睛,中间竖提是挺直的鼻梁,底下那一撇一捺舒舒展展地铺开,活像一张咧开的嘴。整张“脸”亮堂堂的,像是刚吃了糖,藏不住的欢喜。
后来才晓得,古人造字,真把“羊”搁了进去。羊在老辈人眼里是好东西,有它就有肉吃,有皮穿,是实实在在的福气。所以“美”字一落地,骨子里就带着暖烘烘的气息,光是看着,心也跟着松快起来。
这字笔画不多,可要写得好看,得讲究。两点要轻,像刚钻出土的草尖,不声不响却透着活气;中间“羊”字的横画得平,像村口晒谷的青石板,稳稳当当撑住上下;最末那撇捺,得放开手写,像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随风荡开,才显得自在。我小时候总爱把撇捺拖得老长,老师皱眉:“收着点!”可我偏觉得,不这样写,就配不上“美”字那股敞亮劲儿——它就该是舒坦的,是野地里开花,不躲不藏,大大方方把香气散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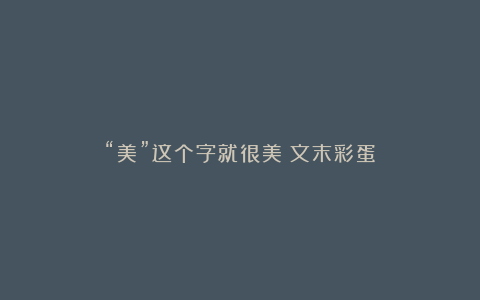
“美”字能耐大着呢,不光看,还能尝、能听、能揣在怀里。说“美味”,是灶上砂锅咕嘟着,掀盖时扑你一脸的肉香;说“美声”,是戏台上传来的唱腔,绕着屋梁打转,半宿还往耳朵里钻;说“美滋滋”,是兜里摸出颗糖,纸都揉皱了也不舍得剥开。一个字,装得下这么多滋味,像个旧木匣子,打开来,全是日子熬出的甜头——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美么?
更妙的是,这字会跟着日子活过来。春上,柳条儿刚抽芽,嫩绿得能掐出水,人就说:“这颜色真美”——这时的“美”是湿漉漉的,带着土腥气。夏夜,蝉声混着穿堂风,摇着蒲扇的人眯眼道:“这声音真美”——这“美”是凉的,像井水沁过的瓜。
秋深了,糖炒栗子的铁锅一响,捧在手心的热乎里,那“美”是甜的、是焦香的。冬晨,钻出被窝,摸到晒得蓬松的棉被,贴着脸一蹭,“这触感真美”——这“美”是软的,裹着太阳的余温。同一个字,落在不同光景里,竟变出千般模样,像块老玉,经年摩挲,越看越有光。
其实,“美”字像根细线,串起那些容易被脚步踏碎的小欢喜。看见孩子扶起跌倒的老人,心里会蹦出“人真美”;雨天忘带伞,同事把伞塞过来,那句“谢谢”里裹着“情分真美”;翻旧书,掉出张卷了边的电影票,泛黄的纸上印着日期,那点“细碎的美”便悄悄洇开——是“美”字给了这些暖意一个名字,也让我们肯为一片落叶、一缕饭香,多停一停,多看一眼。
如今再提笔写“美”,手还是不自觉地把撇捺铺开。墨迹从纸面游过,两点如星,竖提如脊,末笔如翼——像在画一幅袖珍的春景:有光,有草木,有笑出声的人。原来这字打从造出来那天起,就揣着对日子的热乎劲儿,藏着对好光景的盼头。怪不得人人都说爱美,你瞧,连“美”这个字本身,就长得让人心头一软,值得人好好收着,当个念想。
【感谢看到这里,如果方便的话,预约一下下面的直播,期待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