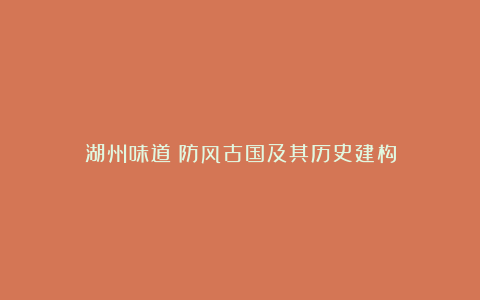“地裂防风国,天开下渚湖。三山浮水树,千巷划菰芦。埏埴居人业,渔樵隐士图。烟波横小艇,一片月明孤。”清代戏曲家洪升赋诗一首,形象地展示了防风古国及下渚湖的山水风光、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与民俗风情。
防风氏的文学形象
最早关于防风古国的记载,可追溯至汉代典籍。《史记・孔子世家》中“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防风氏作为上古部落首领的鲜明形象,同时也奠定了防风古国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防风古国的确切地理位置,源自于地方志书的记载。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吴兴西有风渚山,一曰风山,有风公庙,古防风国也。”此说法被后世地方志书广泛采信,清道光《武康县志》进一步细化“封山石室为防风氏居所”。
唐代以降,文献典籍对防风国地望的记载趋于具体。吴越国王钱鏐重建防风祠时所立《新建风山灵德王庙碑》,既载祠庙规制,亦确认防风山为古国核心地标,该碑被阮元《两浙金石志》、陆心源《吴兴金石记》等著录,成为地理考据的实物文献佐证。
综合这些文献记载,现代学界通过文献互证与考古发现,进一步锁定防风国范围,即是封山、禺山“两山夹一湖”的地形,它以封山、禺山为核心,横跨杭嘉湖平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防风氏率领着他的部落,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独特的文明。其所处的地理范围,恰好处于江南水乡的核心区域,这里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和人类居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防风古国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使其成为江南早期文明聚落的重要代表之一。
防风山作为防风古国的核心区域,至今仍留存着许多与防风氏相关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它们宛如一部部无言的史书,默默诉说着那段遥远的历史。现存的“封山十景”中,封山石室(蝙蝠洞)、百丈深潭等自然景观,与传说中防风氏的居所、治水遗迹相互呼应,还原了防风古国的历史场景。
封山石室,又名蝙蝠洞,雅号“封公洞”,《山海经》中称之为“大人之堂”。这里夏日冰凉,常年渗水,人入无汗,洞壁滴泉,水质清凉甘甜。道光《武康县志》载“洞中广容百席”,传为防风山王居所。石室后有蝙蝠洞,洞内栖息蝙蝠无数,大且红色。传说此洞深不可测,直通山下的下渚湖。封公洞冬暖夏凉的天然小气候,且无蚊虫苍蝇,是避暑纳凉的胜地,其神秘莫测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探访、题咏赞赏。洪升曾作《封公洞》五律诗:“松崖未及岭,石洞忽旁穿。泉滴四时雨,云通一线天。虫蛇盘土室,蝙蝠避炉烟。最是山僧静,袈裟正坐禅。”
百丈深潭,大小约一亩,深不可测,三面绝壁,高十余丈。崖侧俯视,惊险刺激。阳光直照在潭面,若无风不许游漾影可清点。传说这里是防风氏治水时留下的遗迹,其深邃的潭水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历史秘密。
除了自然景观,防风山还有许多人文景观,见证了防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唐代天宝年间,改“封山”为“防风山”,这一改名事件本身就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防风氏的尊崇和对防风文化的认同。
良渚文明是距今5300—4300年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学术界有说法认为,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可能起源于良渚文明。良渚文明晚期,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夏朝。
防风祠堂
学术界认为,防风国属于良渚文明的范畴,是“杭嘉湖平原区域性部落联盟”,而且存续时间正是良渚文明晚期。考古人员在下渚湖周边发现了密集分布的良渚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与防风古国存在的时期相吻合,显示防风国可能是良渚文明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区域性部落联盟,暗示了防风国可能是良渚文明向北迁移的过渡形态。
图腾崇拜是关联防风国与良渚文明的核心切入点。有学者提出“风字古从鸟,风姓表示崇拜鸟图腾”,指出防风氏“以居地与图腾为氏”的命名特征,而良渚文物中反山玉钺神徽下的鸟纹、福泉山墓鸟纹黑陶豆等遗存,显示二者共享鸟崇拜文化内核。“风与凤相通,防风氏即防地崇鸟之人”,这种图腾共性指向文化传承关系。
民俗学研究也提供了旁证。南朝齐祖冲之《述异记》载防风祭祀“奏古乐、吹竹如嗥、披发而舞”。现代民俗学者认为此为“越俗”核心仪式,而良渚文明遗址周边的吴越先民亦延续“断发文身”习俗,这种稳定的民俗传承暗合防风国与良渚文明的接续性。
生产技术的文献记载亦获考古支持。《浙江通志》载防风氏“以玉器换取青铜器”,而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钺等礼器群与“几乎无青铜器”的考古发现形成对应,据此推断防风国可能为良渚玉器文化的继承者。此外,防风传说中“教民耕犁、种植水稻”的叙事,与良渚遗址石犁、石镰等农具遗存形成互补,印证该区域早期农业文明发达。
更为重要的是,良渚文明北迁,主要因为生存环境恶化,最大可能是洪水,这与防风氏治水的传说相互印证。良渚古城外围100平方千米的水利工程体系,印证该区域“防洪为生存核心需求”,为防风治水传说提供史实背景。有学者提出“防风氏核心事迹为治水”,而下渚湖湿地“易涝地形”与防风国“以治水安邦”的文献记载高度契合。
防风古国是良渚文明向北迁移的过渡,这种说法更得到了考古遗址的印证。其中,蒋庄遗址作为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虽地理坐标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交界处,与文献记载的防风古国核心区(德清下渚湖流域)存在空间距离,但其考古发现通过文化属性、社会形态、传说印证三大维度,为防风古国的历史真实性与文明特质提供了关键支撑,成为学界关联二者的重要实证依据。
下渚湖湿地公园
防风古国与蒋庄遗址的核心关联植根于共同的良渚文化基因。防风国是良渚文明江南地域的延续性部落联盟,而蒋庄遗址则揭示了良渚文化向北扩张的重要轨迹,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玉琮、玉璧等礼器与良渚核心区反山、瑶山遗址的礼器制度一脉相承。
这种文化同源性在器物特征上尤为显著:蒋庄遗址黑陶壶上的猪形、鹿形刻画符号,与良渚文化常见的动物纹饰风格一致;带有“凸”字形祭台符号的玉璧,更是首次在明确地层中出土的精神信仰遗存,与防风祭祀中“敬天法地”的巫祭传统形成文化呼应。这类贯穿良渚文化圈的礼器与符号体系,是界定防风氏为“良渚文化后裔部落”的核心依据,而蒋庄遗址则提供了该文化圈边缘区域的关键实证。
更具深意的是,蒋庄遗址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含烧骨葬与拾骨葬),且部分墓葬存在“无首、独臂或随葬头颅”的特殊现象。考古学者推测其与“战争或戍边”相关,可能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这一发现与防风氏作为“封嵎之山守者”的文献定位高度契合。孔子称防风氏“守封、禺之山”,其“守护者”身份恰与蒋庄遗址先民的戍边特征形成互证。
另外,从空间功能看,蒋庄遗址“聚落外围水网与泰东河相连并通达长江”的地理特征,与防风国核心区“下渚湖湿地水利枢纽”的属性一致,均体现了“以水为生、以水为防”的生存策略。这种水利适应性不仅为防风氏“治水安邦”的传说提供了史实背景,更暗示良渚文化圈边缘部落与核心区在生产生活模式上的统一性,而防风国正是这类部落联盟在江南地域的典型代表。
所以,通过文化谱系分析构建了防风国与蒋庄遗址二者的关联逻辑。将其统一于良渚文明的视野之下,可以推测防风氏族群可能以德清为核心,沿水网向江淮地区扩散,蒋庄遗址或为其支系聚落。这种关联的本质在于,防风古国的研究并非局限于单一地理点位,而是以良渚文化为纽带的区域性文明研究,证明良渚文化圈的影响力已覆盖江淮东部,这为防风国“横跨杭嘉湖至江淮”的潜在疆域提供了考古支撑。
从时间线来看,防风古国是良渚文明部落联盟向夏王国过渡的重要一环。而解读这一环的关键在于“禹伐防风”。大禹诛杀防风氏这一历史事件,对早期国家的建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防风氏雕像
从政治层面来看,夏朝建立之前,大禹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其中以功绩授爵的分封制度改革尤为重要。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使得权力的分配不再仅仅依赖于出身,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的功绩和能力。这一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部落的传统地位受到了挑战,防风氏所在的部落便是典型代表。
据《尚书》等典籍零星记载,防风氏在当地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势力。他们长期以来依赖传统的部落制度,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对于大禹推行的以功绩授爵的分封制度,防风氏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态度。
大禹在会稽山召集天下诸侯会盟,这一事件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史书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因为时间问题而引发的悲剧,但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我们会发现这应该是大禹对不服从中央权威的部落进行严厉打击的一种手段。
这一事件标志着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的过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部落联盟时代,各个部落之间相对独立,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管理。而大禹诛杀防风氏,表明了中央政权开始拥有对地方势力的绝对控制权,这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通过这一事件,大禹成功地确立了“会盟”制度。这一制度成为了早期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义务和责任,加强了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诸侯们通过参加会盟,向中央政权表示效忠,接受中央政权的领导和管理。
另外,大禹诛杀防风氏,很可能跟防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在古代,水上交通相对发达,而陆地交通则受到诸多限制。下渚湖湿地的水域环境使得外来的军队难以大规模集结和行动,大大增加了进攻的难度。封山、禺山“两山夹一湖”的地形,更是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两山对峙,中间的下渚湖宛如一道天然的护城河,使得防风国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能够凭借地理优势进行有效的防御。
传说中,“百丈深潭”和“封山石室”曾是防风国的屯兵据点。百丈深潭深不可测,周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理想的军事防御场所。封山石室则是一个天然的洞穴,内部空间宽敞,可以容纳大量的士兵和物资。这些屯兵据点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防风国的防御能力,使其在面对外敌时能够坚守阵地,抵御敌人的进攻。
据有关学者研究,除了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军事据点,防风国还可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可能包括瞭望塔、烽火台等预警设施,以及壕沟等防御工事。瞭望塔和烽火台可以及时发现外敌的入侵,为防风国的军队提供预警,使其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壕沟则可以进一步增强防御能力,阻挡敌人的进攻。这些防御设施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为防风国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然而,防风古国的战略位置和防御体系,恰是夏族势力北上的重大阻碍。因此,大禹诛杀防风氏,正是其向北扩展、进入中原的被迫或者说是必然选择。最终防风氏被杀,防风古国随之消散,最终成为了夏王朝的一部分。
防风氏传说,作为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多元的叙事,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在这些传说中,防风氏的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特征。
诸如《史记》《论语》《山海经》等典籍记载,突出了防风氏“骨节专车”的巨人特征,使其形象充满了神秘的神性。祖冲之的《述异记》记载“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长子丈,其骨节专车。今南中民有姓防风氏,即其后也,皆长大”,进一步强化了防风氏作为巨人的神性形象。在这些描述中,防风氏高大的身形超越了常人的认知,使其具有了超凡脱俗的神性特质。此后,各类民间文学,对巨人形象进一步演绎,并将这种巨人形象与治水功绩相结合,印证了其神性传说的特征。
这种巨人形象的构建,极有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隐喻。孔子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而“守”或“神”应该是部落酋长。防风氏的巨人特征,实则是其作为“封嵎之山守者”的政治权威象征。在上古,“以体型喻功绩”的认知体系中,身躯庞大意味着掌控资源的能力与部落领导力。而“禹杀防风”事件更凸显了巨人意象的政治内涵。防风氏的“巨人”身份使其成为江南部落联盟的具象代表,大禹通过诛杀“巨人”首领,实现对地方势力的压制与王权统一,这一叙事被儒家典籍强化为“君权至上”的早期例证。
远古时期治水画面
当然,对于“巨人”传说,学界仍无定论,一般有“历史还原”与“神话解构”两种路径。“历史还原”者认为,巨人传说源于防风氏部落“身材较高且崇尚高大体型”的文化特质,结合良渚文化发达的农业经济,推测充足的食物供给可能支撑部分个体发育超常。“神话解构”者则强调,“三丈之躯”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背景下,儒家、道家为强化“王权合法性”而进行的叙事夸张,与《庄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大物想象属同一文学思潮。
或许,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防风氏被赋予了治水英雄的神性光环。在远古时期,洪水泛滥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防风氏能够参与治水并取得成功,这无疑彰显了他的非凡能力和神性力量。远古时期的英雄人物,会被先民披上神话的外衣,通过体型夸张实现权威神化、族群标识的叙事策略。
防风古国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不仅是上古部落文明的碎片化记忆,更是后世不断层累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其历史书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防风古国文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