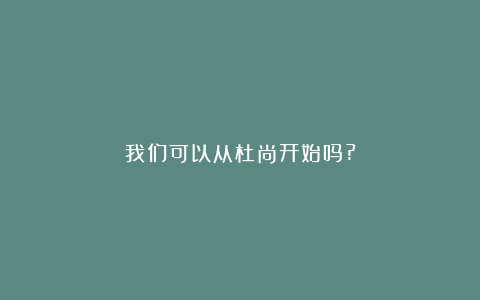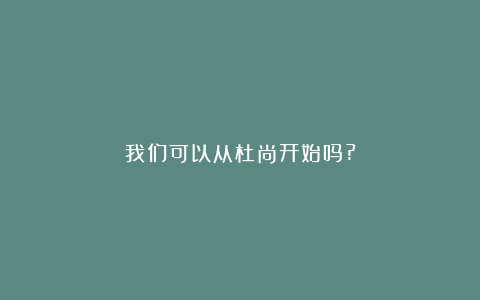|
本来人们认为语言可以直接表达思维。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的产生是一种偶然现象,一种游戏。没有一个能够通过语言去跟可指之物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后来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形而上学的终结。艺术作品的理解上,我要打一个补丁。在真理层面上,一旦有一个作品出来。这个作品跟艺术家的所思,或者说他的想表达,就已经分离了。
怎么打补丁呢?就是用诗人创作诗歌的方式。诗歌是用语言写成的。但诗歌本身又是超越语言的。他是对原有语言界限的模糊与超越。
所以艺术作品只有在隐喻的这个层面上才能够达到所思与表达的不分离。前提是,它本身是分离的,一旦有作品,它就分离。只有通过隐喻的方式才能指向同一性。
理论不能指导艺术,艺术更不是思想的插图。但是它(思想)提供了一种考察的高度。就是说一旦有作品出来就要带着一种怀疑去考查它只有作品的隐喻指向了不分离的时候,这个作品才成立(在杜尚的概念下)。
一旦你做出来一个存在之物。不管你是用雕塑还是先现成品的方式首先都带有这种分离性。只有你的作品有这种隐喻性的指向的时候力能超越这种分离,指向同一性。
西格的相册-Ludwig Wittgenstein
一旦你做出来一个存在之物。不管你是用雕塑还是先现成品的方式首先都带有这种分离性。只有你的作品有这种隐喻性的指向的时候力能超越这种分离,指向同一性。
思维与表达的分离是艺术这种创作方式不可逃离的命运。
首先作品出来先打个叉儿,然后再验证它有没有这个指向性,有这个指向性那就进入到这个这个线索里面,没有就排除掉。
首艺术家作作品,就是分离的,不然没有作品。一上来就是分离的,只有通过这种隐喻的方式,才有可能指向一个不分离的认知。杜尚用的是剥离的方式,这一点很智慧。维特根斯坦考虑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的几于年的形而上学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万物有一个原型(理念)。然后万物按照原型再有各种各样儿。先有一个椅子的概念。然后,人们再按照这个概念来造椅子。但是,那个原始椅子是一个纯理念,是不显形儿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套东西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个语言,一旦把语言挖掘出来之后发现。语言是没有指认能力。因为事物是在变化当中的,不断的变化的,它没有本质,就没法命名。
一个没有本质性的东西怎么可能命名呢?你没法儿抓住它,它一直在变的,瞬息万变的,从量子力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
包括对于“我”也是,我说“我”的时候儿。已经不是上一刻的那个我了。这是从真理层面去考察,不是从实践的经验上去考察。
所谓的隐喻性,就是将原来的那种固定性的,我们天然认为我手指可以指向石头的这个行为的合理性,顽固性把它松动掉。不是造出来一个能所的不分离,而是要通过瓦解掉能所分离,才能指向能所同一。之前有一个和朋友的争论。他总说常识性啊!谈艺术家遵从常识。
我说艺术家恰恰的是要破除常识。因为常识是一种我们天然认为正确的东西。艺术家能做的不是建立新的东西,而是去破除被我们天然接受的一些东西,一些理所应当的东西。在这个破除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新的认识。
艺术家: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所谓的隐喻性,就是将原来的那种固定性的,我们天然认为我手指可以指向石头的这个行为的合理性,顽固性把它松动掉。不是造出来一个能所的不分离,而是要通过瓦解掉能所分离,才能指向能所同一。之前有一个和朋友的争论。他总说常识性啊!谈艺术家遵从常识。
可以把杜尚理解成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方式达成的。不能化1为2,也不能归2为1,而是通过破这个2。通过否定这个2,或者松动这个2来指向那个1。这个1是被指认出来的,而不是塑造出来的。
艺术创作里有语言,一旦有语言它就是分离的。因为有媒介。所谓的不分离的状态,就是不二,这是佛教的概念。
也可以说,艺术品的产生天然具有一种分离性,思维与表达分离是它的天然属性。具体谈,比如杜尚的小便器,过去说一个雕塑家,我创作一个苹果的雕塑,就是要雕出来一个苹果,作品就是指向这个苹果。它也可能指向宗教创世的故事,亚当夏娃。叫象征主义,这都是对常识的回应,对于共同文化背景的认同。
当杜尚拿出小便器,又命名为《泉》,它就松动了原有的认识。他的艺术品的小便器和现实中的小便器之间的必然的联系被松动了。显然它不是象征主义。他是通过命名的方式(以前这个权利是 God专属的)创造出来的。而象征主义是文化共识,比如说太阳代表真理,夜晚代黑暗。
杜尚破除了原来的,固有的这种联系。松动了原有的思维与表达的必然性。通过否定性的方式指向了合一,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
其实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特别好理解。有一句诗叫:我赶着一群羊,就像赶着我自己。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但是给人产生的含义(言外之意)是超出语言范围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松动了原有的语义以及语言所指的必然性带来的明确性和确定性,但是它达成了诗意上的深刻性。
这种创作行为不一定是通过哲学思辨,它更是一种直观,这种直观是超越文化背景和常识的。是更原始的一种感性,未分之前的感性。
其实对于诗人创作模式分析,在诗歌研究中已经达成一种共识,有神秘性。米沃什曾经写过,是上帝执笔!
当然也有主动的部分,有能动的部分,还有理性的部分。最终是混合的,混沌的,神秘的。
一方面要理解杜尚的理性和创造性。是积极的,绝非虚无主义的反方向的去谈这个问题:杜尚不是构建了什么东西。不是通过创造了,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说他通过瓦解了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达成的。比如他通过否定性的方式瓦解掉手工性。然后通过匿名性,瓦解了作者性。通过非艺术家制作瓦解掉了原有的艺术家“我”。
一般来讲,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一定是要有一个由艺术家造出来的艺术品,这是根深蒂固的。我是从强调否定性的层面去考察他的。不然观念艺术就解释不通,因为古今中外所有艺术的表达都包含观念。杜尚的伟大或说他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他既有正面的东西,有理性的东西,有创造性的东西。也有否定性的东西,去蔽的东西。
而且我在我看来,他的否定性起到了积极的,特别坚决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他与之前的所有艺术家的根本区别。
艺术家: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
塞尚还是构建,还是康德那一套。人类的强悍,理性的必胜。人类用理性来改造界,成为世界之主的这么一种心态。而到杜尚这儿,已经变成一种退让,匿名性,去艺术家性。把艺术家拉下来。本身也包含着后来波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层面。因为没有技术壁垒。但是他恰恰强调,艺术品可以脱离原有艺术品的定义。一个小便器(工业现成品)也可以是艺术品。他通过剥离的方式来,通过否定的方式,通过退缩的方式“让”出来一个新的空间。而不是“抢”出来一个新的空间。也不是什么以退为进,成语一说容易误解。
这样的话,杜尚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超越了之前的艺术家。之后的艺术家也不是说比杜尚多差,而是没有办法超越杜尚的这个维度。
就像塞尚出来之后,才超越了达芬奇的维度。塞尚之前的所有艺术家,几乎都没有办法逃离达芬奇所定下的这个边届。只能在边缘去试探。只有到塞尚这儿,才彻底破除了那个东西。
塞尚的现代主义是如何击败达芬奇的,我在小红书的视频里讲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看到很多人现在谈观念艺术,一会观念注入绘画儿了,一会儿观念艺术注入雕塑了。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所有的艺术品都包含着观念。现成品之后,所谓的观念艺术之所以成立,是通过摧毁艺术家手造之物的方式,让观念“脱离”出来的,而不是说单拎出来一个东西叫观念。观念本身是不可显现的。没有办法做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观念。只有去除原有的这种联系之后,“观念”本身才自然而然的显现,是通过否定的方式。西方是有这个传统,叫去蔽,不是说呈现一个新的真理,而是把覆盖在真理之上的这层面纱揭开,让它自己显现出来。
我所谓这个反对也不说现实意义上的反对。他不用原有这套方法论了。还能成立是艺术品,就证明原来那个方法论自然而然被弃用了。过去都骑马,现在开汽车了。比谁骑术高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弃用的过程等于摧毁了它。
喜怒哀乐的表达不用通过媒介,而是身体的直接反应,是比较接近不分离的状态(当然还要考查肉身与思维的关系,我们先放一边)。使用语言之后就分离了。因为使用语言就出问题了,通过语言来链接思维与表达的必然性被切断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指出了这个问题,名言的不可能。
有一些声音艺术实验,实验舞蹈试图回到前语言的状态。吼叫,喘息,各种类似膝跳反射的动作都是一种尝试回到语言之前。
杜尚后来大段时间去下棋了,非常有可能是主动性的退场。不是说做不出来,而是说他觉得认识到这一步(仅以观念呈现艺术)之后再作就没有意义了,只是重复而已。因为观念显现是一次性的,只有形式才能不断幻化和演变。
塞尚打开一扇门(现代主义),好多人进来。而杜尚是打开一扇门,随手门又被带上了,杜尚自己也把自己关里面了。用赵本山的话讲:我们也进不去,他也出不来。
抛开我们今天的当代艺术仅仅是对杜尚的重复或者拙劣的模拟而已。尼采死前品留下遗书要销毁作品;卡夫卡对于作品遗稿的销毁意图都是主动的退场。这些行为可以连在一起去理解。
艺术是多义性的。就像诗歌的多义性和精确性之间,既是矛盾同时又是整一的。这一方面只有艺术内部(非真理层面)是可以接纳的。
杜尚的“观念显现”,不是指认出来的。是通过剥离手工性’之后,思维的显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面我们还不能谈“思维我”和“手工我”,因为思维我是一个主语性的词汇,而手工我是一个主体性的词汇。这两个词汇同时出现时就会产生范畴范围的混用。可以这样理解,杜尚通过去除手工性,铲除了艺术家我的存在根基。然后又通过命名建立了一个新的艺术家我。这个新的艺术家我,是不需要之前艺术家自身的手工性参与的。通过剥离包含思维的手工我,剔除了手工之后,仅留下一个思维(显现)。这个思维暂时还不能叫思维我,因为当我们谈到思维我,和手工我的时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手工我本身内涵思维。我们是用思维在指导我们的手工来进行实践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思维是手工我的指导者,而这个指导者是一种形式,而不是手工我的一个实体的部分,剔除手工性之后,并不能留下一个思维我。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手工我,一个思维我。就产生了范围的混用。当然,从艺术实践内部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杜尚通过去掉手工性,显现出来一个思维我,而这样的一个思维我其实指的是艺术家的我,也就是艺术家的思维我,顶替原有着本来就包含着思维的手工我。当我们说杜尚通过构建起来一个新的艺术家的思维我,而代替了艺术家手工我的艺术家的手工。这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学术层面上是并不严谨的。
这样看来杜尚选择了现成品,不是绕道儿的方式,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方式,有强烈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艺术还是有边界的。到杜尚这,已经剥离到一个无可剥离的地步,几乎没有办法再前进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再剥离观念,观念是剔除不出去的,它是夹带。而且它是不可显形之物。能够剥离的东西只能是内包于一个可显现之物。杜尚的剥离是在关系上的剥离。仅真正意识到杜尚的问题的时候,意识到他的高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成功”了。(朋友圈似乎很流行这个词)杜尚为什么后来不作艺术,也好理解了:剥离的方式是一次性的。没有必要重复,重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抽象性的,观念化的,指向性的问题。而不是像语言层面的革命,推进,可以不断的深入,前进。现代主义就是不断前进,而且设立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蓝图,后来变成前提。当代哲学认为这个东西不存在,人是有限性。理性,科学都是有限的。
现代艺术中重复问题确实很麻烦。现代艺术之前你画的像拉裴尔一样,那你就是大师,就是拉斐尔前派。因为那时的艺术是以技艺为前提的,就是杜尚的所说的艺术家的手工性。而塞尚以后,这个可重复的技术性的合法性被取消了。当然也不得不取消,因为摄影术来了。在我的视频号里有讲,大家可以去看。到塞尚这,艺术家获得了主动创造绘画内部世界的权利,不依附于客观实在的视觉真实性。这个艺术家的主体我就被建立起来了。它的要求是,必须是发明语言,不能重复,必须前进。因为重复就不自由了,不先进了,也自然不是现代艺术了。这一点上,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对艺术家的要求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是积淀,一个是创造(反叛)。古典艺术要求的是你要掌握一个秘籍,获得一种能力,有一个最高标准,接近它。你离这个最高标准越近你的能力越强。
有一本书叫《我的名字叫作红》,讲的是细密画,谈的都是要靠近古代大师,不能有我。而现代艺术是要求你的艺术语言的构建或发展。共同性的东西也有,但更重要的是考察你的贡献性,有没有推进,有没有仅属于你的艺术家的签名。
如果从大时代的角度去考虑,有一点儿悲观,或者神秘主义的讲法。就是说这个真理是闪现的,它就闪一下,马上走,包括神的降临也是以闪现的方式。人类的认知可以一直发展下去,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进,不断进步。这是一个设想,只是一种期望。“人”能通过理性征服自然是被催生出来的雄心。
跨时代的人物是很难超越的。至少很难从他的纬度上超越他。
抽象表现主义也并没有彻底超越塞尚。它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面貌,加入一些新的内容(情感)。杜尚也是一样,在他的维度之下,他相当于是数学当中的公理(前提)。
然后安迪沃霍尔,博伊斯这些是定理。定理是需要求证的。公理是不能求证的,它是作为前提存在的。但是真正的数学上的革命或者物理学上的革命,是对公理的重新定义。非欧几何对平面几何的突破是推翻前提然后建立起来的。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一定是意识到杜尚的纬度在哪;杜尚到底在说什么?才有可能……不要说超越杜尚,才有可能对杜尚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但是如果对这个纬度没有认识,那后面的问题就是稀里糊涂一大片了。除了考察他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外,杜尚也是艺术史中的杜尚,才有可能对杜尚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但是如果对这个纬度没有认识,那后面的问题就是稀里糊涂一大片了。除了考察他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外,杜尚也是艺术史中的杜尚,是一个需要不断被构造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现实人格,还有一个历史人格。这个历史人格是后来的理论家,哲学家,以及艺术家通过讨论,思辨,艺术实践对他的重塑。
其实博伊斯也没做什么,安迪沃霍尔更不行,就弄了一个布里诺盒子,蹭了一下艺术史热度。博伊期的社会雕塑无非把观念性的东西,不可见的那个东西和现实社会结合了而已。“社会”成了他的材料。至今在各种双年展文献展上我们看到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命题的转向与此有关。波伊斯影响了这个部分,以身份问题,社会问题,环保问题,女权问题,政治问题介入遗书。是这个脉络。还有他影响了表演艺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表演是真的表达,比如演讲和政治宣言,不是演的。后来很多行为艺术家是表演大于表达,一个是有点隔靴搔痒,有一种虚假和矫揉造作之嫌,比如阿布拉莫维其就挺典型的。
博伊斯不是一般的艺术家。他的认知能力,创造力肯定是不差的。有一种可能是博伊斯意识到了杜尚触碰到艺术的边界了。不能往外再迈一步。那一步再迈出去就是上帝的事情了,人解决不了。
博伊斯是通过撤回的方式,到人间。整个后现代哲学转型也是如此:不关注形式上的问题,语言学也不搞了。就是齐泽克这一套。社会学改造,女权,政治问题,身份问题,人类学,伦理学,技术这些具体的人间议题。
但博伊斯在方法论上,在根本问题上没有超越杜尚一点儿,他还没迈出杜尚画下的这个圈圈。
劳申伯格通过现成品指向了消费主义,还来过中国。基弗是通过现通过现成品指向了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这都是杜尚语言模式下的应用。并没有逃出杜尚的模式,还是在这个模式下的运行,以这套方法在各个领域延伸而已。
各个领域的大成者都在谈关联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不管是塞尚,康德, 包括牛顿。然后杜尚他和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物理学家(如霍金)。还有博伊斯与齐德克,都是同时代的最高层面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追问。艺术家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如果根据印度古哲的想法儿,“我”存不存在都是一个问题。无独有偶,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之诺。他提出了海上行船的悖论,也叫忒修斯之船。他假设一条船在海上行走,行走了很长时间,然后不断的修,不断的换下坏掉的部分。最后再把它换下来的部件儿重新组装成一个船(全是他原来的部件),那到底是修完的这个船是它本来的船,还是用他的原有部件组装的那个船是它自己。造成了一个名言的悖论。“我”也是一种名言,当我说“我”的时候,我也在变,在不断的变化,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刹那的变化,而变化的东西怎么能被指认(命名)呢?
我觉得有这个角度,考察现成品的去工“我”的层面。杜尚是通过去除手工性,让思维显现。他不是直接指认思维。因为手工我是包含着我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思维。它在实践中指导艺术家的劳作。这个思维(意识)并不是一个可以指认的实体,不如说它是手工我的认识模式。其实说思维我是不准确的,并没有一个与手工我对立的思维我。之前我们说了,思维是内涵与手工“我”之中的。同时被剔除思维的手工“我”也不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从艺术家诞生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艺术家都有一个思维或者朔观念融化在手工我之中。但直到杜尚的出现。他通过剔除艺术作品当中的手工性,让思维显现出来了。我们说杜尚直接通过思维,也就是观念表达了艺术或者说艺术可以是观念的直接表达。当我们说思维我与观念我的时候,也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可指认的对象(思维我)。
有可能说去除我的层面,才有可能在杜尚的思考的范围之外。但是问题就在于,一旦去除我之后,还有没有艺术?那就没有艺术了!因为“我”都没有了,哪还有艺术?
丹托与安迪沃霍更紧密一些。丹托所谓的终结论是指艺术进化到一个不可能再进化的地步,已经是一个完成时了。我认为,这是以不断剥离的方式进行的。到杜尚这已经几乎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像一个脱衣舞女,表演到达高潮时段后就结束了。她已无所抛了。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抛掉了。唯一能做的就是谢幕下台。塞尚把客观世界的对照性抛掉了。然后杜尚又把艺术家的手工性抛掉了,仅剩一个观念的我。到这个地步就无所能抛了。不可能把思维抛掉。因为思维是通过去手工剥离出来的剩余(显现),它不是一个可指之物,自然不可剥离。从这个结论去考察,博伊斯是以撤回的方式(添加内容);而不是现代主义那样以前进的方式去发展。不是说之后艺术就没有意义了。还有很多艺术家在作艺术,艺术家一直存在,艺术世界也一直在运行,只不过在进化逻辑上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其实触及问题几乎等于解决问题了。明了的情况下总是比稀里糊涂的要好。
达芬奇统治了西方绘画300年,大卫霍克尼说是400年。杜尚才多少年?如果人类把意识上传到网络后,只通过意识存在于此,不通过肉身存在于,这个新维度的直观经验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这个经验很重要。为什么说几百年才出来一个达芬奇?然后再几百年才出来一个塞尚?之后五十年出来一个杜尚,我们发现这个进程其实是越来越快的。也有朋友善意的指出,我这样的想法是单一线条的,历史进化论的认识。这一点我也承认,只不过如果不在逻辑线索上把达芬奇,塞尚,杜尚联系起来。仅从艺术家个体去进行考察,那仅是艺术史上的零碎考察,对整个历史进程的认知是无法达成的。大多数时候,个人的能力很难能够左右时代的局限和赋能的。所谓的AI艺术,不是这些艺术家用一个AI运行一下产出个作品,当成一种手段(还是技术化的手工性)。而是AI会带来一种处境。什么样的处境?AI可以脱离肉身而拥有“意识”人可以抛离肉身而存在。很多科幻小说和电影都有这样的描述。当这个新的处境降临的时候,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前所未有的,新的维度有可能打开。这方面艺术家的想象力太落后了,把一个艺术品放倒火箭里点上天,就是和宇宙发生关系了?并没有!借助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力量其实是自身的不自信,狐假虎威嘛!反而失去了艺术家思维的创造力和雄心。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艺术创作,特别是杜尚之后不是比谁胳膊粗,你胳膊粗能比过巅峰时期的希特勒吗?
比如AI创造了一个艺术作品,在认知这个艺术作品之时,还是要有“我”(观看者)的介入。谈到自然的之美的自然性(非人性)还是人在观看,欣赏,下判断。《三体》里面讲三体人是非碳基生命,没有语言。思维和思维之间直接交流。他们的交流是没有任何障碍和遗漏误解的,同时三体人不会说谎。人类的这方面有长处,也有短处。语言的不确定性才有诗歌。人类语言的分散性(巴比别塔),不准确性,弥散性多意性是语言的局限也是诗歌的前提。三体人很可能是没有艺术的。
思维的“我”是不能扩散的,一旦扩散,就是等于回撤了。我们能看到国内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从抽象撤回到叙事,从抽象撤回到意象。装置作品中从观念撤回到雕塑(现代主义的范畴里)。这种例子很多,大众看不懂,还以为这是对于原有概念的延伸。我在小红书发过一篇文字帖,叫《我们对装置艺术本身有一种误解》,是与朋友聊天整理出来的两篇小短文,谈的就是这个。相当于读书发明了一套理论规则,然后大家用这种理论规则来指导实践行动。这只是真理的实际应用。
主体性的我不在的情况下,就不没有必要问了,就没法儿问了,和杜尚的方法一样,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杜尚还是保留一个余存的观念的艺术家的我。
我觉得几乎做不到一个无我的作品。但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这个维度存在。你再去有“我”的作品还是不一样的。
杜尚是两步走,首先杜尚通过去除手工性消灭了原有的艺术家我(村尚之前的艺术家我都是通过手工我来实现的)。第二步他又通过命名,重新建立了艺术家的主体我。先把原来的主体消除掉,又新建立起一个主体。这个新的主体性就是说,只要是我提供一个观念独立存在的例证,就可以直指艺术,我就可以是艺术家。表达即是观念,不再需要通过艺术家本人的手工完成。
这么看来,杜尚的去手工跟命名之间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两步走,没有一步费棋。
杜尚去手工就是绕开“形式”直抵观念。当然我认为他是通过剥离的方式让思维自身显现出来的。
关于命名,也可以简单的谈一谈。在杜尚之前,任何人都在命名。领养一只狗,给它起个名。父母新出生一个小孩,给他起个名。画家画个画起个名。这都是命名。这并不是杜尚意义上的命名,他是通过指着一个小便器,然后说这是《泉》。这个泉的名字与安格尔的绘画,与男性特征是相关联的。类似一个艺术史小玩笑,一个语言的错意,看似的四两拨千斤。这就是一个玩笑。我曾经看过一个哲学家讨论玩笑是如何达成让我们笑的效果的,就是由语言使用过程当中的错意产生的。这个命名非常重要,因为在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世界里面,命名是上帝的专属,圣经开篇:上帝说要有光!这个上帝“说”就是命名。就像我之前谈过塞尚是绘画世界的上帝,他抛开了现实也界的客观性再现(艺术家用模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拟真)。塞尚把艺术家从这样的方式当中,也就是从自然当中解放出来了。所以塞尚是绘画世界的王者。杜尚是通过命名这样的一种非日常意义上的语言错意的动作使得艺术家再次如同上帝一样,具有了命名的权利(意念到现实)。当然,杜尚是以艺术的方式。
如同古希腊哲学家提蒙对巴门尼德的赞美诗,说巴门尼德把理念从表象世界拯救出来了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杜尚把艺术家的观念我从手工我中拯救出来了。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杜尚是有严密性的,也有深度和巧妙。这也就是至今人们还在围绕着杜尚,还无法超越杜尚的原因。看来最一流的文本是有这个承受力的。
我们今天讨论杜尚,并不是把杜尚当成一个艺术家个案来进行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谈的杜尚并不是在谈一个在上个世纪法国生活的爱下棋的艺术家老头。而是要赋予他一个历史人格。我们这样谈论他的时候,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就是在对事实作品进行严格考察和考证的前提下,还要对他的重要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过滤掉那些不符合这条线索上的作品或者是杂事。因为杜尚身上具有太多复杂性,调侃,反叛甚至是捣乱的气质。在他对自己作品的谈论过程中也鲜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所以谈论艺术史人格的杜尚,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及阐发,是要讨论杜尚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认识的起点,或者是说发展的起点。当然也可能是无法迈出的起点……这都没有关系,首先我们要自明。从这一点上来看,理解,阐述,重构杜尚并不仅仅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更关于我们将走向何处。
孙策,艺术家。’会’画小组联合发起人。 1982年生于沈阳。200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
重要个展: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今日美术馆,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国美艺术基金会。作品曾于:何香凝美术馆, 山东省美术馆, 喜马拉雅美术馆,筑中美术馆, 雅昌当代艺术中心;拖迪( 意大利),新加坡,首尔,仁川,台湾等地展出。曾获:新锐艺术奖,Artand 年度杰出艺术家奖,新星星十周年艺术家奖。讲座:分别于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高校举办学术讲座。主要收藏 :广东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神州数码集团,华为集团,希拉里教育基金等。(个人):郭为Maria夫妇,董国强先生,张锐先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