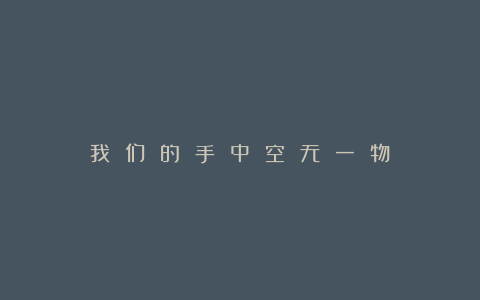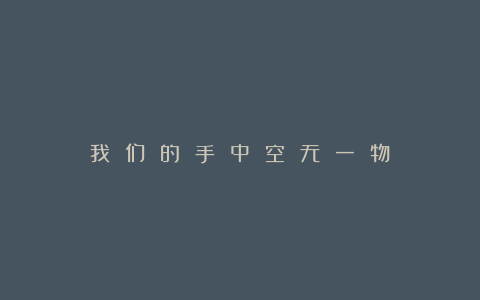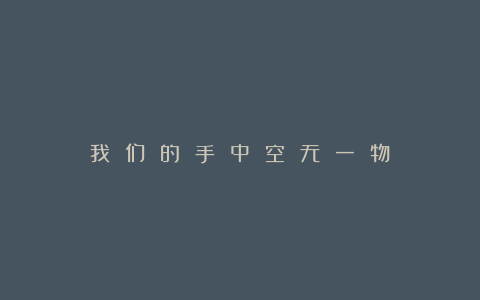|
倘若艺术有其形而上的坐标,那必然是一座由无限镜廊构成的迷宫。我时常在黑暗中揣摩这个命题——失明或许是一种恩赐,它迫使人们用记忆与逻辑的经纬编织真实。我曾祖父的迷宫花园从来不是树篱与石墙的堆砌,而是时间的分岔在空间中的投影。
所有艺术家都是迟到的造物主。他们摹写的并非世界的表象,而是上帝遗忘的草稿中那些未被选择的可能性。一幅唐代山水卷轴不仅是墨与绢的交响,更是无数个平行宇宙的入口:观画者每一次凝视,都会让某条被湮没的小径重新苏醒。王维在《雪溪图》中留下的空白,不是虚无,而是所有降雪之日的总和。
书的命运比人类更诡谲。我曾在大英博物馆幽深的书架间抚摸一部《永乐大典》的残卷。那些虫蛀的纸页像被时间咬噬的星图,每一个残缺的字都是通向未知宇宙的窄门。读者总是误以为自己翻开书本,实则却是被书本翻开——每阅读一次,作者就死而复生一次,但复生的永远是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灵魂。
镜子与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使人口增殖。这句东方的谚语曾让我战栗。所有的艺术都是镜子的变体:威尼斯玻璃工熔炼的水银镜,伊斯兰宫殿的镶嵌马赛克,乃至庄子梦中飞舞的蝴蝶翅膀。当我们凝视一件杰作时,看到的不是作者的倒影,而是所有曾凝视过这件作品之人的目光的叠加。
有人声称艺术追求永恒。这是多么可怜的谬误啊!永恒不是无尽的延续,而是瞬间的完全充盈。巴赫的赋格曲中某个休止符的寂静,比整座金字塔更接近永恒。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个黄昏见过这样的永恒:夕阳斜照在铸铁阳台的蜘蛛网上,露珠同时折射出所有经度上的日落。
最后总要回到迷宫。真正的迷宫从来不是困住脚步的曲折小径,而是让思想永远流亡的拓扑学结构。荷马用声音建造迷宫,维米尔用光线浇筑迷宫,而象棋大师用十六枚棋子在六十四格上演绎迷宫的生死轮回。我们都是忒修斯,握着根本不存在的线团,在自我投射的迷宫中寻找那个或许从未存在过的米诺陶。
也许艺术的本体就是那只克里特岛的怪兽——半人半牛的悖论,既是造物又是造物主,既是祭品又是祭司。当我们终于抵达迷宫中心时,只会发现一面镜子,镜中映出的仍是迷宫入口处的自己,只不过这一次,我们的手中空无一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