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五所学校里上过学
六十多年前,我曾在唐河县源潭公社、城关镇和城郊公社的五所学校里上过小学。
一、在张岗学校上一、二年级
1957年秋,张岗学校开学的那天上午,我去学校报名。负责登记的是位女老师,三十来岁,和蔼可亲。我的前边有一个男生和一位女生。老师问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回答:“王铁头。”“谁给你起的名字?”“我两岁时在大路上玩,不小心被牛踢着了头,又撞在拖车上,但我的头并没受伤,庄上人说我的头结实,就喊我王铁头。”
“你哥叫什么?”“王天义。”“我给你起个学名,叫王天祥,中不中。”“中啊。”老师又问女生叫什么。女声回答说叫董二盼。“你一定还有个姐姐,她叫什么?”“董富兰。”
老师笑着说:“你母亲一定盼望着再给你要个弟弟,所以给你起个二盼的名字。这样吧,我也给你起个学名,叫董桂兰,你同意吗?”女生高兴地回答:“我同意。”(大安庄王天祥、董桂兰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当我报上我的名字后,老师说“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有新中国公民的含义。”听到老师的赞扬,我很高兴。登记后,我交了5角钱的书杂费。老师给我发了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本练习簿。从此,我成了张岗学校的一名小学生。
负责登记的老师叫赵春芳,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她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的语文课。她的语文课教得很好,我们都爱学语文。
那时的语文课文既简单易学,还富有教育意义。
如《太阳山》,教育我们不能贪心不足。
《狼来了》,教育我们不能撒谎骗人。
《小猫钓鱼》教育我们办事情要专心致志。
《狗公鸡狐狸》教育我们偏听偏信会吃大亏。
那时的许多课文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出来。
在这两年里,印象深刻的还有高清林老师。他是学校的校长,并教我们唱歌。我十分爱上高老师的音乐课,至今我还能记住并能唱出来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歌唱二小放牛郎》《高高的兴安岭》《春天在哪里》《小燕子》《找朋友》等等。
记得在一次师生大会上,高校长列举了某些学生辱骂老师、殴打同学的违纪事实后,十分气愤地说:“这些学生经学校多次批评,仍屡教不改,真是球呲哩!”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高校长望着大笑的学生们大声喊道:“笑什么笑,这就是球呲哩,球呲哩!”
学生们都认为高校长说的是赖话,经传播,“球呲哩”成了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我将此事告诉了俺村最有学问的合章叔,他听后说:“高校长一定说的是岂有此理,只是说得快了,你们听成了球呲哩。”
看来,的确是学生们误会了高校长讲话的用词。
二、在龚岗学校上三年级(秋期)
1958年秋,源潭地区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集中全民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一平二调,迁村迁户什物大搬家。我们斋公桥村被定为“青年场(队)”的试点,要求没有45岁以下男劳力的人家,一律搬迁出村。我家只好搬到东仝庄我大姨家居住。我以为这也有好处,仝庄紧挨张岗,我上学能少走二里路。哪知上级又有指示,让张岗学校、春坡学校、蔡庄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一律去龚岗学校(联校试点)上学。
只有9岁的我,只好挑着稿荐、被子和学习用品,徒步五里路到龚岗学校上三年级。
那一期是怎样学习文化知识的,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学了很多紧跟形势的歌谣。如“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万丈高炉平地起,钢铁产量顶呱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翻一丈三,粮食堆成山。”“唐河县,不简单,出了个模范牛桂莲,棉花亩产一万三!”
我曾到龚岗村的东北地看三个大塚子(后来听说是四朗塚)。
我们常去棉花地里砸棉秆皮(听说是用来造纸或织麻袋的)。还曾去蔡庄村运过萝卜。入冬时下着雨雪,我们去红薯地里扒出红薯运回学校(当时的劳动力都被派到外地修渠筑坝,无暇顾及秋收)。
记得最清楚的是去车厢店村帮助摘花生。学生在摘花生的过程中,常常剝些花生仁填在嘴里。刚开始专挑大的饱满的吃。不少同学吃得肚胀、泻肚。后来有了经验,专挑半干的秕花生吃,又甜又香,还不会肚胀拉肚子。
那时学生们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免费就餐。伙食基本上是高粱面馍,苞谷糁稀饭,萝卜白菜,到后来以吃红薯为主。大锅蒸熟的芽子头红薯,面的噎人;节子红薯又软又甜。特别是大锅里的蒸红薯水,放凉后像现在的果冻,十分好吃。
三、回张岗学校上三、四年级
1959年春节过后,上级通知龚岗不办联校了,学生一律回到原来的学校学习。于是我回到张岗学校上了三年级(春期)和四年级(秋期)。
三年级期间,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按部就班地开展。我能够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所以语文和算术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犯了一次错误,至今想起来仍感到很惭愧。
那是在一个下午的自然课课堂上,我心血来潮,在课本的空白处用铅笔画了一个弯着腰、戴着草帽、吸着旱烟的老汉,我的同桌看到后,把课本和铅笔要过去,用铅笔在老汉的烟袋锅上边画了许多不规则的小圈圈,直通老汉的屁股后。我一见这创意,竟旁若无人地笑出声来。引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看向我,也引来正在讲课的郑古胜老师到了我身边。他看到我的这幅杰作以及刚才扰乱课堂的表现,十分恼火。
下课后,他将我叫到他住室批评我,而我却还想着那老汉吸烟的烟气飘到屁股后的画面,禁不住又笑起来。郑老师更恼火了,瞪眼看着我大声说道:“咋,你还笑,今天我不把你嚷哭,我就不姓郑!”我一听这话,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就是不哭,看你还姓郑不姓郑。他训斥我十多分钟,我并没哭。后来校长找他有事,他出去了。等一阵子,我见他没回去,就偷偷地溜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于是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找到郑老师认了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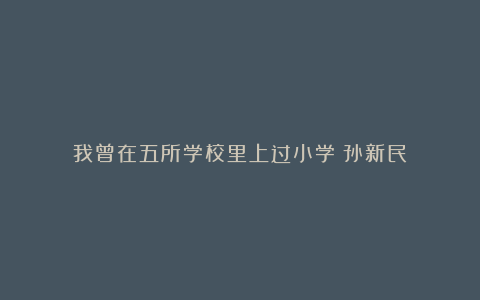
上四年级时,斋公桥村的青年场(队)也已停办,我家又搬了回去。那时的一日三餐,都到队里的公共食堂吃饭。只是质量越来越差,数量越来越少。入冬后已经吃不上馍了,后来连红薯也吃不上,只能喝稀面汤。再后来,葱花儿茶。在这种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哪还有心思上学?为了活命,只好到野地里挖油菜根,剜野菜(灯笼棵、面条菜、毛妮菜),掐豌豆秧。拿回家偷偷地用瓦盆瓦罐煮煮充饥(那时队里的干部决不允许群众私自做饭吃)。
村里除了队干部、司务长、炊事员及其家属外,群众都是忍饥挨饿,面黄肌瘦(一天吃一两,饿不住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住炊事员。就是那时的口头禅)。
因此,四年级的下半期,我基本上没有去上学。
四、在唐师附小和野地里上四年级(春期)
1960年过罢春节,为了躲避饥荒,我父亲央人托己,将我家搬迁到唐河城北二里地的史庄村居住。该村用麦秸在榨油厂换回许多芝麻饼,在食堂里加水加葱加盐后,用大锅蒸成饼干饭,群众每人每顿可分到2至3两。由此我们全家摆脱了忍饥挨饿的困境。
搬到史庄后,我到唐河师范附属小学(现在的唐河三小)读四年级。班主任姓夏,二十来岁,十分严厉,从来没见过他有笑脸。每天第一节都是他的算术课。凡是迟到的学生,他不问原因,都让你站在教室外,下课后还大声训斥。对犯错的学生,他常常揪耳朵,抓领子。我曾两次受过这样的惩罚。一见到他,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一个月后,我背着全家刻意省下的一提兜晾干的饼干饭,经七里沟,趟泌阳河,走王湾东,过袁庄马埂大安庄,送给我住在仝庄村的大姨充饥。第二天我原路返回。来回七十多里路程,累得十一岁的我筋疲力尽。
第三天(周二)早饭后,我背上书包去上学,路上心里总是害怕,不知道这旷课一天会受到夏老师怎样的惩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快到学校时听到了上课的铃声,看来又要迟到了,更是害怕。干脆不去了,等下午再去吧。到下午还是害怕,等明天再去吧。就这样,每天在惊恐中逃学,在野地里消磨时光。到放学时装模作样地跟着同村的学生一起回家。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常常躺在沟边的草丛里看蓝天白云,蹲在大树前看蚂蚁上树。我曾在麦地里捉过刚出壳不久的鹌鹑,曾跳到水坑里摸过大螺壳,曾到破旧的菜庵里躲避风雨。我也曾翻开语文课本阅读里面的內容,也曾低头沉思,对将来何去何从产生难言的惆怅。
终于在麦收之后,母亲从本村学生那里得到了信息,发现了我的行踪。挨了一顿狠揍,做了永不再犯的保证,总算得到了母亲的宽容。
后来,母亲和我找到在唐师附小任教的女老师李英勇(娘家住张岗学校北隔墙),让她领着我找到校长说明了情况,请示校长解决我上学的问题。校长十分干脆地对我说:“本期快结束了,你就不用再来校了,秋期留级,还上四年级吧。”
五、在三里王学校上四年级并考入唐河一小
1960年7月,我家搬到城郊公社刘马洼大队的马庄村。秋期,我到马庄村东南二里的三里王学校上四年级。这所学校很简陋,每班两间土坯草房教室,桌凳破旧。但老师们都和蔼可亲,从没有体罚学生让学生站教室门外的现象。他们教课非常认真,对学生的算术作业和作文,常常当面批改,当面纠错。我在这里上学感到十分轻松愉快。由于刻苦勤奋,我语文和算术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1961年6月份经过升学考试,我被城关一小录取为五年级新生。
秋期开学,走进城关一小,看到偌大的校园,宽敞的教室,整洁的桌凳,我十分高兴。我被分到五二班学习。通过一周的上课,体会到班主任和蔼可亲,教语文算术的老师教学方法得当,让学生听得懂,学得会。课堂上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深深地感到这所学校,的确是全县最好的学校。我为能在这里上学而深感荣幸。
当年的十月份,源潭地区的经济形势大有好转,群众的温饱有了保障。在此情况下,我家又搬回了源潭公社张岗大队斋公桥村。
六、回张岗学校上五、六年级
1961年秋,我家搬回斋公桥村后,我便回到张岗学校上五年级。班主任是李修文老师(椿树李人),他的语文课教得很好,我特别爱听他的写作课。从他上的写作课上,我学会了写记叙文、写读后感的方法和技巧。
我最高兴的是学校为五、六年级配备了汽灯。晚自习时,同学们能在明亮的灯光下读课文,做作业,没有了点煤油灯熏黑鼻孔的烦恼。
当时的五、六年级是寝教合一,晚自习下课后,男生在教室里挪桌凳、摊床铺,然后睡觉。
记得有天晚上,因值日生忘记往教室里掂尿桶,我和另两位同学只好披上衣服到六年级教室门前,隔着门槛,尿到放在门槛內的尿桶里。
第二天早自习,六年级班主任蒿成章老师,把我叫到一年级教室的讲台上,“咚”的一脚,把我踢成立正姿势。“你夜儿黑为啥尿到我们班王道远头上?”突如其来的质问如晴天霹雳,吓得我目瞪口呆。仔细回忆我昨晚绝对是尿到尿桶里的,我便问蒿老师是谁说的,蒿老师:“你别问谁说的!你必须承认错误,向王道远道歉!”“我敢保证我没尿到他头上,我没有啥错,道啥歉?”“那你就站这儿吧,啥时候认错了啥时候回你们教室!”
一直等到放学,我仍没有认错。蒿老师说:“你去找你们班主任吧,让他处理这事。”于是我悻悻地找到李修文老师,李老师问我有无此事,我向李老师保证绝无此事,李老师说:“没有也就算了。你最近买新画书没有?”“买了一本《鸡毛信》。”“那好,吃罢饭拿来让我也看看。”
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鸡毛信》画本装进口袋,一到学校我就拿给了李老师。
这事到此为止,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是我班李恒林同学那晚不小心尿在桶沿上,迸到睡在附近的王道远的头上了。
1962年秋期,我上六年级。班主任是李灿然老师(宋洼村人)。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放学时,他对我和同村的孙栓柱、孙新朗说:“下午你们仨不用来校了。班里有勤工俭学的5元钱在李修文老师那里,他现在在庙坡学校,你们下午到庙坡学校找李老师把那钱拿回来,我们好买些白纸、油墨,印复习资料用。”
当天下午,我们三人蹚过毗河,来到椿树李村北边的庙坡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老师。她长得眉清目秀,白皙的脸上透着红晕,浅浅的酒窝,红润的嘴唇。中等身材,丰满标致。说话和气而温柔,举止端庄而从容。她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微笑着对我们说:“李老师今天上街了,还没回来,等他回来了,我一定把你们的来意告诉他。”(后来听说李修文老师在第二天就到宋洼村,把5元钱交给了李灿然老师。)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人不谈没见到李老师的遗憾,却大谈见到的女老师如何漂亮,如何端庄,如何有气质,一致认为来庙坡学校能看到如此美丽动人的女老师,也太值了。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她就是美女的天花板。
六年级的秋期和春期,李灿然老师教算术,何长庆老师(何庄村人)教语文。他俩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课堂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讲解,早晚自习不厌其烦地辅导,使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
在1963年6月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校学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二十多名考生中,我和李勤功、李古贤、孙栓柱、李建玉、任文平、张荣珍、雷春记、雷保山、雷庆山等十人被唐河二中(源潭)录取,升学率竟与号称“小宝塔”的宋沟学校不差上下。
从此,我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句号,又开始了初中求学的新征程。
2025.08.30
主 编 | 马营 副主编 | 陈峰 题 字 | 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