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北直隶顺天府香河县有位倪太守,名叫守谦,字益之,家里有千金财产,良田美宅。夫人陈氏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善继,长大娶妻后,陈夫人便去世了。倪太守辞官在家,虽然年纪老了,精神却还很健旺。收租放债这些事,他都亲自操心,不肯闲下来享受。
倪太守七十九岁那年,儿子善继对他说:“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今年七十九,明年就整八十了,何不把家事交给我掌管,您安心享享清福?”老头子摇摇头,说了几句话:“活一天,管一天。看着你,帮着你,挣些利钱吃穿用。等到两脚一伸直,那时才不关我的事。”
每年十月,倪太守都亲自去庄上收租,一住就是整月。庄户人家杀鸡备酒,好好招待。这一年,他又去住了几天。有一天午后无事,他绕庄散步,观赏野外景色。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和一个白发婆婆在溪边石头上捶洗衣裳。那女子虽是乡村打扮,却颇有几分姿色。
倪太守老年兴致勃发,竟看呆了。那女子捶完衣裳,跟着老婆婆走了。倪太守留心看着,只见她们走过几户人家,进了一个小小的竹篱笆门。倪太守连忙转身叫来管庄的,对他说了这件事,让他去打听那女子是否许配人家。若是没有人家,自己要娶她做妾,不知她肯不肯?管庄的一心想巴结家主,领命便去。
原来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跟着外婆生活。今年十七岁,还没许人。管庄的打听清楚后,就去对老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外孙女长得整齐,想娶她做偏房。虽说是做小,但老夫人去世已久,上头并没人管束。嫁过去后,丰衣足食自不必说;连你老人家每年的衣服、茶米,都由我家照顾;临终还有好发送,只怕你老人家没这福分。”老婆婆听了这番花团锦簇的话,当下就答应了。也是姻缘前定,一说便成。管庄的回复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讲定财礼,看了黄历选个吉日,又怕儿子阻拦,就在庄上行聘成亲。成亲之夜,一老一少,倒也别致。
当夜倪太守抖擞精神,圆了洞房花烛。过了一天,叫顶轿子抬梅氏回宅,与儿子媳妇相见。全家男女都来磕头,称她“小奶奶”。倪太守赏了些布匹给众人,大家都很欢喜。只有倪善继心中不悦,当面虽不言语,背后却和妻子议论:“这老头子真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烛残年,做事也该想想前后。谁知还能活几年?偏做这种没结果的事!讨这样花枝般的姑娘,自己得有精神应付她,难道让她守活寡?还有一桩,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撑不住;那少妇熬不住,走了邪路,丢人现眼,败坏门风。再一桩,那少妇跟着老汉,就像外出逃荒一般,等到荒年过去,她就走了。平时偷偷摸摸,攒下私房钱,东藏西放;又撒娇撒痴,要丈夫买衣置饰给她。等到树倒猢狲散,她便改嫁走人,一包裹收拾了去享受。这是木中蛀虫,米里恶虫。家里有了这种人,最伤元气。”
又说:“这女子娇模娇样,像是个妓女,全无良家体统,看来是个会撒娇撒泼的主,降服丈夫的克星。在咱爹身边,顶多半妾半婢,叫声姨娘,日后还有个退步。可笑咱爹糊涂,竟让众人叫她’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她娘不成?咱们只不认她,别奉承过了头,让她做大起来,日后咱们反倒受她的气。”
夫妻二人嘀嘀咕咕,说个没完。早有多嘴的传了出去。倪太守知道后,虽不高兴,却也藏在心里。幸好梅氏性情温良,待上待下,一团和气,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过了两个月,梅氏怀了孕,瞒着众人,只有丈夫知道。十月怀胎,生下一个男孩。这天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就叫重阳儿。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这年他正好八十岁,贺客盈门。倪太守设宴款待,一来庆寿,二来小孩儿三朝,就当汤饼会。众宾客都说:“老先生高寿,又新添了小公子,可见血气不衰,这是长寿之兆啊。”倪太守大喜!倪善继背后却说:“男子六十而精绝,何况八十岁,哪有枯树开花的?这孩子不知是哪来的杂种,决不是咱爹的亲骨肉,我绝不认他做兄弟。”老子又知道了,还是藏在肚里。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重阳儿周岁,准备抓周。亲戚们都来祝贺。倪善继却出门去了,不来陪客。老子知道他的意思,也不去找他回来,自己陪着亲友,吃了一日酒。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总有些不痛快。自古道:“子孝父心宽。”那倪善继平日做人又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分了他一份家产,所以不肯认作兄弟;预先散布恶言,日后好整治他们母子。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怎不明白这个关节?只恨自己老了,等不到重阳儿长大成人,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生活;现在不能跟他结仇,只能忍耐。看着这小孩子,好生疼爱;看着梅氏年纪轻轻,好生怜惜。时常想一阵,闷一阵,恼一阵,又懊悔一阵。
再过四年,小孩子长到五岁。老子见他聪明,又很活泼,要送他去学堂读书。取个学名,哥哥叫善继,他就叫善述。选个好日子,备了果酒,领他去拜师父。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倒也方便。谁知倪善继和父亲不是一条心。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与自己排行,先就不乐意了。又让他和自己儿子同学读书,儿子要叫他叔叔,从小叫惯了,日后怕被他欺压;不如叫儿子出来,另找个师父。当天就把儿子叫出来,推说有病,连日不到学堂。倪太守起初以为真病了。过了几天,听师父说:“大公子另请了个先生,分成两个学堂,不知是什么意思?”
倪太守听了这话,不觉大怒,就要找大儿子问个究竟。又一想:“天生这个逆子,跟他说也没用,随他去吧!”憋着一口闷气回到房中,偶然脚步慢了些,绊着门槛跌了一跤。梅氏慌忙扶起,搀到醉翁床上坐下,已经不省人事。急忙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是中风。忙取姜汤灌醒,扶他上床。虽然心里明白,却全身麻木,动弹不得。梅氏坐在床头,煎汤熬药,殷勤伺候,连服了几剂,全无效果。医生诊脉后说:“只能拖延日子,不能痊愈了。”倪善继听说,也来看过几次。见老子病势沉重,料想不行了,便开始呼喝奴仆,打骂童子,预先摆出家主的架势来。老子听了,更加烦恼。梅氏只好啼哭,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留在房中陪伴父亲。
倪太守自知病重,叫大儿子到面前,取出一本簿子,家中田地房屋及各项账目总数都在上面,吩咐道:“善述才五岁,衣服还要人照管;梅氏又年轻,未必能管家。若分家产给他,也是枉然,如今全部交付给你。倘若善述日后长大成人,你看在爹的面上,帮他娶房媳妇,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亩,不让他挨饿受冻就够了。这些话,我都写在家产簿上,就当分家,给你做个凭证。梅氏若愿改嫁,随她的便;若肯守着儿子过日子,也别逼她。我死之后,你一一照我的话做,就是孝子,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倪善继翻开簿子一看,果然开得细,写得明,满脸堆笑,连声答应:“爹不用担心,儿子一定照爹吩咐的办。”抱着家产簿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梅氏见他走远,两眼垂泪,指着孩子道:“这小冤家,难道不是你的亲骨肉?你却和盘托出,都给了大儿子,叫我们母子日后靠什么过活?”倪太守道:“你不知道,我看善继不是个善良之人,若把家产平分了,连这孩子的性命也难保;不如都给他,顺了他的意,他才不会猜忌。”梅氏又哭道:“虽然如此,自古道’子无嫡庶’,若分得太不平均,会被人笑话。”倪太守道:“我也顾不得了。你年纪还轻,趁我没死,把儿子托付给善继。等我死后,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你心里选个好人家,自己去图下半辈子幸福,别在他们身边受气。”梅氏道:“说哪里话!我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况且有了这孩子,怎舍得抛下他?好歹要守着这孩子。”倪太守道:“你真肯守一辈子?莫非日久生悔?”梅氏便发起誓来。
倪太守道:“你若立志坚定,不愁母子没得过活。”便从枕边摸出一件东西,交给梅氏。梅氏起初以为又是一个家产簿子,却原来是一尺宽、一尺长的一个小轴子。梅氏道:“要这小轴子有什么用?”倪太守道:“这是我的行乐图,其中自有奥妙。你要悄悄收藏,别让人看见。直到孩子长大,善继不肯照顾他时,你也要藏在心里。等遇到贤明的官员,你拿这轴子去告状,说明我的遗命,求他细细推详,自然会有个处理,足够你们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轴子。
倪太守又拖了几天,一夜痰涌,叫唤不醒,呜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岁。
倪善继得了家产簿,又要了各仓各库钥匙,每天只顾查点家财杂物,哪有工夫到父亲房里问安。直到父亲死后,梅氏叫丫鬟去报丧,夫妻二人才跑来,也哭了几声“老爹爹”。没一个时辰,就转身走了,倒让梅氏守着尸首。幸亏衣衾棺木都是预先备好的,不用倪善继费心。入殓成服后,梅氏和小孩子守着孝堂,早晚啼哭,寸步不离。善继只是点名应客,全无哀痛之意,七天就择日安葬。回丧那夜,他就到梅氏房中,翻箱倒柜;只怕父亲存了私房银子在内。梅氏乖巧,怕他收走行乐图,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箱笼先打开,拿出几件旧衣裳,让他夫妻查看。善继见她大方,倒不来看了。夫妻二人乱翻一阵,走了。梅氏想到苦处,放声大哭。那小孩见亲娘如此,也哀哀哭个不停。这般情景,任是泥人也应落泪,纵是铁汉也会心酸。
第二天一早,倪善继又叫了泥瓦匠来看房子,要重新改造,给自家儿子娶亲用。将梅氏母子搬到后园一间杂屋内栖身。只给他们一张四脚小床和几件粗桌粗凳,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件。原来房中有两个丫鬟服侍,只把年纪大的叫走了,留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使女。每天到厨房取饭。有菜没菜,都不管。梅氏见不方便,索性要了些米,砌个土灶,自己煮饭吃。早晚做些针线,买些小菜,勉强度日。小学生到邻家上学,学费都是梅氏自己出。善继又屡次叫妻子劝梅氏改嫁,又找媒婆说亲,见梅氏誓死不从,只得罢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声不响,所以善继虽然凶狠,也不把他们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似箭,善述长到十四岁。原来梅氏平生谨慎,以前的事,在儿子面前一字不提。只怕孩子口不紧,惹出是非,有害无益。等到十四岁时,他心里渐渐明白,瞒不住了。一天,他向母亲要件新绢衣穿,梅氏回道:“没钱买。”善述道:“我爹做过太守,只生我们兄弟两个。现在哥哥那么富贵,我要件衣服都不能,这是为什么?娘若没钱,我自己去跟哥哥要。”说罢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儿啊,一件绢衣,不是什么大事,也去求人。常言道:’惜福积福’,’小时穿线,大来穿绢’。若小时穿了绢,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再过两年,等你读书进步,做娘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给你穿。你那哥哥不好惹,缠他做什么!”善述道:“娘说得是。”口里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想着:“我父亲万贯家财,少不得兄弟两人平分。我又不是随娘改嫁带来的拖油瓶,怎么哥哥全不照顾?娘又这样说,难道一匹绢都没有我的份,非要娘卖身来做给我穿?这话好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老虎,怕他怎的?”
心生一计,瞒了母亲,径自到大宅里去。见了哥哥,叫声:“作揖。”善继倒吃了一惊,问道:“你来做什么?”善述道:“我也是官宦子弟,身上破烂,被人耻笑。特来找哥哥,要匹绢做衣服穿。”善继道:“你要衣服穿,自己跟娘要。”善述道:“老爹爹的家产,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继听说“家产”二字,知道来头不小,便红着脸问道:“这话是谁教你说的?你今天是来要衣服,还是来争家产?”
善述道:“家产少不得有日分家,今天先要件衣服,装装体面。”善继道:“你这野种,要什么体面!老爹爹纵有万贯家财,自有嫡子嫡孙,关你这野种屁事!你今天听了谁的挑唆,来找麻烦?别惹我生气,叫你母子二人没安身之处!”善述道:“都是老爹爹生的,怎么我是野种?惹你生气又怎样?难道害了我们母子,你就独占了家产不成?”善继大怒,骂道:“小畜生,敢顶撞我!”抓住他衣袖,捏起拳头,一连七八个栗暴,打得他头皮青肿。善述挣脱了,一溜烟跑走,哭哭啼啼到母亲面前,一五一十告诉母亲。梅氏埋怨道:“我叫你别惹事,你不听,打得好!”口里虽这么说,扯着青布衫,帮他揉头上肿处,不觉泪流满面。
梅氏左思右想,怕善继怀恨在心,便叫使女进去致歉,说小学生不懂事,冲撞了兄长,赔个不是。善继还是怒气不息。第二天一早,邀了几个族人在家,取出父亲亲笔分家文书,请梅氏母子到来,当众看了,便道:“各位尊长在上,不是善继不肯养他们母子,要赶他们出去。只因善述昨天跟我争家产,说了许多话,怕他日后长大,说得更多,所以今天分他们母子出去住。东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亩,都是遵照老爹爹遗命,不敢自作主张,请各位尊长作证。”这伙亲族,平日知道善继为人厉害,又有父亲亲笔遗嘱,谁肯多嘴,做冤家?都说着好听话。那奉承善继的道:“千金难买亡人笔。照分家文书办,没话说了。”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也只说:“男子不吃分家饭,女子不穿嫁时衣。多少白手起家的!现在有屋住,有田种,不算没根基了,只要自己努力。有粥莫嫌稀,各人自有各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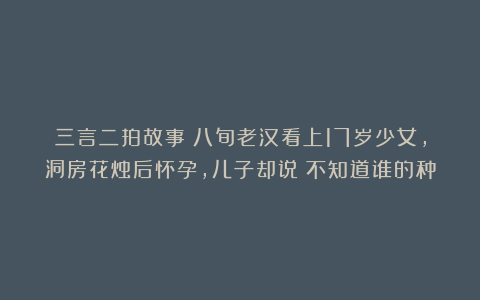
梅氏料想:“在园屋里住,不是长久之计!”只得听凭分家,同孩子谢了众亲长,拜别了祠堂,辞了善继夫妇;叫人搬了几件旧家具和原嫁来的两只箱笼,雇了牲口骑坐,来到东庄屋内。
只见荒草满地,屋瓦稀疏,多年没有修整。上漏下湿,怎么住得?勉强打扫一两间,安顿床铺。叫庄户来问,连这五十八亩田,都是最差的下等田:大熟之年,一半收成还不够;若遇荒年,还要赔粮。梅氏叫苦不迭。倒是小学生有见识,对母亲道:“我们兄弟两个,都是老爹爹亲生,为什么分家文书上这样偏心?其中必有缘故。或许不是老爹爹亲笔?自古道:家产不论尊卑。母亲何不告官申理?厚薄由官府判断,也免得心里怨恨。”梅氏被孩子提起线索,便将十几年来隐藏的心事,都说了出来:“我儿别疑心分家文书,那正是你父亲的笔迹。他说你年纪小,怕被你哥哥暗算,所以把家产都判给他,让他安心。临终那天,只给了我一张行乐图。一再嘱咐:’其中藏着哑谜,直到贤明官员在任,送他详察,包你们母子有得过活,不致贫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为什么不早说?行乐图在哪里?快拿来给我看看。”
梅氏开了箱子,取出一个布包。解开包袱,里面还有一层油纸封着。拆了封,展开那一尺宽、一尺长的小轴子,挂在椅子上,母子一齐下拜。梅氏祷告道:“村庄香烛不便,请恕怠慢。”善述拜罢,起来仔细看时,是一个坐像,头戴乌纱,白发苍苍,画得神采奕奕。怀中抱着婴儿,一只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天,全然不懂。只得依旧收卷包好,心里好生烦闷。
过了几天,善述到前村想找个师父讲解,偶然从关王庙前经过。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礼,祭赛关圣帝君。善述站住观看,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着竹杖,也来闲看,问众人道:“你们今天为什么祭神?”众人道:“我们遭了冤枉官司,幸亏官府明白,断明了这案子。以前许下神愿,今天特来还愿。”老者道:“什么冤枉官司?怎么断的?”其中一人道:“本县奉上司明文,十家为一甲。小人是甲首,叫成大。同甲中有个赵裁缝,是第一等好手艺。常在人家做夜工,整几天不回家。忽然一天出去,一个多月不回。老婆刘氏央人四处寻找,没有踪迹。又过了几天,河里漂出一具尸首,头都打破了,地方报官。有人认出衣服,正是那赵裁缝。赵裁缝出门前一天,曾和小人酒后争吵。一时发怒,打到他家,砸了他几件家具,这是有的。谁知他老婆把这条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县听信一面之词,把小人判了死罪。同甲不举报,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小人无处伸冤,在狱中一年。”
“幸好新任滕县官,虽是举人出身,却很明白。小人趁他审案时哭诉冤枉。他也疑惑道:’酒后争吵,不是大仇,怎会谋害性命?’准了小人的状子,出牌拘人复审。滕县官一眼看着赵裁缝的老婆,千不说,万不说,开口便问她是否改嫁?刘氏道:’家贫难守,已经嫁人了。’又问:’嫁的什么人?’刘氏道:’是同辈的裁缝,叫沈八汉。’滕县官当时火速捉拿沈八汉来问道:’你几时娶这妇人?’八汉道:’她丈夫死了一个多月,小人才娶回来。’滕县官道:’谁做的媒?用了什么聘礼?’八汉道:’赵裁缝在世时曾借过小人七八两银子,小人听说赵裁缝死了,走到他家探问,顺便催取这银子。那刘氏没钱还,情愿嫁给小人,抵折这银两,其实没请媒人。’滕县官又问道:’你做手艺的人,哪里来这七八两银子?’八汉道:’是陆续凑给他的。’滕县官拿纸笔让他细开每次借银数目。八汉写了出来,或米或银共十一次,凑成七两八钱。”
“滕县官看完,大喝道:’赵裁缝是你打死的,怎么冤枉别人?’便用夹棍夹起,八汉还不肯认。滕县官道:’我说出实情,叫你心服。既然放债收利,难道再没第二个人可借,偏偏都借给赵裁缝?必是平日与他妻子有奸情,赵裁缝贪你东西,知情纵容。后来想做长久夫妻,便谋害了赵裁缝。却又教那妇人告状,赖在成大身上。今天你开账单的字迹,与旧时状纸笔迹相同,这人命不是你害的是谁?’再叫把妇人上拶刑,要她招认。刘氏听见滕县官言语,句句合拍,像鬼谷子先师一般,魂都吓散了,哪敢抵赖。拶子套上,就承认了。八汉也只得招了。原来八汉起初与刘氏私下相好,别人都不知道。后来往来勤了,赵裁缝怕人看见,渐渐有断绝之意。八汉私下与刘氏商量,要害死赵裁缝,做长久夫妻。刘氏不肯。八汉趁赵裁缝在人家做完活回家,骗他到店里喝得烂醉;走到河边,将他推倒;用石块打破脑门,沉尸河底。只等事情冷了,便娶那妇人回家。后来因尸首漂起,被人认出,八汉听说小人有争吵之隙,便去唆使那妇人告状。那妇人直到嫁后,才知道丈夫是八汉谋害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语。却被滕县官审出真情,将他夫妻抵罪,释放小人回家。多承各位亲邻凑出份子,叫小人祭神。老伯,您说有这样冤枉的事吗?”老者道:“这样贤明的官府,真是难得!本县百姓有幸了。”
倪善述听在肚里,回家告诉母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这样好官府,不拿行乐图去告状,还等什么时候?”母子商议定了。打听了放告日期,梅氏起个大早,领着十四岁的儿子,带着轴子,来到县衙叫喊。县官见没有状词,只有一个小轴子,很是奇怪,问起缘故。梅氏把倪善继平日所作所为,以及老子临终遗嘱,详细说了。滕知县收了轴子,叫他们先回去,“等我进衙细看。”正是一幅画图藏哑谜,千金家事靠搜寻。只因寡妇孤儿苦,费尽贤官一片心。
不说梅氏母子回家。且说滕知县放告完毕,退回后衙,取出那一尺宽、一尺长的小轴子,看是倪太守行乐图: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指着地下。推敲了半天,想道:“这个婴儿就是倪善述,不用说。那一手指地,莫非是要当官的念他地下之情,帮他出力?”又想道:“他既有亲笔分家文书,官府也难做主。他说轴中含藏哑谜,必定还有道理。若我断不出这事,枉自聪明一世。”每天退堂,便将画图展开玩味,千思万想。这样过了几天,还是不解。
也是这事该当明白,自然生出机会来。一天午饭后,又去看那轴子。丫鬟送茶来,他一手去接茶碗,偶然失手,泼了些茶把轴子沾湿了。滕知县放下茶碗,走到阶前,双手拉开轴子,就着日光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见轴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县心疑,揭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字纸,衬在画下,正是倪太守遗笔。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太守,寿过八十。死在旦夕,也没什么遗憾。只是小儿子善述,才满周岁,急切不能成人。大儿子善继一向缺少孝悌之心,日后恐怕会害他。新置的两所大宅及一切田产,都交给善继。只有左边旧小屋,可分给善述。这屋子虽小,室中左墙埋银五千两,分作五坛;右墙埋银五千两,金一千两,分作六坛,可以抵田园之数。日后有贤明官员断案,善述可酬谢他白银一百两。八十一翁倪守谦亲笔。年月日画押。
原来这行乐图,是倪太守八十一岁时给小孩子做周岁,预先备下的。古人说知子莫若父,果然不假。滕知县最有机变,看见这许多金银,未免动了贪念。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差人“密拿倪善继来见我,自有话说。”
却说倪善继独占家产,心满意足,天天在家享乐。忽见县差拿着手令拘唤,一刻不容停留。善继推脱不得,只好跟着到县。正值县官升堂理事,差人禀报:“倪善继已拿到了。”县官叫到案前,问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长子吗?”善继应道:“小人正是。”县官道:“你庶母梅氏告你赶母逐弟,霸占家产房产,这事是真的吗?”倪善继道:“庶弟善述,从小在小人身边抚养长大。近日他告有万贯家财,非同小可;遗笔真假,也未可知。念你是官宦之后,且不难为你。明天可叫齐梅氏母子,我亲自到你家查问家产。若厚薄确实不均,自有公道,不能凭私情而论。”喝令差役押出善继,就去传集梅氏母子,明天一同听审。公差得了善继的好处,放他回家去了,自往东庄传人。
再说善继听见官府口气厉害,好生惊恐。论起家产,其实并未分家,单凭父亲分家文书,必须有亲族见证才好。连夜将银子分送一帮亲长,嘱咐他们第二天一早都到家来。若官府问起遗笔一事,求他们同声相助。这伙亲族,自从倪太守死后,从没见善继送过一盘一盒,过年过节也没请过一杯酒。今天大块银子送来,正是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各自暗笑,乐得收了买好东西吃。明天见官,旁观动静,再见机行事。
且说梅氏见县差来传,知道县官要为她做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母子二人先到县衙去见滕县官。县官道:“怜你孤儿寡妇,自然该帮你说话。但听说善继持有亡父亲笔分家文书,这怎么办?”梅氏道:“分家文书虽有,却是保全孩子的计策,并非亡夫本意。老爷只看家产簿上数目,自然明白。”县官道:“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别抱太大希望。”梅氏谢道:“若能免于饥寒就满足了,哪敢指望和善继一样做富家翁?”滕县官吩咐梅氏母子:“先到善继家等候。”
倪善继早已打扫厅堂,堂上设一把虎皮交椅,点起一炉好香。一面催请亲族:“早点来等候。”梅氏和善述到来,见众多亲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见,也免不了说几句求情的话。善继虽然一肚子怒火,这时也不好发作。各自暗中准备见官的说辞。
等不多时,只听得远远喝道之声,料是县官来了。善继整顿衣帽迎接;亲族中,年长懂事的,准备上前见官;那些幼辈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后张望,打听消息。只见一对对执事排成两班,后面青罗伞下,罩着足智多谋的滕县官。到了倪家门口,执事跪下,吆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迎接。门子喝声:“起来!”轿夫停下轿子,滕县官不慌不忙,走下轿来。正要进门,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躬;嘴里应答,好像有主人迎接一般。众人都吃惊,看他做什么模样。只见滕县官一路作揖让礼,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说了许多寒暄的话。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打个躬,好像有人请他坐一般,连忙转身,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放下;又向空中再一谦让,方才上坐。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县官在上座拱手作揖,开口说道:“尊夫人把家产事告到我手里,这事究竟如何?”
说罢,便作出倾听的样子。良久,才摇头吐舌道:“大公子太不善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言自语道:“叫小公子怎么活?”停一会,又道:“右边小屋,有什么生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又停一时,说道:“这些也交给小公子?我都遵命了。”稍停又拱手作揖道:“我怎么敢当这样厚礼?”推让了半天,又道:“既然尊命恳切,我勉强领受,便写个凭证给小公子收执。”于是起身,又连作数揖,一直说:“我就去。”众人都看呆了。
只见滕县官站起身来,东看西看,问道:“倪老爷哪里去了?”门子禀报:“没见什么倪老爷。”滕县官道:“有这等怪事?”叫善继问道:“刚才令尊老先生,亲自在门外迎接;和我对坐讲了半天话,你们想必都听见了。”善继道:“小人没听见。”滕县官道:“刚才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高颧骨,细眼睛,长眉大耳,亮晶晶的白胡须,纱帽皂靴,红袍金带,可是倪老先生模样吗?”吓得众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的模样。”县官道:“怎么忽然不见了?他说家中有两处大厅堂,又东边旧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继不敢隐瞒,只得承认道:“有的。”
县官道:“且到东边小屋去看一看,自有话说。”众人见县官半天自言自语,说得活灵活现,分明是倪太守显灵,都相信倪太守真的出现了。人人吐舌,个个惊心。谁知都是滕县官的巧计。他也是看了行乐图,照着画像说来,哪有半句是真话!
倪善继引路,众人随着县官,来到东边旧屋。这旧屋是倪太守未中举时所住,自从造了大厅大堂,旧屋空着,只做仓厅,堆放些零碎米麦,留一个家人看管。县官前后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对善继道:“你父亲果然有灵,家中事情,详细跟我说了。叫我做主,这所旧宅子给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继磕头道:“全凭老爷明断。”县官讨家产簿子细细看了,连声道:“好一份大家业。”看到后面遗笔分家文书,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己写定的,刚才却又在我面前,说善继许多不是,这老先生也没主意。”叫倪善继过来,“既然分家文书写定,这些田园账目,一一给你,善述不许妄争。”
梅氏暗暗叫苦,正要上前哀求,只听县官又道:“这旧屋判给善述,这屋中所有东西,善继也不许妄争。”善继想道:“这屋里破旧家具,不值什么。就是堆些米麦,一个月前也卖了七八成了,剩不多点,我也够占便宜了。”便连连答应道:“老爷断得极明。”县官道:“你两人一言为定,不得翻悔。众人既是亲族,都来做见证。刚才倪老先生当面嘱咐说:’这屋左墙下,埋金五千两,分作五坛,应当给小儿子。’”善继不信,禀道:“若果然如此,即使万金,也是兄弟的,小人并不敢争执。”县官道:“你就是争执,我也不准。”
便叫手下拿锄头、铁锹等工具,梅氏母子带路,率领民壮,往东墙下掘开墙基,果然埋着五个大坛。挖出来时,坛中满满的,都是光闪闪的银子。把一坛银子上秤称,算来该是六十二斤半,整整一千两足数。众人看见,无不惊讶。善继越发信以为真:“若不是父亲阴灵出现,当面告诉县官,这埋银,我们尚且不知,县官哪里知道?”只见滕县官叫人把五坛银子一字儿摆在自己面前,又吩咐梅氏道:“右墙还有五坛,也是五千两。另有一坛金子,刚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做酬谢,我不敢当,他一再相强,我只好领了。”梅氏同善述磕头道:“左墙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墙还有,怎敢不遵先人之命。”
县官道:“我怎么知道?据你家老先生这么说,想不是假话。”再叫人发掘西墙,果然六个大坛,五坛是银,一坛是金。善继看着这许多金银,眼里都冒出火来,恨不得抢他一锭;只是有言在先,一个字也不敢开口。滕县官写个凭证,给善述收执,就将这房家人,判给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胜欢喜,一同叩头拜谢。善继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磕几个头,勉强说句“多谢老爷主张”。县官贴了几张封皮,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门,落得受用。众人都以为真是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觉得理所当然,谁敢说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产平分,这千两黄金,兄弟两人各该五百两,怎会到滕县官手里?白白成全了别人,自己还讨气闷,又加个不孝不悌的恶名,千算万算,何曾算得别人,只算得自家而已!
再说梅氏母子,第二天又到县衙拜谢滕县官。县官已将行乐图取出遗笔,重新裱过,还给梅氏收领。梅氏母子这才明白行乐图上,一手指地,是指地下所藏的金银。此时有了这十坛银子,置买田园,成了富户。后来善述娶妻,连生一子,读书成名。倪氏门中,只有这一支极为兴旺。善继两个儿子,都好游荡,家业耗尽。善继死后,两所大宅子都卖给叔叔善述管业。乡里知道倪家之事始末的,无不认为是天理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