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格奥尔基在此所体现的现代性不能和佩雷克相提并论,他达不到后者所追求的纯客观以及随之而来的“体系性”,但我们一样会如同听到贝多芬的奏鸣曲感到一种不自在一样,我们从男孩看到的场景中感到一种不自在,下一秒钟这种不自在就转化成了绝望般的悲凉,仿佛我们就是那个男孩。一个将阅读当作休闲、娱乐选项的读者不太会想要这种悲凉,他甚至厌恶它,而我们享受它,因为在某些时候——一定存在那种时候——悲凉笼罩了生活,但我们仍旧想从绝望中生发出希望,否则生活的意义简直就要消弭殆尽了。正因如此,我们在鞋子场景的背后,开始着迷于这样的场景:
“秋天的时候,窗户上积满掉落在人行道上的金黄发红的树叶,这让房间里的光线变得柔软且泛着金色。之后,晚秋的风又会吹散这些树叶。雨水来了,眼前就成了永远的一汪水洼。你长时间地这么站着,看着雨珠是如何掉进水洼里,形成并不能持久的小气泡,组成整编的舰队,然后,后面的雨珠又会消灭掉这些舰队。历史上有多少海战就是在这样的水洼里展开的。再之后,雪就堆满了小小的窗户,小小的房间也随之变成了洞穴。我蜷缩成一个球,就像一只藏在雪下面的兔子。如此明亮,但你还是被隐藏了起来,他们看不见你,虽然他们的脚步声就在你眼前一拃远的雪地上嘎吱作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的呢。”
因此我们也会理解男孩为什么会成为“蚂蚁的上帝”。
“很多时候,他是个好上帝,帮助它们,喂给它们面包渣或者打死的苍蝇,他用小木棍把死苍蝇推到蚂蚁窝旁边,免得蚂蚁还要受搬运之苦。
但有时他也会没来由地发火,就像真正的上帝一样,或者,他只是想玩玩,往迷宫的沟槽缝里浇上一小茶缸水,给蚂蚁们来一场大洪水。
另一些时候,他把盐撒在地砖的边缘,偶然发现了蚂蚁们一点也不喜欢盐,它们在这个临时监狱的走廊里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智慧和语言。它们相遇的时候,会快速触碰一下彼此的触须,似乎在相互通知某个非常重大的秘密。
他的另一个发现神圣而且科学,那就是蚂蚁一点也不喜欢人的气味。如果你用手指头在一只蚂蚁的周围画一个圆圈,蚂蚁就会在这个看不见的界线上费力折腾,似乎是你建造了一堵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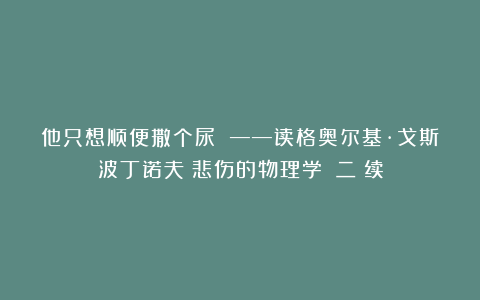
他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这种能力,他把这视作可怕的缺陷,他能体验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他能进入别人的身体里、语言也会随后而至。他成了他们。”
绝望会传染。对于一个一整天被留在家里的六岁男孩,被警告说街上已经爆了两个煤油炉、因此一定密切关注家里的煤油炉,他只会有被遗弃、害怕的感觉。就像悬崖上的受惊的岩羊,它们慌不择路地四下奔跑,寻找安全的感觉;就像饥饿的雪豹,拖着疲惫的身体,寻找可以生存、可以致命一击的机会。对于这个男孩,猜测车牌,成为“蚂蚁的上帝”,就是他宣泄、释放那种恐惧感的通道。帮助它们、玩弄它们、折磨它们,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体会一种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生存困境——被折磨,同时也折磨他人。
暴力也会传染。这就像信奉“棍棒出孝子”的教育准则的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与自己的认知有所区别的教育观念,不相信爱、包容、理解、批判性的思维或许才是教育的真谛,暴力是他们面对子女的“过失”——他们所以为的过失——唯一的武器或工具。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校园中的霸凌者、抑郁者、被欺辱者、心态扭曲者往往就是这样诞生的。
霸凌者将所承受的暴力转嫁到他人身上,因为既然无法抵抗强力者的暴力,那就让弱小者也常常暴力的滋味吧,这是他们的符合逻辑的推理。抑郁者已经对世界失去了信心,因为如果最亲近的人都不相信自己,不爱自己,要通过暴力惩罚自己,那还有什么是值得希望的呢?被欺辱者被暴力吓破了胆,他们就像经常被鬣狗围攻、侥幸逃脱的小羊,以为无论是谁,都是可以拿捏、欺辱、侵害甚至消灭自己的强者,除了忍受之外,生活不会有其他的样态。心态扭曲者已经脱离了逻辑、理性的范畴,他们如果成长为霸凌者,将是狐狸、刺猬、鬣狗、狮子的结合体,想想《白夜行》中的主角,我们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即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像一头被虐待、被规训、被迫表演取悦于人,因而怒火中烧的疲惫的大象一样,将任何一个不幸走到近前的驯兽师踩成——肉——泥,让人分不清骨头和血肉的区别。
所以我们不能谴责男孩对蚂蚁施加的暴力,正如在霸凌者、抑郁者、被欺辱者、心态扭曲者的动因和后果中发现的一样,我们再次体会到一种悲凉。这种悲凉仅仅在下面的场景中得到些微缓解:
“但是到了冬天,事情就发生变化了,你不可能一整天都待在外面。房间变得更加昏暗,散发着煤油炉的气味,而且有可怕的东西从床下探出头来,或者在被咬出洞的柜子里面嘎吱作响。那时唯一的救星就是窗户了。他一早上就爬到窗户上去,只有中午吃面包片的时候才下来,顺便撒个尿。”
评价:4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