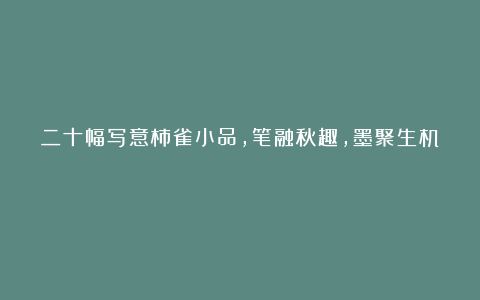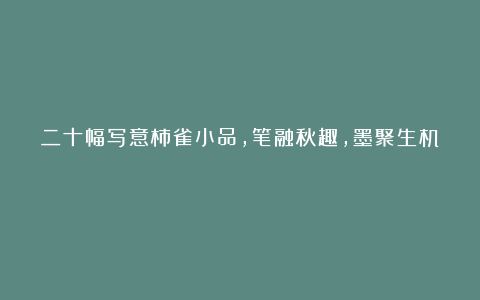|
在中国写意花鸟画的谱系里,柿子与麻雀是承载着烟火气与文化意涵的经典组合。柿子以“柿柿如意”的吉祥寓意扎根民间审美,麻雀凭灵动鲜活的姿态成为自然生机的代名词,二者相遇,便生发出“寻常物象藏雅趣”的艺术张力。当代写意画家安立鲲,以笔墨为舟,在这一传统题材中开辟新境,其笔下小品,既守古法笔墨的醇厚,又融当代审美的通透,将柿子的温润、麻雀的灵动与自我的情志熔于一炉,让观者在浓淡墨色间,读懂写意画“以形写神、以物抒情”的深层魅力。
赏安立鲲的柿雀作品,首重笔墨的“活态表达”。写意之魂在笔墨,而笔墨的生命力,在于“笔随心动”的自在与“墨分五色”的层次。安立鲲画柿子,不取工笔的精雕细琢,而用没骨法晕染,笔锋先蘸朱红,再在笔尖轻扫赭石与淡墨,落纸时依着果实的形态“按、转、提”,一笔便勾勒出柿子的圆润轮廓。最见功夫的是柿子的“质感塑造”——向阳面朱红浓烈,似裹着秋日暖阳;背阴处赭墨轻笼,若蒙着一层薄霜;顶端的柿蒂以浓墨点画,两笔交叉出蒂萼的卷曲之态,仿佛还带着枝头的青涩与韧性。这种笔墨不是对柿子的“复刻”,而是对其“神韵”的提炼,朱红不艳俗,赭墨不沉闷,一笔之中藏着色彩的渐变,尽显柿子“饱满而不臃肿,温润而不软塌”的特质。
再看画中的麻雀,更是笔墨灵动的绝佳注脚。安立鲲画雀,从不陷入“羽毛细描”的桎梏,而是抓住麻雀“动与静”的瞬间神态。画面中三只麻雀栖于柿枝,姿态各异:一只昂首啄向柿蒂,喙部微张,雀身前倾,似能听见啄食的轻响;一只侧身梳理羽毛,翅膀微展,尾羽轻翘,透着几分慵懒闲适;一只垂首凝视下方,爪子紧扣枝桠,眼神专注,藏着孩童般的好奇。他画雀身,以淡墨横扫,一笔成形,似不经意间便带出麻雀的蓬松体态;画翅膀,用浓墨短皴,线条短促而有力,如风吹羽动,暗藏韵律;画雀眼,以焦墨点染,虽小如粟米,却有神采,或灵动、或专注、或俏皮,瞬间让麻雀“活”了过来。尤为精妙的是雀爪,以中锋细笔勾勒,线条劲挺如铁丝,牢牢抓在柿枝上,与雀身的蓬松形成“刚与柔”的对比,既显“稳”,又藏“劲”,寥寥数笔便让麻雀有了“立于枝头而不晃,动于瞬间而不僵”的生动感。
若说笔墨是画作的“骨架”,那意境便是其“血肉”。安立鲲的《柿雀图》,最动人处在于“以简驭繁”的意境营造。构图上,他摒弃了“满纸皆景”的堆砌,转而追求“疏朗有致”的留白之美:柿树主干从画面左侧斜出,枝干虬曲如老龙探爪,却不杂乱,分枝或长或短,或粗或细,错落间透着章法;枝上柿子七八枚,或聚如团锦,或散若疏星,疏密搭配恰到好处,既不显得拥挤沉闷,也不显得空疏单薄。画面右侧大片留白,无云、无山、无竹,却让观者生出无限联想——那空白处,或许是秋日的高远晴空,或许是庭院的斑驳竹篱,或许是微风拂过的柿叶轻响,正如中国传统美学中“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追求,留白不是“空”,而是意境的延伸,让观者在凝视中,仿佛走进了一幅“秋阳暖柿,雀鸣枝头”的田园画卷。
更深处,安立鲲的柿雀作品还藏着“以物抒情”的温度。写意画的高妙,从不只在“画物”,更在“写心”。柿子的“红”,在他笔下不只是色彩,更是对生活的热爱——朱红的果实挂满枝头,如灯笼般点亮画面,传递出“事事顺遂”的美好期许,这份温暖不刻意、不张扬,却像秋日里的暖阳,悄悄熨帖着观者的心境。麻雀的“活”,也不只是形态,更是对自由的向往——它们没有笼中雀的拘谨,只有天地间的自在,或啄食、或理羽、或嬉戏,每一个动作都透着“无拘无束”的生机,这恰是安立鲲对“写意精神”的诠释:不被技法束缚,不被物象局限,以笔墨为媒介,传递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与对自然最本真的敬畏。
细品安立鲲的柿雀作品,还能看到他对“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从题材上看,柿雀图是传统的,但他的笔墨语言却带着当代的通透感——他笔下的柿子,比传统没骨法多了几分立体感;他画的麻雀,比古法多了几分动态感;他的构图,比传统更注重“视觉焦点”的营造,让观者一眼便能抓住画面的核心。
一幅好的写意画,能让观者在笔墨中见性情,在画面中悟人生。安立鲲的作品便是这样的作品。它没有繁复的构图,没有艳丽的色彩,却以简练的笔墨、悠远的意境、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每一位观者。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柿子与麻雀,更是一位画家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对传统的敬畏。当我们凝视那朱红的柿子、灵动的麻雀,仿佛能闻到柿子的清甜,听到雀鸣的清脆,感受到秋日田园的静谧与美好——这,便是安立鲲写意水墨的魅力,也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根本所在:以寻常物象,写不寻常情怀;以朴素笔墨,绘最动人诗行。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