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和一日:安哲罗普洛斯访谈录》 达恩·弗伊纳鲁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5 年 5 月
1998年,《永恒和一日》实至名归地获得金棕榈大奖,安哲罗普洛斯从戛纳评审团主席马丁·斯科塞斯手中接过金棕榈奖杯时说,他属于慢慢走向职业终点的一代人。
1935年4月27日,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出生于希腊古城雅典,今年是这位大师诞辰90周年。‘’我所着迷的一切在我的电影里进进出出,就像交响乐团里各种乐器声忽隐忽现,短暂的隐没是为了再次响起。’’安哲罗普洛斯曾把自己的电影创作归纳为一个主题——“旅途,边界,放逐”。对他来说,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远行,万事万物都是远行和求索。在远行的过程中,那些意识当中原本模糊不清的东西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他著名的 “漂泊/沉默” 三部曲分别代表了历史的沉默(《塞瑟岛之旅》)、爱的沉默(《养蜂人》)和上帝的沉默(《雾中风景》) 。《雾中风景》中那个小男孩曾问他姐姐:’边界的意思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 “边境/追寻” 三部曲中,安哲尝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鹳鸟踟蹰》表现的是分隔国家和人群的地理边界,《尤利西斯的凝视》讲述的是人类视野的边界或局限,《永恒和一日》讨论的则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我没完成我自己想要达到的任何东西。总是有界限,物理的和情感的,它们总是阻止我达到完全满意的状态。”他曾这样回望自己的创作。愈发明显的一点是,安哲完成了从着迷群像到注重个体境遇的转换,历史逐渐淡化成虚焦的后景。
《永恒和一日》的灵感来源于他的衰老和朋友的离世,比他所有之前的影片更加情感化和个人化。片中的主人公、诗人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大半生事无所成——当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发现自己的野心要比最终得到的结果大很多。这几乎就是安哲的自我抒发——他所有的影片都是其生平和生活的组成部分及表达,来自他的人生经历和曾经的梦想。如果说《永恒和一日》更加个人化,是因为这部影片并不像安哲的其他作品那样知性,更多地表达了导演自己的情感而非思想。
故事从灰蒙蒙的塞萨洛尼基、一座位于希腊北部的城市开始。这里曾经是历史遗址,如今是工业中心,城市交通混乱而疯狂。当一辆辆汽车在红色信号灯前猝然停下,成群结队的男孩便从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这些停下来的汽车旁,争抢着擦洗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当一辆警车呼啸而至,警察冲过去抓捕这些卑微的违法者时,只有一个孩子得以逃脱:开车正巧路过的亚历山大打开车门,让那孩子躲了进去。只不过是一个手势,一点人情味——显然,亚历山大并没有什么目的。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他病得很重,不得不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海边住所,预计当晚得住进医院,也拿不准自己能否活着离开。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遇到了这个阿尔巴尼亚男孩。他将孩子从贩童组织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并与之开启了一段贯穿其生命重要时刻的旅程。整部影片就是一段持续的、穿越时间的旅程,贯穿了过去和现在、现实与想象。在某个节点上,这段旅程变成了一场内心之旅,比如,当两人抵达阿尔巴尼亚边境的时候,有个镜头是这样的:有人悬挂在边境的铁丝网上——这当然只是幻觉。有些事件和图景只发生在亚历山大的想象中,那个男孩不仅帮助诗人面对了自我内心的冲突,还给予亚历山大一个理由去游历生命的重要时刻,去回忆他与亡妻安娜共处的欢乐时光。在一天之内,亚历山大向生命中的所有人道别,不断忆起亡妻一封数十年前的信。他几度要把流浪儿送往边境,却与之结下友谊。
为收集到的新词付钱的想法则是安哲从这一真实事件中的扩展,其中的隐喻显而易见。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母语是我们仅有的身份证。每个单词都为习得者打开了新的大门,但要通过这扇门,你必须付出代价。影片中的小男孩看到亚历山大很伤心,为了安慰他,给了他一些自己收集的词语。小男孩走出去,到普通人中间,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个新词,卖给亚历山大——就像两人之间的一种游戏。亚历山大希望找到可以让他超越死亡的桥梁,而且他相信,这座桥梁就是让他继续存活下去的词语,无论他的肉体是否存在。小男孩在影片结尾处离开时留下的三个词语,实际上就是影片的精髓——似乎亚历山大整个的人生都反映其中。第一个词 ‘korfulamu’(一朵花的心),一个很精致的词,在希腊语中表达一个孩子睡在母亲怀中时的感觉;第二个词 ‘xenitis’(具有来自’’陌生’’一词的词根),意指发现自己处于陌生人状态的一类人,带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第三个词是 ‘argathini’(迟暮),表达的是时间,在与小男孩短暂相遇之后,时间已然流逝,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事实。
亚历山大在与小男孩的游戏中收获的三个词,以某种方式评价、概括了他度过的一生:第一个词代表着爱与亲密;第二个词表现的是故事的存在面向,内心的精神状态;第三个词意味着告别。听着亚历山大跟着小男孩反复念叨Argathini,Argathini,Argathini,你会觉得除了最后这次他生命中真正的经历,他只是那些短暂经历的合成体。一如博尔赫斯的诗句所言:‘’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安哲罗普洛斯以安静、忧郁、痛楚和充满哲思的方式重新构建了一种电影美学。在《永恒和一日》中,可以发现与之前影片相似的画面,比如黄色派克外衣、边境的群山景观等等。安哲的父母来自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而他却迷恋希腊北方,迷恋那里阴暗的天空、湿冷的冬季、雨天和雾气。他还认为,每位独具个性的导演都拥有一套可以代表自己的影像——某些特定颜色的使用,独特的格调手法,那些在一部部影片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元素。他像一位地形学者那样勘测实际景观,然后利用它们揭示角色的情感景观。实际上,电影中的景观并不完全真实存在。安哲一度游历了整个希腊,在旅途中发现了那些吸引他的元素——一间屋、一条街、一座山、一个村。他把这些单个元素拼在一个组合的景观中,有时是颜色的统一和谐,有时是形状的相得益彰。在某种意义上,他像画家一样创造图像,从而将自我的愿景投射到画布上。
旅行与返家的主题频繁出现在安哲的影片中。事实上,旅行的动机就表达出再次归家的愿望,在旅行中理解自然而至。即使像《永恒和一日》这样,讲述的只是发生在一座城市里的故事,也依然如此。对于安哲来说,他就像一个仍在寻找自己家园的异乡人,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内心深处的边界,但问题依然如故:抵达目标之前,还要跨越多少条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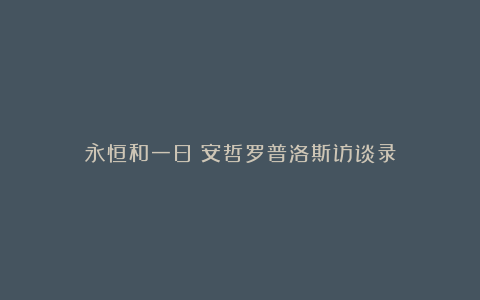
下文选自该书,为英国资深电影评论家杰夫·安德鲁(Geoff Andrew)在1998年所撰写的《他的生命时光:〈永恒和一日〉》。
在影评人大卫·汤姆森( David Thomson)深受好评的1994年版《电影传记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中,他认为希腊电影制作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应该被算作少数几个仍在电影界耕耘的真正大师之一。这是在他壮丽的巴尔干史诗《尤利西斯的凝视》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一年前,也是《永恒和一日》实至名归获得金棕榈奖的四年前。然而安哲罗普洛斯在电影节之外仍旧相对鲜为人知。虽然去年河畔回顾影展的电影票大多销售一空,但他仍旧被那些不熟悉其作品的人普遍视作一个令人“费解”的电影制作人。不是因为他的电影在故事层面难以理解——其实这些故事反映的多为简单的神话,而是人们怀疑,正是这些电影优雅从容的节奏(关于《永恒和一日》是在凑时长的玩笑铺天盖地)与其出处(希腊不是一个电影生产大国)的结合,以及对生与死、记忆与遗憾、历史与身份、艺术与间离这些宏大主题持久且不合时宜的迷恋,让那些期望电影更符合当代快速且激烈的主流美学的看客望而却步。这是一大憾事,因为大卫·汤姆森说得对:抛开偏见,安哲罗普洛斯将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施下一道让人迷惑的魔咒,这在当今电影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从主题和风格上讲,其作品的关键是他对时空的独特处理。自1975年凭借经典之作《流浪艺人》(计划今夏重映)获得国际赞誉之后,安哲罗普洛斯逐渐将其大部分影片建构为旅程,既是实际的旅行和精神之旅,也是地理与时间之旅。相应的,其风格的决定性特征是“游历镜头”(travelling shots):在悠长而流畅的镜头中[这种镜头的复杂性,使得影片《好家伙》(Goodfellas)中经常被引用的那个进入科帕卡巴纳夜总会的长镜头相形见绌],随着从过去(或者说实际上是从个人幻想中)唤起的人物和事件转入当前现实之中,主角就像摄影机一样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其结果犹如梦境一般,令人赏心悦目(流畅的摄影机运动,完美无瑕的构图,抒情诗般的色彩运用,说明安哲罗普洛斯的摄影师乔治·阿瓦尼蒂斯本人几近天才),同时,作为一位极度自信又富于想象力的电影诗人,他的鲜明特征也一目了然。这是人们倾向于把《永恒和一日》部分视为其自传的原因所在。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位病入膏肓的作家回忆旧日幸福时光,并在他离开家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极其短暂的未来之际,与一位阿尔巴尼亚少年难民相遇的故事。
“怎么说呢,”安哲罗普洛斯微笑着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灵感,确实是我自己正在老去,加上近年来朋友们相继离世。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是获悉演员吉安·马里亚·沃隆特(Gian Maria Volonté)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期间,在他的旅馆房间中去世的那个早上。前一天我还跟他在一起,当时他看上去很开心,在他喜欢的地方,与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研读他喜欢的剧本。他的离世让我感到疑惑: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第二天将不存于世,他会怎么样?在面对生死大限的时候,他会怎样起床,怎样喝咖啡?他会去哪里,做什么?”
“就这样,心心念念这些事数月后,另一个想法袭上心头:作为巴尔干战争受害者的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的破碎人生。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时,我遇到过这样的孩子。我也想探讨一位诗人和语言的故事,思考一下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的身份无法与我们的母语分割的观点。接下来,当我去探访托尼诺·圭拉(是安哲罗普洛斯剧本通常的合作者)时,我意识到我只能有一个主题而不是三个主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就像古代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那样,边走边讨论,最后把故事拼在一起。”
凑巧但也不幸的是,疾病和死亡总是萦绕着安哲罗普洛斯后期的影片。除了沃隆特在拍摄《尤利西斯的凝视》期间过早离世外,马斯楚安尼也被死神从他身边夺走,他在其早期影片《养蜂人》和《鹳鸟踟蹰》中担纲主演,是饰演亚历山大的最初人选,也就是这部新影片中的那位作家。“但当我去看望他时,”安哲罗普洛斯叹了口气,“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原来一直充满生气,当时却犹如鬼魂,一切像是预示着他的生命将走到尽头。在遭遇沃隆特突然病逝的意外之后,我只是在想:这怎么可能。于是接下来我打电话给让-路易·特兰蒂尼昂( Jean-Louis Trintignant),他对出演这个角色深感紧张,犹豫不决,后来我还考虑过好几个演员,其中一些是英国演员,但语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安哲罗普洛斯的英语很差,我们的采访是用法语进行的)。这时有人提起布鲁诺·甘茨。我知道他是一名十分优秀的演员,而且像所有瑞士人一样能讲多种语言。但我想到的是他在文德斯影片中的形象,很年轻而且看起来又十分开放,根本不像南欧人!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在巴黎遇到了甘茨,我看到他时,他身着一件灰色长外套,胡须灰白,看上去就像他在我影片中那样苍老。于是我们在影片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的形象……包括那件外套。”
如同安哲罗普洛斯的其他影片一样,《永恒和一日》[这个片名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奥兰多说的一句话:他的爱将坚持到“比永远再多一天”(Forever and a day)]融合了个人与政治:不仅是亚历山大的家庭生活回忆让他重温了希腊近期历史中的那些重要时刻,回想起那位创作了国歌并统一了现代希腊语的诗人索洛莫斯,而且与阿尔巴尼亚孤儿的相遇也反映了当下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局势。这两者的融合既具体又具有普遍性。
“绝对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用意所在。我不能对身边的事漠不关心,例如科索沃正在发生的事情(本次采访是在1998年6月进行的)。就我关心的事情而言,我当然是十足的希腊人:每个艺术家都会深受其生养之地的影响,他的作品因而会成为某种精神自传。我们读的书,我们遇到的人,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期——在我心中,这些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光——都会进入我们的影片,战争之类的事也是如此。希腊内战期间,不仅我的家人分裂为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而且我的父亲被捕入狱并被判死刑。我九岁时,母亲带我进到一间堆满尸体的屋子,去辨认父亲的遗体。就像我会受到欢乐与悲伤、语言、风景等的影响一样,我怎么可能不深受那件事的影响?
所以,您说得对,影片总是会指向历史和当代现实,但我努力以一种诗意的视角去呈现。其他电影制作人可能会拍摄更加现实主义的影片,我给予尊重,但那不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因此,《永恒和一日》不是干巴巴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对一个时代的焦虑做出诗意的隐喻式回应。比如那个孤儿,他不仅仅是个难民,也是亚历山大自己少年时代的映射,而且还是一位死亡天使,引导他穿越过去与现在盘根错节的迷宫,让他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妥协:他的职业导致他常忽视家庭。影片中最后这一点是不是也反映了安哲罗普洛斯自己对于创作生涯的矛盾心理呢?他笑了。
“哦,西班牙作家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n)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写作还是生活》(L’Ecriture ou la Vie)……在家时,我女儿会说:’是呀,我们知道,你明天又要出门了,你忙这忙那,我们根本见不到你。’突然之间我发觉她长大了,懂事了。我错过了与她共同发现某些事情的机会。那些失去的时光是我为创作付出的代价,这让我很是伤心。
每次制作电影时,我都说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接下来……这就像咖啡馆里的两个老头,正值春季,他们注视着匆匆而过的世界,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性。他们看着一个女人走过去,消失在远处。其中一个老头说:’我们要这样多久?’他的朋友答道:’一直到死。’对我而言,这就像我跟电影的关系。”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