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被风吹开的秘密
你信不信,眼前的世界还是有没讲明白的事?就好像咱们小时候路过那片树林,总觉得某棵树底下,会不会真的蹲着个什么——你叫不出名的,野生的毛孩子。事情要是真碰上你身上,可能比电影还离谱。1970年代的一个夏天,新疆戈壁滩上的石油工人老马可就遇到了。
其实那天不过是例行公事,修设备,热得脑门儿都冒汗。可总有人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忽然撞见点不属于这世界的东西。老马就是拎着扳手拐进林地时,蓦地一个踉跄,脚下发了空,差点摔倒。他一回头,发现柳树下蹲着个东西。说是“人”,又不像,说是“猴”,比猴还规矩。浑身毛茸茸,瘦得皮包骨。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它那双大眼睛,活像道子井水——你盯它,它也盯你。那个瞬间,老马宁可相信自己是晒懵了心神走火,也不愿真承认碰见了“妖物”。
可人越是不愿承认,心里的好奇就越嗷嗷叫。一时间,天山脚下几个工地小圈子里,全是“红柳娃”的传说。谁谁碰见了“毛孩子”,有的说见着成群结队,有的说晚上偷吃点心。谁正谁假,没人说得清。只是一传十,十传百,神秘的轮廓就在众人味精般的“添油加醋”中越描越重。
其实关于这种小生物的故事,远不光是近几十年才冒出来。在老一辈人菜窖边上唠嗑,也时常能听见“山精野怪、小人国”的段子。有心人一查,才发现古人早就给这些怪事留了笔。据说,纪晓岚——就是那个清朝出了名的白胡子学者,他在茶烟袅袅的夜晚,边嚼瓜子边给客人讲过“红柳娃”。
他说,这些小家伙每年红柳开花的时候,会把枝条叼走,编成圈当花冠。有时还会排成一溜跳舞,嘴里咿呀咿呀地念叨着“呦呦”——听着像啥?祭祀?合唱?还是单纯的孩子撒欢?没人知道。还有更“童话”的细节,比如这些红柳娃,馋极了,喜欢翻背包、偷军营伙食,一旦被人逮住,就哇哇大哭,跪地求饶。你说它是不是懂事、是不是聪明,反正那份“人味儿”,说怪也怪,说可怜也可怜。要不怎么一到夜里,那些孤单守夜的老汉,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
顺藤摸瓜,故事线能一直拽到唐朝。《酉阳杂俎》里边,提到成都一位李大人,得着了一具奇怪的“尸蜡”。小得吓人,只有一只小老鼠那么大,面容却五官清晰。李大人说是源自焦侥国的小人,身后一串哀怨。有人传言,这焦侥人一入中原就病重,骨瘦如柴,还没答上两句话就咽气了。尸身做成蜡像,寄着个回家乡的盼头——是不是有点像今人漂泊他乡,归无归处,连灵魂也带着点凄清?
再晚些,元朝的陶宗仪、宋朝的野史,都不时插播“发现小人尸干”的趣闻。细节不一样,确都提到“有个小得出奇的族群,偶尔流入世间,像风像雾”。其实吧,这类记载是真是假,甭说咱们,就连当时写书的人,多半心里也一个打鼓。可越是这样曖昧,越是勾得后来人想探个究竟。
关于焦侥国,翻遍太平广记,都没谁能说得清它的真面目。有的说在新疆,有的说在更远的无人区。怎么找都找不到。当年李章武的焦侥人尸蜡,倒给了多少文人墨客以想象的口实。严肃点的当轶闻笔记,浪漫点的干脆写成小诗。可惜,任何一个想过问的,都得止步在“再无下文”这道槛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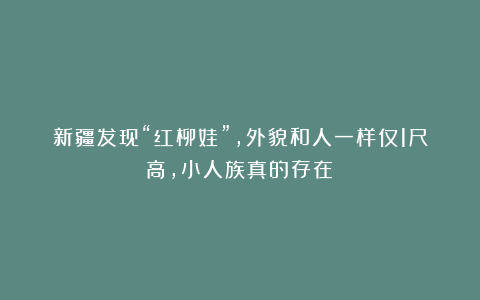
你说,这一桩桩“红柳娃”踪影、焦侥国传说,是不是人类心头永远的痒:山那边是不是还有未知?我们没见过的,会不会真的存在?真真假假,全靠你自己信不信。
当年老马惊魂未定地回到营地,还以为这事儿能赶紧过去。谁知第二天一早,有人说后山发现一串小小的脚印。脚印细得像未成年的孩子,深浅交错,最后消失在一片红柳丛中。你看,这就是生活——它总会留下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给你“做梦”的空间。有人说是野动物胡闹,有人信那真是毛孩子路过。就像咱们现在网上流传的“UFO”视频,谁没在睡前胡思乱想两句?
至于科学怎么说,争得倒也热闹。有人坚信那是灵长类进化的分支,躲在西域深山独自过活。理由嘛:毛多,灵巧,听风就是雨,见人就溜。反对的人却抬杠——你见过哪种猴子会流泪、会下跪?猴子要是“人味儿”这么重,还不早进动物园明星行列了?嘴上一仗难分输赢,背地里谁还没点私心:要是真有这种神物,世界多有意思。
当然,民间更会编,把“红柳娃”当成《西游记》里的“红孩子”落户人间。有胆大的大姐,晚上放羊还真能冒出个小人影子来吓自个一跳。你要是追问,她眨巴眼说,你不信是真没碰上。——这种故事吧,多少带点儿自家院子里的烟火气,真假不足为外人道。
后来呢,年复一年,天山草原变化得快。城市化、工厂、油田,噪音和废气铺天盖地,老马那片柳树林也成了物流中心。谁再提“红柳娃”,已经不多了。不是没人信,只是大家忙,活着不易,难有闲心泡杯热茶坐树下等一场离奇的邂逅。
但有趣的是,每隔几年,总有人在论坛上翻出老一辈的闲话。有人说,是环境变了,红柳娃给赶走了。也有人说,本来就是一群鬼精灵,谁也别奢望捉住。几条模糊的脚印或一颗被啃咬过的果子,成了爱信的人夜里寂静时的小乐子。
该信哪个?没人能拍着胸脯说清。但世界要真是没点“讲不明”的——那日子该多没劲。谁愿意未来全是水泥、钢铁,和一望无际的事实?
老马那年再没遇上红柳娃。再后来,他退休南下,家里人搬了三回。可每次喝点小酒,他总喜欢逗小孙女,说自己“差点把妖怪揪回来陪你玩”。孙女笑着跑远了,院子里晒着手洗的衬衣,风一吹,晃晃悠悠,就像那棵柳树下,说不准哪天真的还会钻出一个说不定的奇遇。
我们呢,虽然活得越来越“科学”,可心底没准还是盼着,有一天走在路边,突然听见一阵“呦呦”低语,一个答案悄悄靠近身后。谁知道红柳娃到底存不存在?或许这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能让人有一丝好奇、一点温柔的期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