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毒品使用量只有欧盟各国平均用量的三分之一,这背后是这个北欧国家投入三倍于欧盟平均的禁毒经费、长达半个世纪的坚持和一套备受国际关注的政策体系。
1950年代,苯丙胺在瑞典的用量相当大,而且很容易获得。1960年代后半期,由于毒品管制不严,瑞典毒品用量出现全面上升。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瑞典逐渐加强了对毒品的管制,毒品用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大幅度下降。
01
法律框架:从宽松到严格的演变
瑞典的禁毒政策并非一贯严格。在1960年代,这个北欧国家曾采取相对宽容的禁毒方式,甚至在1965年至1967年间允许合法开具毒品处方。
政策的转变始于斯德哥尔摩的精神病学家尼尔斯·贝杰罗特(Nils Bejerot)的分析与倡议,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毒品政策方案。
随着时间推移,瑞典逐步收紧毒品法律,消除了一切合法持有或消费非法毒品的法律灰色地带。
1990年代初,由于预算削减、失业增加和毒品供应增长,瑞典的毒品用量再度抬头。
作为回应,瑞典政府实施了一个全国行动计划,设立全国控制毒品协调员职位,并大幅增加控制毒品的经费投入。
瑞典为实现无毒社会的目标,对毒品使用采取了“零容忍”政策,并在执法、预防和以戒断为基础的治疗方面投入巨资。这一政策模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吸毒现象。此后,瑞典逐步提高了毒品犯罪的最高刑罚,并在1988年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将持有毒品和吸毒行为都定为犯罪。
最初,吸毒仅处以罚款,但这种情况在1993年发生了变化,监禁也被纳入了可能的处罚范围。引入更严厉的处罚措施是警方无需个人同意即可进行血液或尿液检测的前提条件。目前每年进行此类检测的次数高达 3 万次,此外,每年还有 1 万次针对驾驶员的检测。
过去十年间,因毒品犯罪被定罪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虽然罚款仍然是最常见的处罚方式,但绝大多数定罪(83%)都是针对简单的持有或使用毒品。因此,绝大多数被定罪的都是轻罪犯。
近年来,瑞典议会通过立法将吸毒定为刑事犯罪,并扩大当局收治成年酗酒者和吸毒成瘾者的权力。
02
管控体系:全方位禁毒网络
瑞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禁毒法律体系,其中包括《麻醉药品处罚法》(1968:64)和《麻醉药品管制法》(1992:860)。
这些法律为列管麻醉药品提供了法律基础,并定义了什么是“麻醉药品”——即“任何对健康有害、具有依赖性特性或令人兴奋的药物物质或商品”。
1999年,瑞典通过了《禁止某些危害健康商品法》,该法适用于那些“因其内在特性,对人类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并被用于或可假定用于中毒或其他影响目的”的商品。
瑞典的毒品列管系统不断更新,以应对新型精神活性物质(NPS)的涌现。
例如,在2015年1月,瑞典政府修改了《关于禁止某些危害健康商品的条例》(SFS 1999:58),新增列管了32种新型精神活性物质。
这种动态的管控系统使瑞典能够及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毒品,确保法律与实践同步。
03
禁毒成效:数据说话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06年发表报告,特别指出瑞典的毒品政策是值得各国学习的成功范例。
报告数据显示,瑞典的毒品使用量仅为欧盟各国平均用量的三分之一。
这一成果的背后是瑞典对毒品控制的高度投入——投入的经费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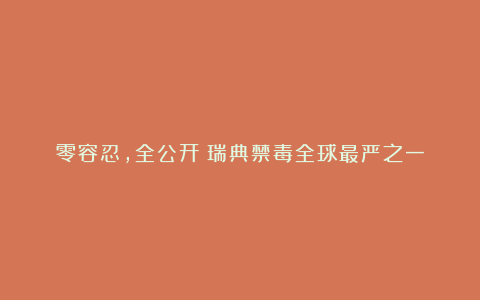
从2001年以来,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瑞典的毒品使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瑞典的禁毒成效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研究显示,瑞典年轻人使用非法毒品的水平在欧洲范围内处于非常低的位置。
瑞典证明了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能够将社会福利与防止非医疗用药的有效方法结合起来。
04
创新实践:多元协同的禁毒策略
瑞典的禁毒工作不仅依靠法律制裁,还不断创新预防和干预方法。
其中一个例子是“反毒品俱乐部”(Clubs against Drugs,CaD)项目,这是一个针对夜生活场所的多组分干预项目。
通过社区动员、培训和执法协同,该项目在20年的持续实施中显示出显著且持久的预防效果。
研究显示,对明显药物中毒顾客的干预率从2003年基线7.5%显著提升至2023年56.9%。
另一个创新实践是瑞典邮政系统参与的“共同对抗网络毒品”(Together against online provided drugs)项目。
这一项目通过改变邮政工作人员的操作规程,使他们能够在发现邮件中含有毒品时联系警方或海关,有效拦截了通过邮政系统流通的毒品。
2022年7月1日,瑞典对《邮政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允许邮政服务与执法当局之间的合作。
05
经验与挑战:平衡的难题
瑞典禁毒政策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几个关键因素:长期一贯的政策、充裕的资金支持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
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科斯塔所指出的,这些因素是瑞典控制毒品成功的关键。
瑞典毒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创建一个无毒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瑞典采取了惩罚性的、以执法为主导的毒品政策。一些人认为,正是这种政策造就了瑞典历史上极低的毒品使用率。因此,瑞典模式的这种表面成功常常被用来反对毒品政策改革,例如非刑事化和法律监管。
然而,瑞典低毒品使用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压制性政策,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研究始终表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才是毒品流行率的关键驱动因素,而非执法的严厉程度。
然而,瑞典的禁毒政策也面临挑战和批评。有研究指出,瑞典的禁止主义立法和政策对吸毒者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
瑞典致力于打造无毒社会,这导致旨在减少毒品使用潜在危害的干预措施难以推行,而非预防或消除毒品使用本身。2011年发表的一项重要评估报告指出,有必要扩大减害措施的规模,但由于上届政府坚持以戒断为基础的方针,因此未能采取行动。活动人士希望新政府能够重新审视这些建议,但目前瑞典的减害服务水平仍然低于欧洲标准,也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建议标准:
全国只有五个针具交换点——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甚至没有一个。
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OST)虽然存在,但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美沙酮)。
一些OST中心对使用其他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导致接受治疗的人数减少。
监狱中的OST于2007年作为试点项目启动,并于2010年成为一项全国性计划,但覆盖率仍然很低。
瑞典没有提供安全注射工具包;没有全民乙肝免疫接种计划;过量用药信息和过量用药应对培训也十分有限。纳洛酮(可对抗阿片类药物过量的影响)只能通过医务人员获得,不能带回家使用。
瑞典没有受监管的吸毒场所(例如丹麦、德国、荷兰、西班牙和挪威的此类场所),也没有收集关于在夜总会和音乐节等娱乐场所提供减害措施的数据。
这些问题包括社会排斥、缺乏整体服务提供,以及警方对吸毒者的虐待和暴力行为。
近年来,公开毒品场景和枪支暴力也成为瑞典禁毒工作中的新挑战。
研究显示,毒品市场和枪支暴力的模式有所重叠,使得这些犯罪热点地区的问题更加复杂。
今天的瑞典,在斯德哥尔摩的夜生活场所,对毒品干预率已从2003年的7.5%上升至2023年的56.9%。而在二十年前,瑞典的毒品使用量曾一度回升。
从宽松到严厉,从单一到系统,瑞典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严格的禁毒政策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