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这活儿,说起来谁都想当,可真轮到自己头上,未必就那么痛快。百龄就遇上了这事:嘉庆十六年,老百姓夸他是好官,皇帝也给了面子,让他从两广总督调进北京,眼看就要升成刑部尚书。这按理说是一步青云、火箭升官的节奏了。但谁能想到,百龄接到圣旨,心里的忧虑却比当县令还多,进京后一声不吭,先递上辞呈——说自己有病,想歇着,不想干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这事啊,还真不是表面这么简单。有人说清朝刑部官儿带点原罪,干这活总让人觉得背后凉飕飕的。一边是皇冠上的荣光,一边是官场的冷板凳。这就像,我们今天工作遇到升职,有人欢喜有人愁,谁还没点自己的小九九?
很多人不明白,刑部尚书,这可是朝廷一品大员,名头响、权力大,还能直接和皇帝对话。怎么会有人不想要?但在清朝科场百家争鸣的年代,刑部的名声始终有点尴尬。为什么呢?你说汉朝讲吏治、唐宋推名臣,到明清,刑部变得“又管生又管死”。儒家雅士从来觉得跟死人打交道是晦气事儿,哪怕官大也不沾这个边。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说到刑部在清朝六部里的地位,还真不是表面上那盘棋。排序呢,刑部挨着工部,靠后排,但要说日常事务、难度,就数这儿最复杂。每年秋审、冤案、要命的死囚,头疼得很。可那些自小读圣贤书的官人,更愿意去吏户礼部,哪怕当礼部里管礼仪的闲职,也不想碰刑官这块硬骨头。你琢磨这“身份感”,还真有点像今天的行政岗和纪检岗:一个香饽饽,一个累人还遭人嫌。
古时候习惯自称“士大夫”,啥叫士大夫?谈笑风生,动辄“仁者爱人”。但碰上刑部,心里打鼓,怕背上酷吏的名声。有进士李坚,乾隆朝选官时分到刑部,人前摆脸色,说自己不愿做那“法吏”,还真硬着头皮四处活动,最后才调了出去。这个活儿多人躲不是一天两天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说到方家的故事也有点意思。嘉庆年间,有个官员方璞,家里原本清白,做了刑部湖广司的差,人家自己没啥意见。可他爹听说儿子去管刑事,着急忙慌,像是自己去坐牢了一样,还为此四处花钱,最后花重金把儿子调走,那自由空气才算吸了一口。你说做亲子的,宁愿花银子,也不让孩子沾染“用刑之地”,心里那份执拗,其实跟我们现在拼命让娃避开某些行当一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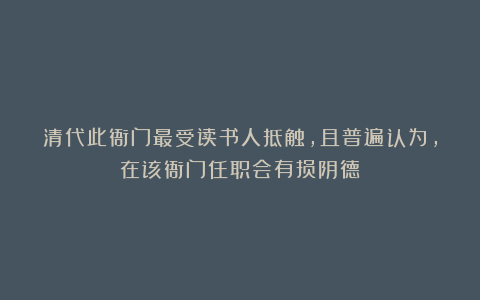
刑部,其实是拜相的跳板,百龄要是上任了,再过几年大学士也不是没戏。可是他一听说要在刑部坐厅,脸色就变了。其实明眼人也看得出来,他不是一般倔。他这一生,说白了也不是没见过风浪,但做刑官这事儿,怎的就是心里过不去?不过,京城里的风声也不能忽略,刑部当时的领导金光悌,是出了名的酷烈,办事狠辣,百龄要真去坐班,说不定得和这号人并肩,名声里难免沾上点戾气。官场上风评,谁不介意?百龄能干两广,能不能玩转刑部,这里面其实是有一条隐线。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官场知识这东西,有人天生就不在行。当时大多数做地方官的,律例根本没钻研,谁会没事去背条文?分到刑部,下属全是书吏、差役、犯人,场面狼藉,在清高的人嘴里,那就是风尘俗事。乾隆年间有个王又曾,进士出身,一封任命下来,得在刑部当差。结果他一点律条都不会,内心憋屈又害怕,最后干脆找借口养病,拍拍屁股就走了——也是痛快人,圣旨没挡住心头的忌讳。
刑部的活儿,不光是法律,还带点阴晦。特别是每年秋审刑讯,各省死囚涌进京城大牢,刑部官员要天天面对三教九流的案底,脑袋里压力山大。这种气氛放在书生头上,始终有点“穷途末路”的意味。你想,捧着诗书长大的,真未必受得了监狱铁锁和冤魂哭嚎的日子。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这里面,还有一层佛教色彩。古时有句闲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士大夫信因果,中枢里讲究积德。刑部手里杀人问罪,谁都担心自己杨家后世不顺,抖落了阴德,死后还下地狱。说是迷信,其实骨子里是怕事。到晚清,有个官员张云藻,干刑部,家里没后,便信是自己因工作“杀人太多”惹的祸。这种说法,京城里怨声载道。另一头,金光悌,做了一辈子刑部首脑,人到晚年儿子病危,也是向佛长跪求命,同僚们背后都拿这事当茶余笑料——但谁又真愿意碰上呢?
其实讲道理,所有当官的都念叨刑名是国本,可一到自己身上,却宁愿退避三舍。这气质,跟古人讲矫情也没错。一面高呼治世,一面怕丢名声,谁又不是凡人?我们总笑明清士大夫虚伪,但细细想来,有些人性里的纠葛,是绕不开的。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百龄那次进京,不敢说是怯场,至少有点自知之明。面对刑部这锅浑水,他宁愿慢一步,也不肯顺受潮流。嘉庆帝后来看透了他的为难,把他挪到左都御史,绕开风口,算是给面子也给台阶。这一遭之后,或许百龄终于松了口气。换做我们,面对一步登天的诱惑,自己也许也难做那个痛快人。
古人的隐忧、士大夫的矫情,在官场沉浮里无处不在。朝夕之间,有些路不愿走,理由或许千头万绪,也许只有一句:人各有志,谁都不愿自己心里有个结,哪怕身旁皆为荣耀。至于百龄后来怎么想,他是否真的后悔?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令人心虚的刑部尚书之位,往后还得许多人绕着走。
世间功名,谁说得清值不值得?有时想通了,不过是一坛旧醋,一身俗尘,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