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拾稻金
漫游武功山
今天是自武功山回来的第六天,一个可以缓口气的星期六。中午,吃了点母亲新近酿成的米酒,微醺中来记录上周末的那趟行程。之所以现在才动手,一是归来当晚身体疲惫不堪,倒头便睡;其后几天,是工作日,又陷入了日常工作的繁忙漩涡,总不得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心想静心通读一遍《西游记》后,再动手写作。
为何非要如此?只因那日在金鼎漫游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浮现脑海: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上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故事可谓跌宕起伏,但细细看来,他们少有“匆匆忙忙”的时候,步履似乎总是透着一股不紧不慢的从容。他们虽有明确的目标,却从没有紧张赶来的时候,遇山看山,遇水渡水,化缘、讲经、降妖,一切仿佛皆顺其自然。这与我等今人凡事讲效率、赶时间的“慌慌张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我想,真正的“行万里路”,或许正应了是那般气度。于是,在再读了《西游记》后,我才觉心境沉淀下来,可以开始这电脑上敲字了。
此番奔赴武功山之行,于我而言,实在是太迟了。为什么说太迟呢?首先娃娃们都到过了而我才动身,更重要的是我的贵人——大汉天子的后人家就在武功山脚小的泸水河边。感恩思源,到安福去看看,去泸水河边跑跑步,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此行,与其说是一场观光,不如说是一场感恩之旅,一场试图通过脚步去丈量、通过呼吸去感受那片土地的温暖。
路途迢迢,到安福县城已经天黑,却倍感亲切和温暖。第二天,天际刚刚透出一抹鱼肚白,我便已起身。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用一场晨跑,来问候一座陌生的城。按照地图指引,我很快就跑到了泸水河边的绿道,之后便沿着河慢跑。泸水河边,我不追求速度,只享受这种与大地一同苏醒的过程。我的目光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尽管河面不宽,却给人宽广的遐想,刘氏先人选择这样一片土地栖息,应该是有远见的。泸水是赣江的支流,赣江又是长江的支流,这就给人一种——进可以顺流而下到达汪洋大海,退可以耕读传家、休养生息。
当我手腕上的华为手环轻轻震动,提示我已经完成了设定好的6.66公里时,我恰好停在一座桥边。这个数字,于我而言,是一个寓意着顺利与圆满的吉兆,于是欣然接受这份来自安福清晨的祝福。此刻,朝阳已完全跃出地平线,万物都沐浴在冬日暖阳中。我用这样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奔跑,完成了与这片土地最深切的初晤,为接下来的武功山之行,住满了清醒而平和的力量。
回到酒店简单冲洗一番,从容地享用了安福地道早点,让温热的食物暖透全身,才不慌不忙地在酒店门口等待前往武功山的大巴。没有一会儿,大巴来了,我随着同样去往武功山的人们,一起上了车。大巴蜒的山路上盘旋,我的心也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充满了期待。及至乘上索道,那种漫游的感觉愈发强烈。缆车以一种近乎优雅的缓慢速度攀升,如同一只巨大的摇篮,将我稳稳托起,送入云端。透过明净的窗,我得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视角,俯瞰着窗外的景致如何从深秋的斑斓,一层层褪去繁华,最终彻底演变为冬日特有的、素简而苍劲的笔触。当缆车悠然越过最后一道山脊,那片在照片中见过无数次、在人们听闻过无数回的十万亩高山草甸,就以一种无比磅礴、无比坦荡的姿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一种漫山遍野的、酣畅淋漓的枯黄,昔日的绿浪翻滚,化作了今日深沉厚重的金色海洋。每一株草,都褪尽了春夏的水分,只剩下坚韧的筋骨,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最幸运的是,今日天公作美,晴空万里如一块无瑕的蓝宝石,一轮明亮的冬日暖阳高悬中天,慷慨地将光与热洒满山峦。预想中那割面生疼的凛冽山风,此刻也温柔得不见踪影,天地间一片温暖、宁静、和煦,这完美契合了我心中对于”漫游”的全部想象——一个可以让我肆意停留、无需匆忙的绝佳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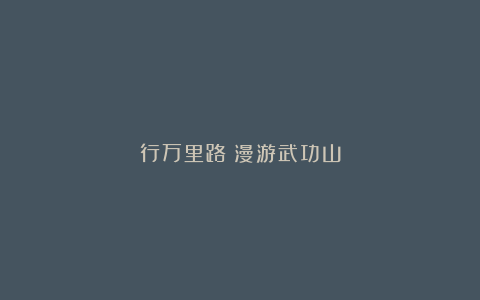
我真正的、灵魂意义上的漫游,从双足切实踏上山脊游步道的那一步起,才正式宣告开始。我彻底抛开了所有的时间观念与路线规划,让自己的步履完全听从内心好奇的指引。我走得极慢,慢到可以听见自己均匀的呼吸声,慢到可以看清每一株枯草在逆光下呈现的、如同毛玻璃般的通透纹理。这信步由缰的状态,无意间竟暗合了这片山野深厚的历史文脉。武功山的历史文化遗存,素以佛、道、儒三教交融而著称。儒家思想如空气般渗透在山野角落的秩序与人情之中,而安福武功山,更是道、佛文化的重要源流。此刻,我恍然意识到,我这般摒弃目标、心无杂念的行走,不正是道家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某种实践吗?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以“道”为基本信仰,尊老子为教祖,强调“清静无为”。“清静”是道的表征,关键在于没有贪欲,《清静经》有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此刻,我心中无赶路的焦躁,无打卡的执念,唯有对眼前草木天光的全然沉浸,这或许便是一种短暂的“清静”。而“无为”,并非不为,乃是做事不夹杂私心,顺其自然。我此时的漫游,东走西看,全凭兴之所至,不正是“按道而行,顺其自然”吗?这般想来,我的脚步更添了几分从容与哲思的韵味。
我看到一块形态奇崛的褐色巨石,便会走过去,用手掌感受它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表面,想象千百年来,是否有修道之人也曾在此驻足静坐,吸纳天地灵气。我望见一片草甸因坡度的起伏而在阳光下形成美妙的光影乐章,便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主径,走过去,找一处最柔软厚实的地方坐下,甚至躺下,闭上眼睛,让阳光像一床暖被覆盖全身。这无边的旷野与寂寥,不正是道士学道修道,以“清静”炼心的天然道场吗?天地之大,唯我一人,仿佛整个宇宙都向我汇聚而来。
就在这走走停停、恍若时间停滞的漫游中,我的思绪也飘向了远方。我想起了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那个正月初一,旅行家徐霞客自安福方向开始他探访武功山的壮举。他在《江右游日记》中开篇即写道:“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正南为香炉峰,尤耸拔云表,为武功主峰。” 我停下脚步,倚着手杖,在湛蓝得没有一丝杂质的天幕下,极目远眺,试图在那一道道如屏风般横亘于天地之间的山脊线中,辨认出霞客先生当年所见的“香炉峰”。我的足迹与他的记述,在这跨越了近四百年的时空中,因这同一条山脊,而产生了奇妙的重叠。他的探险精神,与我所体会的道家“顺其自然”的漫游,虽形式迥异,却都是对这片天地的深度叩问。
而此行最令我感到惊奇,甚至带有一丝宿命意味的巧合,发生在我下山之后。当我怀着随意的心情,点开手机上的运动轨迹,想要回顾这一日的行程时,我被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惊呆了:我在山脊上信马由缰、毫无目的、东游西逛的总徒步距离,竟然也是6.66公里!与清晨在泸水河畔奔跑的距离,分毫不差!一个是我主动选择、寓意美好的开始;另一个则完全是随心所欲、无意中走出的结果。这两个数字的精准契合,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条无形的线,将山下的水与山上的路,将晨起的动与日间的游,完美地串联了起来。这奇妙的“无为而治”的结果,不正是对这场“清静”漫游最美好的嘉奖吗?为这场漫游画上了一个无比圆满、充满神意的符号。
我的漫游,也因此更添了一层与古人精神对话的深邃色彩。当我想象徐霞客当年,在此地“升降宛转,俱在半天”,发出“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金在冶,游人履步彩云间”的赞叹时,我对“金在冶”三字有了触电般的感悟。眼前这片在明媚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枯黄草甸,不正像是在天地这座宏大的熔炉中,被淬炼出的、流动着的纯金吗?而我,则以这“清静无为”的漫游姿态,行走在这奇妙的数字循环与三教文化交融的意境里,感受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宁静与喜悦。
就以这样完全不理会时间流逝的步子,我悠悠然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登上了金顶。顶上景象,与我一路享有的清幽自是不同,因天气绝佳,此刻已是人流如织,充满了节日的欢腾气息。游客们脸上洋溢着笑容,纷纷在标志性的石碑前排队留影。我并未急着挤入这热闹的漩涡,而是在人群边缘寻了处相对安静的岩石坐下,饶有兴致地当一个观察者。这喧闹热烈的场面,与徐霞客笔下“宿于山脊之茅庵”的孤寂清苦,已是天壤之别;这芸芸众生的欢乐,也与道家隐修者的清静山林大异其趣。他盛赞武功山“虽未及黄山之奇诡,庐山之飞瀑,然其山脊草甸之绵延开阔,独具一格,令人胸襟大畅。” 站在这温暖的阳光下,感受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层叠与当下的喜悦,我对他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共鸣——这开阔,不仅在于地理空间上的无垠,更在于它能海纳百川般地容纳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情感与体验,既能承载佛寺道观的清修,也能包容儒家学说的教化,既能寄托一个人的幽思,也能欢腾众人的假日。而我的“漫游”,恰好在这诸多维度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属于我自己的平衡与丰足。
流连忘返,直至日头明显西斜,山风开始带来些许凉意,我才带着满心的丰足与不舍,踏上了返回三百多公里外、我在赣州的家的归程。车轮飞驰,窗外的景色从苍茫山野逐渐变为田园城镇,最后融入漫长的高速公路夜色。身体虽因一日的行走而有些疲惫,但我的精神却异常地饱满、宁静而喜悦。
回望此行,它早已超越了一次简单的地理上的抵达与离开。那泸水河畔因长者而生的深切感念与晨跑开启的仪式,那冬日暖阳下如金似火的草甸所赐予的温暖与磅礴,那贯穿始终、充满神奇宿命感的两个6.66公里,尤其是那在缓慢步履中,与长者乡愁的共鸣、与徐霞客足迹的隔空神交,以及对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道法自然之“清静无为”的切身体悟……所有这些细微而真切的体验,都已深深沉淀为我生命年轮中厚重的一圈。这段旅程,始于一份感恩,成于一次融入文化的漫游,终于内心的充盈。而这一切收获的广阔与宁静,必将如这山脊一般,绵长而稳固地,留驻在我的心间。此刻,碗中米酒已尽,窗外月色正明,我的纸上漫游,也终于追上了六日前的脚步,心,也随之安顿了下来。(草稿于2025年11月19日)